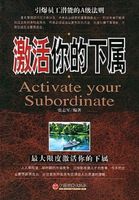天亮时出发,到达太羽山山顶禅宗寺内时已是黄昏。一番简单行礼后各人众被安下自己各处。在寺庙大堂祭拜时,贻萝稍稍留意了一下。皇朝后裔家属中,竟属得宋离这边格外的少了,不算上家奴。宋离与余素敏以及她,统共三人。而一般都是一男子携带好几位妻妾。
主屋由宋离和余素敏住下,她住偏屋。夜里睡下恍惚间又仿佛见到宋离坐到自己的床沿边,正细细的打量着自己。她翻了一个边过去,床沿的重量减轻了些,那人起了身,随后又听见开门走出之声。她闭目还做睡着之状,眼角却不觉一阵湿润。不知何时终是昏昏沉沉入了睡。
天还未亮之时就被叫醒梳妆打扮了,素衣素服。宋离更早的去了。她同余素敏被归到女眷一边,到皇后那边听候。大堂人群林立,有奴人端来瓜果烧香,僧人木鱼念经。祭拜者位高至低依次上前持香跪拜。皇帝身边有一服侍女官,做的男官打扮。贻萝瞧着她看了两眼,只觉得眉目异常眼熟,又一时想不起是谁了。
午间稍作歇息。到申时,再由直系后裔,也就是皇帝及永侯王宋离、煜王宋方三人及其各自家属前往各侧山先祖陵墓做祭文祷告,汇报先祖过世后梁国国情一应。
一府的人出去做事应该都是这个理数,男人永远都是与正室在一起的,妾室都是跟在后头的。就像现在,皇帝的妾室同王爷的妾室因为位阶太低,尚不能靠近皇陵。只由那几人带着正室前往,还另带着几个护卫。
那个她瞧着眼熟的女官也被留着了山脚一同等候。众人都回马车歇坐了,贻萝却不上车,只朝着她走过去。那女子看她走来,低身行礼,却不言语。
贻萝自我介绍道:“我是永侯王家的侍妾。”
那女官微微服身道:“拜见姑娘。”
贻萝看了看她,既知她身份,又只做了服身礼,看来应该是品阶同她一样或者是比她还高的女官了。贻萝心下猜想,面上只扶过她亲热道:“女官姐姐多礼了。贻萝只是瞧姐姐面善,甚觉欢喜,所以过来打个招呼,还不知姐姐姓名?”
“下官由陛下赐名唤玉影。”
……
回程到禅宗寺已是天近黄昏,由于是祭祀,做不得宴席。每餐便都只作了个人自己的吃去。月蝉将素食上于桌上摆好,却见贻萝自打进屋起就一直在沉思着什么,她微微唤了两声,“姑娘,吃饭了。”
贻萝点点头,随意吃过一两点,便要月蝉散了去。随意搭了个袍子开了门,一阵冷风袭来,她不觉拢了拢衣襟。山顶寒意远深于山下,即便现下已是入春多时了,外头也零零散散飘着些小雪来,贻萝心下不觉生出一丝恐慌来,开头皇陵山脚处交谈的那女官,可能容貌已不完全像了,可是那说话的神情、语气。她绝不会认错,那分明就是慕容静!
对着月蝉问道:“王爷现在可在王妃处?”月蝉答是。
“那你去找找阮炎,央他邀王爷出来一下。就说我有事找。”
月蝉听得“找阮炎”一句,却是一喜,贻萝疑惑地朝她看过去。月蝉只赶快应下面色绯红的出了门。
阮炎来时说宋离刚刚陪同皇帝去了偏山平云王墓,夜里不会归来了,要她什么事只到明天再说。贻萝心中冒生的念头令她不安,只说不行,今晚必要见到宋离。阮炎没法,只得带了她到平云王墓那座山脚下一处空置民房内等候,他上山去找宋离。
又岂料出门之时被余素敏房里的一个丫头看见了,那丫头又赶忙去告诉了余素敏。余素敏一听便暗下悄悄跟了来。
虽说是偏山的山脚,在高度上却比主山脉的半山腰还要高出一些,气温也就高了不山顶多少了。
宋离来时,大氅上竟是飘雪。却是赶得急所致。一进门就对着贻萝叱道:“什么事不能留着明天说,腿刚好了些,现在又四处乱跑。”
贻萝看了看一同进来的阮炎,阮炎示意,退了出去。月蝉也甚是会意的出了去。
屋子里头就只剩得他二人,贻萝走近宋离,直盯向他的眼眸问道:“我问你,你想用什么办法夺皇位?”
宋离蹙眉,随之沉声道:“你何必每天思虑那么多。要怎么做,我自有定夺。你只安心过好现在便是。”
贻萝直言道:“皇帝身边那个女官是慕容静吧。你安排她到那里是想干什么。你难道想……”
贻萝眼神宋离一眼看透,她话未说完,他手突然一伸,将她拉得更近,贻萝一愣,只见宋离朝着她低头微声道:“我是要杀了他,不过方法没你想的那么蠢。”果然如她所想,贻萝愕然道:“他可是你的父皇!你便是要夺位也不应该杀了他啊,你这样做就不怕被天下人辱骂?”
宋离冷笑道:“辱骂?他****茳才应该是那个被天下辱骂的人!当年原祖过世,本该是我父王登位,他却串通了余震戎下计将我父亲害死,自己当了皇帝。我的叔叔户王知道这件事被他幽静一生,你的后母姬扶在他手下办事知道他的这些丑恶勾当也被他追杀多年。我要杀了他,夺回本该属于我父王的位子,谁敢辱骂!”
贻萝征然间,又听得宋离道:“事后两年,他心中生了悔过之意,又将我收在他身边做第五子养着。却一直不闻不问,如同监禁一般。这么多年我都一直在隐忍,一面结交外国势力,一面设法慢慢取得他的信任与宠爱。直到这些年他才慢慢开始任用我。但我终究非他亲生,以后皇位也绝对不会传给我,宋稳宋方二人无论以后谁做上了这个位子,都必会先铲除了我!我只有造反夺位!”
贻萝已是讶得说不出话来,又一想起,不觉惊问道:“可是那时的你应当尚在襁褓之中,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他非你父亲?”
“摩鸠山上的那位,原祖的世交,亦甚疼爱我父王。我懂事之年,他悄然来我府上授我武艺事理,也多亏了他,我才得以知道这一切。”
屋子外头的雪还在洋洋洒洒的落,风越刮越大。余素敏蹲在后窗之外,抽了抽鼻子,啐道:“木贻萝这个贱人,背着我来这里勾搭王爷,还靠那么近,偏生风刮这么大,听都听不见他们在讲什么!”
余素敏看楚妍不回声,朝她看过去,竟是她替她挡着风,位置正在风口上,早就冻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