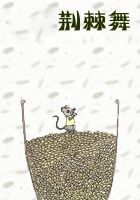有一次,我和潘晶晶在村东头再次不期而遇。当时的她,正骑着一辆崭新的脚踏车,长发飘飘要去县城的路上,而我也骑了一辆脚踏车,不过却是正在回老家的路上。——两年前,我爸妈在市里买了一套房子,于是全家就都搬到市里去了。偶尔,一家人会回老家住上几天。
我说:“你去县城啊!”
她点头说:“嗯,你这是回来?”
我“嗯”了一声,说:“回来拿点东西,你最近过的好吗?”
她笑靥如花:“挺好的!”
我感觉她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大大咧咧了,表情无比的矜持,像一个大家闺秀。看到邻家女孩初长成,我却有点失落,我多想她可以像一个野丫头,也许那样我们就可以开开玩笑什么的。我感觉嘴里有成千上万句要脱口而出,最后只说了三个字:“那就好!”
她说:“我要去县城办件事。有空我们回头聊。”
我说:“好的!”
夕阳西下,她离去的倩影美艳不可方物。好像她身上镀了一层金光一般。她是仙女?
而我那天家里临时有事,错过了和她相逢聊天的机会。——她离开不久,我就又马不停蹄赶到市里去了。
那一天后,我和她并无交集。
我们就像两列相向行驶的列车,渐行渐远。
很多时候,我在想,我是否有勇气让自己可以不用成长得那么成熟,可以让自己像一个自由自在的疯小子,大大咧咧去找潘晶晶,痛痛快快地和她聊着天,诉说着童年和少年的那些快乐的糗事。我是否敢敞开心扉,轻轻问她一声:“最近,你过得好吗?”然后她未给予我答复,我心底已泛起涟漪的情意,痛楚不已。
最后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这样的勇气。
勇气绝不是心血来潮,也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对一件事物的了解娴熟后做出的一种选择。我对潘晶晶的近况知之甚少,我似乎也没有很好的渠道去了解她的方方面面。时间催生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空间同样也在催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不得不锥心的承认,在对待潘晶晶的感情上,我输给了时间和空间。
要命的是,我不知道我对潘晶晶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传统意义上人们所说的:喜欢一个人。
更要命的是,我根本不知道潘晶晶对我什么感觉。也许她对我毫无感觉。
不知道对方是否喜欢自己,这种感觉空空落落的。一旦知道对方根本不喜欢自己,那种感觉就等于是给自己的心里结了一个茧,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茧。
我不想作茧自缚。
不管怎样,潘晶晶的身影一直如同一幅无比精妙的水墨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记得我曾作词一首,在那首词里我把她想象成一只美丽的梨花精。而我是守候她身旁的一个小书生。
词是这样写的:
书里的梨花精
作词:鬼侠
踏着星光一点点蚕食着前方的路
谁的咒谁的梦让青州无法复原那段温柔
你的前世是寺院前的那株小梨树
你的泪你的诀你总在夜里化为墙壁梨花
我是书生手中的毛笔空自将文章挥毫
无法助你逃离前世的魔咒你的哭泣谁懂
你非妖精眸里的哀怨让我悲伤让我惶
究竟怎样的妙计才能救你脱离那座孤城
夜雨清冷空荡荡的孤城兀自响着一支优美的曲子
今夜独我斗胆捧着一卷唐宋诗集静观墙上的梨花
梨花一瓣瓣带着血发出低沉的声音如同狼嗥
偶尔琴声和着寒风从江河路过甩下一阵清幽
这样的夜里我和一个孤魂在心灵隔空对话
不会有任何结局这纯粹就是一个美丽的春梦
梦醒了以后一个人傻傻地笑思想自由飞翔
忘记了哪本古书我曾见识过这样的奇异情节
梨花精雪白色的梨花精她就出现在我的梦里
梦里那只美丽的梨花精你还好吗
今夜傻书生痴痴想念你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