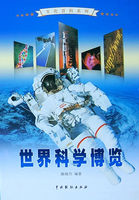此后的几天,龙舞忙于安顿蜃王号的后事。孟颛死了,一时找不到得力的管家,有些事他必须亲力亲为。
水手死亡九十八人,每人发抚恤金五十两纹银;受伤四十五人,送到医馆继续治疗,并每人派发慰问金十两纹银。南洋交易来的物品,大半被抢走或烧毁,剩下的也乏善可陈,蜃王号这一趟航行算是亏到家了。
仲甫自孟颛下葬后,便闭门不出,似乎还没从变故中脱离出来。龙舞也不去打扰他,但有一件事他不得不仔细思量,那就是雨蝶与仲甫的“合弦”之事。
兄弟本是一只手上相连的指头,一根指头断了,另一根就得顶上弥补缺陷,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况且长兄遗子腹中,嫂子若改嫁,则血脉外流,是古训所不允许的,因此贵族之家历来有兄妻弟继的传统。兄弟就像同一张琴上不同的弦,兄弦既断,以弟弦合之,因此这个仪式被称为“合弦”。
虽然雨蝶怀的不是孟颛的骨肉,但这是一个秘密,暂时还不能公开。在外人看来,孟颛亡故,雨蝶有孕在身,而仲甫尚未婚娶,符合“合弦”的所有要求,这已是一件不容回避的事。
但龙舞还不能遽下决心,整日长吁短叹。
“相公愁眉不展,大概是为了雨蝶和仲甫的事吧!”兰香不愧是个兰心蕙质的女子,一下子便猜中龙舞的心事。
“夫人果然懂我!这个事情实在有些难办呐。”龙舞赞许地看了一眼兰香,又叹了口气。
“不知此事难在何处?”兰香问道。
龙舞道:“按古例,雨蝶须续嫁给仲甫,但你也知道,雨蝶跟孟颛只有夫妻之名,未有夫妻之实呀!”
兰香道:“这中间的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了,且不足为外人道,我们不妨顺水推舟,让他们两人在一起,日后雨蝶生了孩子也有个照应。”
龙舞道:“话是这样说,可我心里还是有一些担心。”
兰香道:“你是怕仲甫靠不住?”
龙舞道:“正是,这孩子心里有一些东西我至今还没看清楚。再说,这次南洋的事件还有许多疑点,虽然我不能断定发生了什么,但事情肯定没他们说得那么简单。”
兰香道:“海盗纵火抢劫,船上的人都有目共睹;虽然对于孟颛是怎么死的,大家还有不同的说法,但都没人怀疑到仲甫身上,我看不应跟他扯上关系。”
龙舞道:“撇开这些不说,然而雨蝶腹中所怀之物毕竟不简单,菩萨虽未明示,但可以想象其必有不同凡响之处。眼看再过两个月,雨蝶即将临盆,最怕的就是节外生枝。”
兰香道:“那么暂时不跟仲甫提起这些来龙去脉,待孩子降生之后再作定夺?”
龙舞沉吟道:“实在想不出其他对策,我看也只能这样了!”
一个明朗的日子,雪都融化了,大地干干净净,虽然有些冷,却是个适合出行的好天气。
这一天,又一场婚礼仪式在赵府举行,只不过这回并不像先前两次那样鼓乐喧天、大宴宾客。虽然也贴了窗花和“囍”字,但赵府之内喜庆的气氛大不如前,每个人脸上的笑容好像挤出来一样,显得不自在。
这是因为人们都知道,这场喜事是建立在另一场伤心事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那件事,这对新人也不会走到一起。因此虽然也喝合卺酒,但喝着总感觉不是滋味;虽然也拜天地,但唱礼官也喊得有气无力。
除了自家亲人之外,来道贺的客人也寥寥无几,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瑞德,他跟龙舞谈笑风生,显然是为了活跃气氛,增添一些喜气。
在龙舞和兰香的祝福下,一对新人入了洞房。
冷清,静寂,没人闹洞房,甚至连来讨个福彩的人都没有。
而洞房里,也是一个奇怪的场景。
新娘蒙着红盖头,新郎却迟迟不愿揭去。
过了很久很久,新娘自己把盖头掀开了。
“你是不是很不情愿?”她幽幽地问道。
眼前的仲甫,跟孟颛当时一样穿着一身红色的喜袍,模样比孟颛却英俊了不少。但他脸上没有半点喜悦的神情,反而一副苦瓜相,好像被逼着做了一件十二万分不乐意的事情。
“不敢!”仲甫生硬地道:“此情此景,令我想起了大哥。”
在这样一个日子,在这样一个场所,最最忌讳的就是这个话题了,可仲甫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
雨蝶脸色黯淡了下来。
她心里何尝有半点喜悦之情呢?
虽然跟孟颛的结合并非自己的本意,但她是个死心眼的人,既然认了命,便决心一条道走到黑。在结婚之后,孟颛给了她从未体验过的温馨与安宁,她已认定这就是归宿了,可一场变故击碎了她的美梦,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她本已打定主意忘了其他所有人,但仲甫的出现却在她心底激起一阵涟漪。他跟赵悝长得实在太像了,她面对仲甫的时候,赵悝便阴魂不散地又出现在她心底,这令她感到烦恼。
她对仲甫并不了解,觉得他跟孟颛和赵悝都不一样。
孟颛是一棵树,他就站在那里,你远远就能看见他,走近了还可以靠他身上休息片刻,遇到刮风下雨,还可以在树叶底下遮风避雨,他能给人以最大的安全感。
赵悝是一朵花,你明知道他开放的时间很短暂,在开之前稚嫩脆弱,开过之后很快就会凋谢枯萎,但在他开放的时候,你还是会迷恋他,为他倾倒。
而仲甫是什么呢?雨蝶觉得,他像一阵风,让人看不透,摸不着,有时吹得你很凉爽,有时却可能会让你寒彻骨。
现在,她感觉这风刮得让她有些难受。
“我对不起他!是我害了他!”仲甫的双掌掩在脸上,把整个脸都盖住,发出痛苦的呓语。
“可怕的道士!可怕的圣女!”
他猛地抬头盯着雨蝶,两只眼睛睁得像铜铃那么大,且布满了血丝,样子古怪而可怖。
“你知道有一座叫真皇观的道观吗?”他嘶声问雨蝶道。
雨蝶茫然地摇了摇头。
“你真的不认识西洋道瑞德?”仲甫又用他那灼人的目光在她脸上灼烧着。
雨蝶有点害怕地摇摇头。
仲甫颓然坐回床边的交椅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你知道有人把你当圣女吗?”
雨蝶似乎听过这个名称,在新婚之后的一天,孟颛小心奕奕地抱着她,在她耳边说道:“你就是圣女,我能成为你的夫君,那我也就是圣人了!”
她曾经问孟颛为什么叫她圣女,孟颛神秘兮兮地摸了一下她的肚子,还贴在上面听了一会儿,说神圣不可侵犯,我还是谨言慎行为好妙。
“这是一个阴谋,他们把你当作圣女,安排我们结合,这都是阴谋,显然发目标就是你。”仲甫好像是在对雨蝶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雨蝶看他这样样子,有些害怕,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她不明白仲甫究竟在说些什么,以为他还不能接受顶替兄长与自己合弦的事实,因此心里有些悲苦。
随后几天,仲甫在青龙城里逛来逛去,要么独自踏雪访梅,要么带着家丁凿冰捞鱼,找一些乐子。有时又眼神呆滞地蹲在小河边,自言自语。
他开始喝酒,喝很多的酒。
他本来是个不喝酒的人,他瞧不起那些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家伙,觉得他们缺乏理智,讨厌他们喝醉后洋相百出的样子。
现在他也常常把自己灌醉,趴在杜康楼里就睡着;有时朦朦胧胧的,就跑到聚春阁找紫月,但无论紫月怎么施展魅力,放出十二分的努力引诱他,最后结果都一样,他举不起来。
折腾过两次之后,仲甫终于无奈地面对现实:他被女人彻底抛弃了,他的余生将在黑暗中过着老鼠一样的日子,因为青龙城容不得像他这样的人。
宿醉未醒,仲甫颓丧地躺在床上,雨蝶坐在一旁忧虑地看着他,还让侍姆煲了一碗汤给他暖胃。
格兰城宫阙中的那一夜又浮现在仲甫的脑子里,他恨自己当初为何丧失了理智,一个人跑到烟花巷去,如果好好呆在船上,后来的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他就不会发现自己身上的秘密,也不会在海盗肆虐的时候临阵脱逃!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海盗!孟颛可能就不会死!总之,一切都是自己丑恶的欲望引起的!
但他也意识到,他肯定是掉入瑞德设计好的陷阱里了。他后悔邀他去南洋,后悔在发现真皇观与雨蝶的联系之后不去告诉家主。可当时瑞德是赵氏家族的再造恩人,谁会对他产生这样的怀疑呢?仲甫终于明白,瑞德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心理,并且可能早就窥出那些隐藏在身体深处的秘密,才会有如此周密的计划。
现在,仲甫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他不能再充当任由瑞德摆布的棋子,他要把真相告诉家主。
他挣扎着坐了起来,轻轻叫了一声“娘子!”这是他与雨蝶成婚后叫的第一声娘子,雨蝶听了,心里百感交集,但毕竟已是一家人,她还是有了几分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