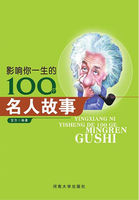墨绿色的天空仿佛又裂开了一条沟渠,涌进无穷的风,乖张出飞扬跋扈的流年鲜为人知的真相,等到渐渐看清了,才发现那些从头顶爬过的道貌岸然早已经密密麻麻地遮了所有光。
槿轩望着我的眼睛,似乎也感觉到了股没来由的悲伤。她故意提高了音量说:“洛曦,来吧。我来教你玩个游戏。”
“是什么?”我说。
她嘴角拉起淡淡的弧形,“洛曦,这是个神奇的绝谷。只要把自己的心愿在这儿大声吼出来!所有的愿望都会一一实现的!”
风仿佛将她的声音拉得无限漫长和浑厚。
“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
“是的,亲爱的王子。”
我惊骇地望着她盈绿色瞳仁,原来他们都知道了。
如果可以不后悔。
如果可以不忧伤。
如果可以不假思索地想象。
“我希望哥哥还能同以前一样,低头冲我做鬼脸叫我起床,对我说:再不起来我就打你屁股!”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即使头顶上的黑幕散得很重,父王也不再命瓦洛叔叔找我回去。而哥哥依旧早出晚归。
银月堡的小公主,有着世间最为锐利的眼神和忧伤。第一眼见到她时就这么觉得。
她比我略小几岁。
当父王还很健康的时候。赤骨叔叔就常带她来玩儿,她总羞涩地躲在她父亲后头不敢出声,眼神锐利地望向我。
到后来渐渐熟悉了,她也不再那么的拘谨,偶尔还会从赤骨叔叔后面探出个头冲我笑,眼神依旧锐利。
烟花城在我眼中也慢慢变得狭小,到处都是些拉拉扯扯的人群。在那样的夜里,我意外地看到了槿轩,穿过逼仄而森然的小巷,擦着黑秃秃的冰冷的墙,拐过七八个弯,脚步仓促而紧张地跟着她。
这就是哥哥让他们远离我的原因吗?然后我看到颜锁从里头跑出来,槿轩温暖地朝他笑。风从高高的地方打下来,划破了尚未痊愈的脸颊。
因为这儿同槿轩的性格完全不同,阴冷,灰暗,潮湿,肮脏,阴霾的气息恍若足以决堤的浩瀚洪流。
这里是烟花城最低贱的地方——贫民窟。
她问过我,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是否是就该尊重命运的安排和摆布。如果说出生高贵是福,那出生低贱是否该称之为“祸”。
幻想没有足够伟大到与现实抗衡都是没有意义的。
父王告诫过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永远不要对别人的世界妄加评价,甚至是揣摩。
我那时一丁点儿也不明白。
只是觉得“做梦”是一件相当费神的事情。
因为很小就开始不断重复一个看似没有结局的梦。在梦里我总能自由地与风驰骋,像是背负了一切以快乐的名义召集而来的悲伤,雀跃,激动,欢畅。可是梦里,却充满了不像以往的瑕疵,它铺上了层淡金色。
瓦洛叔叔说:“没有人能真正掩饰罪恶,即使是恶魔。”
当父王还很健康的时候。我依旧有许多不易甩掉的任性,比如生气会摔碎杯子,比如睡不着要听笑话。
瓦洛叔叔会给我耐心地讲解关于成为一名伟大的圣士该有的一切,对哥哥却生硬口气。
当父王第一次帮我和哥哥探视体内灵力时,他难以置信地望着哥哥。瓦洛叔叔说探视灵力其实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探视本身其实是用自身的灵力去包裹被探视者未知灵力的过程,一旦探视者的灵力亚于被探视者,则会给前者带来不可磨灭的伤害。并且这是门很难掌控的秘术,氏族中会的寥寥无几,瓦洛叔叔说他也无法掌控。
然后他看到哥哥冲他轻蔑地笑,像末日黄昏一样的欢笑。
当父王不再健康的时候,是探视完我体内灵力的之后几天。
当父王不再健康的时候。墨绿色的天空总有种湿漉漉的孤独。
当父王不再健康的时候。哥哥依旧早出晚归。
当父王不再健康的时候。我还是会在肮脏的贫民窟附近看到槿轩干净的笑。
当父王不再健康的时候。银月堡的赤骨叔叔就很少再带小公主一块儿来了。
面朝月光倾倒的城,父王泪眼婆娑地望着灰色花园,他说,他想念我母后了。
那时的哥哥同样泪眼婆娑。
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再年轻的时候,童年却可笑地没有结束。
灰绿色黏滑的天空仿佛也在嘲笑我的愚蠢,那一幕,是伴随着暖雨和苍鸟的不期而遇,黑风肆虐地划破脸颊,父王高兴时把我举过头顶,槿轩跟颜锁有意无意地回避我的眼神,还有哥哥不断地漠视等等平缓的事物一同存在的。
瓦洛叔叔艰难地从暴走的泥流里拽出哥哥,松开原本抓紧我的手。在被泥流掩盖视线的瞬间,他们淡漠的眼神组建了我念念不忘的过往。
灯红酒绿的舞厅外,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扶着杆子歇斯底里地呕吐。
灯红酒绿的舞厅内,有人歇斯底里地高唱: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没错。我是洛曦,凯葬尔地宫的二王子。请原谅我的刻意隐瞒,只因我想执意忘记。
“我笑着,天空明亮干净了,有一个声音在说,温暖得像阵风,黑色眼眸关切的白净国度,有我淋湿后失落的梦。”
“我哭了,世界模糊不清了,听到个声音在说,温柔得像阵风,苦涩泪水眷恋的甜蜜角落,有我淋湿后干净的梦。”
摩卡,我到底该不该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