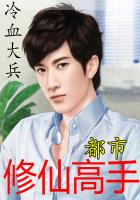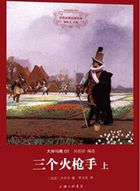临近傍晚的街道上没有落日下沉照射过来的余光,一如既往地不朝你看一眼道别着走了。路上行人也少了些,许是搁在家里饭桌头正盘算着今晚上哪消遣消遣。天气虽刮着风,也不至于太冷到像冬日里搓搓手。
余慢慢地走到店斜对面前的小槐树下,两只手窝起来,一手罩着另一只手点燃了嘴上的香烟屁股,深吸一口背靠在粗实的树根上。从鼻子孔里跑出的尾气带不走愁绪捎不来安慰,不知道他是在望着一辆辆驶过的互不避让的汽车,还是在脑子里自己个儿转着只有自己知道的脑筋。
白走了过去,借上了火便也陪着他杵在那。或许这无聊就是无聊,到哪都是一个味儿,不受人待见。
“都说忆苦思甜,我看你要思到什么时候,真要熬出个蔗糖来?”白看着这不发话的哥们一通调侃,“你倒是一副谁欠你就揍谁的架势,这眼睛眨得。快说说,我一定站旁边不出手。”
余卸下衔在嘴边的烟头,用无名指弹了弹,抖落烧过的烟灰。別过头,一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神情,“有倒是有,不过……”
“搞什么神秘兮兮的,谁啊?”白捋捋衣服口袋,不想让风把烟灰糊到自己身上。
余看着白,咧开嘴笑了笑,拿手指了指靠在自己旁边的男人。不曾想白反倒被捉弄了一番。
“你小子!”白笑着,捶起手便摆出个肘击的姿势。
倒是这余,避也不避,“任凭风雨满江去,独坐烟雨岿如钟”,直叫白想起刘邦的口头禅:为之奈何!
“你这脸皮也真是对得起厚颜这两个字,不知在哪修炼得道的。”白苦笑着说。
“终南山下,活死人墓。”余用背脊在树上一拱,稍有一反弹之势便重新直立起来,盯着白不紧不慢地回答。那纯洁无辜的眼神里仿佛在说:对不起了兄弟,哥练过。
“你……老实说,祸害过多少女生。”白自顾自地想吹个眼圈儿出来,刚一成型便被风打散。
“有些事,一个巴掌拍不响。”这脆弱心灵遭受过无数磨难蹂躏的的声音真想让人马上扁他一顿。那垂下来呆看着水泥地仿佛做错事情接受惩罚的眼睛好似又在说:真对不住,兄弟。哥,也苦。
白是受不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右手会自动地去抚摸面前这张犯浑的脸。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贼心贼胆一样小。”
“你错了,就贼胆。歪脑筋嘛……”
两个人说着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不知道手上的烟掉落了几回。
说起余雨这个人,原先也并不是进了大学就直接和慕白一个班。要说认识起来恐怕是在心理选修课上,当然其余哪里地方又打过几次照面这也数不得了。那时充其量也就过来借个火。白本以为自己是个神经妄想狂,没成想来了个狠角色,精神得让你分不清谁在妄想谁在现实。
尽管如此,他这家伙平日里也颇招女孩子喜欢,单且不说长得白白净净的模样,凭嘴巴上长出的三寸金莲就说得女孩子一下满脸通红一下心花怒放,自个儿又不小气,凡是能照顾到的地方都放得是开。照这样说也确实撩拨得这些小姑娘芳心暗许。
虽说小时候穷,亲爸也去得早,老妈倒是改嫁了好几回。没见过,倒也能想得出是个女强人。听说经营着好些公司,本想逐手让他接管了去,谁知他倒本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两眼一闭、恕不奉陪。去国外混个文凭嫌人生地疏,又懒得学外语,非要自个儿找个地填报志愿来读个不入流的大学。可就这一亲儿子,打不得说不得骂不得,好歹正经是个大学生,落下话来读完四年书再说。
至于说这打工的事,倒也不是说慕白拉他入的伙,相反还是余提起的,后来他那认真的样子也证实了他曾说的话——他在自己养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