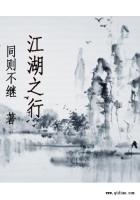哥哥走后第三天,她感冒受了风寒。
穆公任一走,她便开始收拾屋子,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忙了两天,第三天,终于闲下来,便生病了。
她生了一堆火,门口有风,她便把火堆移动到床前。她脱了衣服,光着身子烤火,这样才会觉得舒服。可是没多久,肚子“咕咕”直响。
已经来不及了。她披了一件衣服,匆匆出去。
一个人要到野外去方便,并不方便。
没有月亮,四周都是暗的。
回来的时候,身体还是难受,虚弱。
她是抱着一块烧过发热的石头睡着的。
-----------------------------------------------------------
第二天,他便见到了倚山宫的主事。
还有孙良。
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身材高大,圆脸,大眼,头发却是乌黑。他便是白曾青的师弟,李问道。
“两位小兄弟,我听闻你们前来,是为了拜师学艺的,不知道可否事实?”
“是的。还望前辈收留。”穆公任开口回答。
孙连也是同样答复。只因为他不想表现出奇怪的地方。而且也算是机缘巧合,若真的练好了功夫,下山了也便不再害怕别人了。
“我想问你们,为何想要习武?”
这个问题,穆公任已经想过很多遍了。“练好武功,以后在外行走,才安全。”
“也是,这世道险恶。”
“我想当一个大侠,替天行道。”孙良快人快语。
“嗯。那天下武林那么多门派,为何选了我星相派?”他知道,这两个人,绝非就近而来的。而且便是这附近,也有不少门派。
“因为星相派是武林一大派。白掌门又是武林盟主,天下敬佩。门下弟子又是门规森严……”
“好了,你呢?”他打断了孙良,但听他这么说,还是很高兴的。
“我听说的第一个名字,便是白曾青。所以我来这里了。”这个答案,他也很满意。而且,这也确是申有赖对他说起过的第一个江湖人物。
“哦,你是想找我师兄学武功了?”
“不敢。只愿意在星相派门下,练些功夫。”
“我倒是希望是他教我。”孙良开口了。
“你们来练武,家人同意么?”
“她同意,但也不舍得。我想早点学好功夫回家。”他的家人,只有式仪一个人了。所以他也只是含糊地回答了。
“我一家人都死了。就是因为一个人活着不容易,所以才想要练好功夫的。”
穆公任在一旁,虽然知道他喜欢撒谎,可是这回却露馅了:之前还说习武是为了做一个大侠打抱不平,现在又成了生活所迫了。
“练武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需要恒心毅力。若不能持之以恒,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如果你们只是想要练些功夫防身的话,可以和外门弟子练些拳脚功夫。”
“要做大侠,当然要学最厉害的功夫了。”孙良也没有想过,自己会真的来到星相派学武。但是既然到了这一步,就一定要学最厉害的本事。他甚至在想,如果真的能够成为武林盟主的弟子,说不定也有机会坐坐盟主的椅子呢。以前他没想过不敢想,现在却又太过大胆了。
穆公任不说话。因为他说过只是想要学点武功防身的。若这老人真的思路清楚,只是让他在门外练练防身功夫,便糟糕了。所以他反倒顺着孙良的话了。只是自己不开口。
“我星相派收徒很严,想要拜入门下,若非掌门师兄做主,我还要会合几位师弟才能开这仪式。你们看到那些弟子,很多是外门弟子,他们有些人在这里呆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可是一直都是外门弟子。没能升入内门。如是这样,你们也还要拜在星相派学武么?”
“内门,外门,有什么区别么?”穆公任问道,“一旦加入星相派,又要守那些规矩呢?”
“问得好。但也问得太早了。收不收你们,还难说呢。等到你们有资格了,自然会让你们熟悉门规的。我只问你们,你们要练功么?”
“要。”
“那好,潘盛,带他们下去。让他们从基本功练起。”
-----------------------------------------------------------
刚开始的两天,他们被安排挑水劈柴,打扫院子……总之都是些下人的杂活儿。穆公任知道,这是他们在试探自己呢。
“喂,你说那老头是不是坑我们啊。每天吃的都是青菜豆腐的,却让我们干这么多力气活儿。找人免费打工,也太精了。”
穆公任不说话,继续扫着地。
小时候,他也扫过地。可是自从出了村子,他便再也没有打扫过。
这种感觉,已经不是当初的感觉了。扫地,只是一个任务,一个工作而已。
不打扫了,是因为没了归属感,因为把自己当做了一个过客。一早便要离开的旅人是不会去整理客房的。
“喂,公任,你怎么不说话。你说他们不会让我们在这里扫上三年两年吧?”要真是这样,那这武功,他是宁愿不学了。
穆公任依然不说话。他有些火了,一把夺过穆公任的扫把。穆公任抬起头,直视着他。
“干什么?”
穆公任转身拾起了扫把,继续扫地。
“你这人,是不是傻了。”但是他又想起来,自己的身份,说不定还在穆公任的掌握之中,若是穆公任说出来,他当然是可以抵死不承认的,但终究有风险。所以便收敛了他那多嘴好事的性子。
“你这家伙,不要偷懒,赶快干活。”那个潘盛正好路过,呵斥孙良。
他嘟囔了两句,胡乱挥舞着扫把,地,根本就没扫干净。
-----------------------------------------------------------
穆公任依然记得,陈同也好,孙良也罢,都是劫匪。他虽然无法抽出刀来杀了对方,可是对他的怀疑警戒,却从来不曾消除。
没过两天,大家便都看出来了,这两个人,一个懒散,而且特别多事,一个踏实勤奋。每次挑水,孙良都会抢那个较小的水桶。
“跟他一起干活,都要吃苦不少吧。”有人也很同情穆公任。
但穆公任不想背后说别人,哪怕这坏话是真话,他也不想说出来。
他并不回答。
有时候,他比式仪更不擅长和人交流。更容易得罪人。
渐渐地,便没有人愿意自讨没趣地和他说话了。
穆公任也并不想和这些人说话。
“我说吧,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和他走了一路,他都是这样一副硬生生的面孔。”孙良和旁人说道。
穆公任即便是听到了,也装作没听到。他只会努力地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有机会,便去看看星相派的弟子练功。
这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李问道说起过,练武需打好基础,等过些时候,自然会选择一些基本的武学让他们开始练习的。
他也知道,现在只是一个观察期。
虽然如此,但是偶尔路过,还是可以趁机看上几眼的。
-----------------------------------------------------------
“新来的,你们两个把这些碗给洗了。”
穆公任知道,这些人是仗着自己来得早,资历多,便欺负新人的。但人在屋檐下,也只能这样做了。
还能怎么办?和他们打架么?自己是新来的,要是被人告了一状,说不定就会被扫地出门。否则以穆公任的性子,绝对不会忍受这种委屈的。
他只是感谢,感谢式仪不在身边。否则被她看到了,就该难受了。
就像母亲看到孩子受了委屈又无处申诉时候的心情。
“刚才不是让你们把院子里的柴给劈了么?”一个人跑到厨房里来责备洗碗的穆公任。
可是他一个人无法分身,每一次干活,孙良总会躲着。
“你,”看到孙良舒适的路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想说:你就不能过来干点活儿么?
可是他怎么能够去和一个坏人一起呢?
孙良装作不懂他的意思,跑去睡觉了。
“那个孙子,每次干活就偷懒,又不知道躲哪里去了。”那个颐指气使的“前辈”正在一旁监工。
穆公任洗完了碗筷,要去劈柴。可是突然又被那人夺走了斧头。原来是大师兄来了。所以他要摆一副用力工作的架势来。
“你是穆公任吧。靶场有几个木桩坏了,你帮忙去修理一下。”大师兄于冠中来找他。大家都知道,他手很巧。
这里,穆公任第一次那么近地看到那些人在练武。他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拳,也不知道是否很厉害。他只是尽可能地多记住几招。
“道成,你怎么这么笨啊。看清他们怎么出拳的。还有,最重要的是注意运气,要连贯。”有人在督促这些人练功。
这些人有的年纪三十多岁了,有的才十几岁。穆公任也不清楚,他们是否是同一辈分,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他们都在练同一套武功。
十几岁的童子,和三十多岁的中年人,都在同一个起跑线。
所以只要跑得快,十几岁的人,可是和三十多岁的人不相上下。
这便是差距。
这便是穆公任看到的希望。
这也是他努力下去,决心练武的动力。
“修好了么?修好了你便回去休息吧。”大师兄让他离开。他还是趁机再瞄了一眼。
回去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便躺在,在脑海里默练。
他也告诫自己,不要自作聪明地偷学,也许这一切都被人看在眼里。可是他还是忍不住。
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很多地方都看错了。
-----------------------------------------------------------
“起来了。今天我有点事,你们两个去厨房把碗筷给洗了,还有,锅里的水要添满烧开了。”这一次,那人指明了也要孙良去。
孙良虽然不愿意,可是见对方高出自己一个脑袋的个头,便只好去了。
“哐当”一声,碎了一个盘子。没多久,又打破了一个碗。穆公任都有些看不惯了,可是他才不要去帮助这个人呢。
而且他能够感受到,那是带着情绪在做事,所以才会这样失手。
他摔碎了四个盘子,两只碗。穆公任在灶膛边,看着他偷偷摸摸地将碎片都打包了,不知道扔到了什么地方去了。
他不想多管闲事。要真的被发现了,自己也只能撇开关系了:自己只负责烧水。他对孙良,并无需讲什么道义。
他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坐在一旁,看着灶膛里燃烧的柴火。期待着娘在那头做着饭菜。那是再也尝不了的味道了。
木柴遇到了火,除了化为灰烬,还有别的可能么?
-----------------------------------------------------------
“喂,吴胖子,你这碗洗了么?怎么这么脏?”几个弟子差点没吃吐了。
这是傍晚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当时穆公任也在。他很清楚其中究竟。
那个吴胖子,有苦难言。
碗盘是孙良洗的。
过后,自然少不了报复他们。
穆公任想要袖手旁观,可别人并不把他和孙良当做两拨人。
吴胖子的手下,有五个人。
穆公任若是正要动手,也未必会吃亏。只是他虽然恨这些人,也不能在这里拔出刀来和他们拼命。
但是孙良,却是真的在拼命了
他并没有什么武功,所以抓起碗来,便是朝他们头上砸去。
事情便传到了李问道的耳朵里。
-----------------------------------------------------------
“你们怎么刚来就闹事?”
“我们闹事?”孙良早就不想待下去了,正好借这个机会离开。“我们是来练功的,不是来给你们打杂的。我们来了半个月了,都只是给你们挑水劈柴扫地,这也不说了,连一个做饭的也要欺负我们。指手画脚,让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我受够了。”
连穆公任,也有一点佩服他的勇气了。
“他们毕竟早你们之前入门。便是听他们的差遣,做些事情,也是应该的。”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才是应该的。”反正不指望继续待下去了,他也放大了胆子。他不相信,这些人真的敢对他下手。
“每个门派,都把欺师灭祖犯上忤逆当做头等大罪,而且同门内斗,手足相残,每一样都是重罪。”
“是他们动手在前,我们不能不还手啊。”说完这话,他又看了穆公任一眼,心说穆公任好像还真的没怎么还手。就像一个傻小子一样。
“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来练武的,可是你知道他们几个来了多久了么?吴湛来了六年了,就因为没有一颗心,所以练不成功夫。之前我便告诫过你们,练武是要吃苦的。你们真的有这种准备觉悟么?”
“如果是为了练武,便是吃再多的苦我也认了。我现在是在练武么?我不学了。”孙良就要脱下衣服走人。
“站住。”这时候在大厅的,除了李问道,还有两个师弟何寻情、***业。出言阻止的,便是***业。
“你虽然还不是我星相派的正式弟子,但毕竟还得喊我一声代掌门。你今日在我倚山宫犯了过错,若是不加惩罚,我星相派的颜面何存?”李问道终究是一派之长。此时发声运功,也令两人心胆大震。
-----------------------------------------------------------
第二天,穆公任依然照常的扫地劈柴,可是不远的柴房里,透过窗户,两个人正气狠狠地瞪着他。
一个是孙良,一个是吴湛。
因为两人不肯认错,所以被罚了关禁闭一月,而穆公任默认有错,便没有关禁闭,只是三个人的活儿,都交由他一个人做了,挑水扫地劈柴生火烧水洗碗,除了做饭。
因为做了两天,发现他做得太难吃了。
虽然是不用做事了,可是看着穆公任一个人工作的那么累,却连眉头不眨一下,两人内心有些不快:自己被囚禁了,而他却可以自由的在外面。好像还很享受的样子,一点都不气愤。
毕竟,山里的师兄弟都知道了自己被关禁闭。而关禁闭则是更重的责罚。
但两人又互看了一眼,各自扭头,蹲在墙角去了。
一个来了六年了,还是第一次受这样的惩罚;一个只想着挨过了这一个月,便下山再也不练什么功夫了。
穆公任虽然要做很多事情,但也只能和他们两人一起,同吃同住。
“你倒是认罪了,还要干活。吃穿也和我们一样。姓李的是看不惯你没有骨气呢。”三个人站在白墙前吃饭,孙良笑话他。
穆公任不搭理。
“没骨头的东西。”吴湛更是讨厌他了。
“看你样子,还以为你也算是一个有担当胆量的汉子呢。”孙良找到了知音,便顺着话音继续戏弄穆公任。
“贪生怕死、没有骨气?这词你也配说?”穆公任吃完了饭,转身离开。
孙良吓坏了,就怕他说出了真相。破庙里的事实。显然他是清楚的。
“你们还有故事?”
“你别以为他很老实,其实是个骗子。这一路上,有个叫陈同的伙伴……”孙良突然转头看了吴湛一眼,不再说话了。
两人分明是仇敌的。
-----------------------------------------------------------
第三天,穆公任在劈柴,看到那头人群簇拥着,好不热闹。
可是他讨厌这种热闹,不知道这群浅薄的人,又是因为什么事情而欢呼雀跃。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想去凑热闹,只是用力地挥舞着手上的斧头。
看着那些人,蜂拥而去,他便觉得可笑。
他那么孤僻,没有同伴,而且又是受罚期间,没人敢靠近他,所以不会有人告诉他,掌门回来了。
-----------------------------------------------------------
他是第二天恰巧听到弟子聊天的时候,才得知的。
只是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机会见到白曾青。
他见识过李问道的本事,但感觉还比不过申有赖,却不知白曾青究竟如何。
他幻想过很多次,很多种不同的见面方式。
但他却没有想过,可能自己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他。
“听说盟主回来了。”不知道为何,关在柴房的孙良,竟然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可惜我们是没办法见到他老人家了。”吴湛说道。
“急什么,一个月很快就过去的。”虽然是有仇,可是每一天都只能对着一个人,总会有言语交流。而且孙良,是那种情绪过去了,便过去了的人。
“掌门可不一定能待一个月呢。”
“你怎么一直都不说话?难不倒不想见盟主么?”发现穆公任一直躺着不说话,孙良觉得奇怪,“是不是你早就听说了,却不告诉我们?”孙良很不满意。这样才可以解释穆公任的无动于衷。
虽然那只是穆公任的性格而已。
穆公任依然不说话。孙良算是明白了。“你这人就不能说两句话么?你倒是有机会去看看他。反正你还能走动走动。”
他们三个,都被罚只能在柴房吃住。穆公任的区别,只是白日可以出来劳作。曾经在孙良看来,那只是更倒霉的惩罚而已。但现在,却又成了一种优势。
-----------------------------------------------------------
但是他不能。
因为他还穿着受罚的衣服。
因为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天,整个山脚,就好像空无一人了。空荡荡的,只有穆公任的劈柴声。
柴房里,还有两个人猜拳的口令声。
柴也劈完了,他拿着水桶去打水,发现两人关系倒是近了一步。
路上,他好像听见了喝彩声,是从校场传来的。
好像是打斗,是演武吗?
水,倒满了六口大水缸。他又拿起了扫把。
他也不知道,明明地上并不怎么脏,为何要不停地扫。现在的他,就和孙良扫地那样,心不在焉。他在偷听着远处的声音。可是太远了,除了偶尔爆发的掌声和喝彩声,他什么也听不到。
“你这么想去看看究竟,便放下扫把去看看咯。”在柴房门口的孙良,一眼便看出了穆公任的心思。
既然连孙良都能看得出来,又岂能躲过别人的眼睛?
穆公任还记得申有赖的告诫,一定不要自作聪明。所以,他抓紧了扫把,用力的挥动着。
之前便有人告诫,让他在这里好好工作,别到前头正场去。虽然他不确定,这是否便是星相派几个前辈的意思。
院子里有一棵大树,水缸粗细,他抬头看了一眼,差不多有十来丈高,虽然大冷天,可还是枝繁叶茂的。
他放下了扫把。如果爬上去,也许可以看得到那头的情况的。
但他没有爬上去,毕竟柴房里的两个人也看得到。他只是靠在树上静听。
只能听到风过叶动的沙沙声。
-----------------------------------------------------------
“真可惜,你这么厉害都没能入选。”
“对啊,分明就是你占了上风的。”
“好了。掌门肯定有自己的打算的。”被几个师弟在耳边唠叨,那人烦了。
“也是,连大师哥都没能入选。”
“你懂什么,选上了未必就怎么样,没选上说不定才会有重用呢。”
“怎么说?”
“我就随便一说。”
“不过灵泰倒是很厉害。”
“嗯,另外一个小鬼倒是赢得很侥幸呢。”
“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连道成也进去了。”
“是啊,我也想不通。你们说这掌门是怎么回事?”
“别胡说。”一个入门较早的弟子制止了他们的谈话。这种事情,若是被旁人听了去,告密了,可就不好了。他们是指穆公任。
穆公任都听在耳里,他们似乎是在谈论白天发生在校场的比试。可他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反倒是柴房的两个人,从旁的人那里听到了更多的消息。
掌门白曾青想要挑选一批弟子进入内门,修炼本门不外传的功夫。所以才有了这样一场比试。
吴湛说完,很是不甘。这已经是他来这里的第七个年头了。他依然没有办法加入,甚至在外门,也只练了些粗浅功夫。
不过孙良便无所谓了,反正已经决意下山了。他可不愿意再受人欺辱。但是想到这里,想到和自己有仇之人,便躺在自己一侧,那股痛恨,却又淡了几分。
只有穆公任,虽然有满肚子的疑问,虽然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可是始终不曾拉下脸来,向吴湛询问。
外门都传些什么功夫?如何选拔弟子进入内门?这是常例么?一年便只有这一次么?每次都是白曾青亲自挑选么……
-----------------------------------------------------------
第二天,穆公任在干活儿的时候,便听到了有些弟子在抱怨,因为那些幸运的师兄弟被选上了,现在说不定正在接受白曾青的教导。而他们,则没有这个机会。
而那些被选上的,并不一定是因为昨日比武胜出。有些人甚至是比输了的。
“其实掌门就是在挑他喜欢的人。”
“咳。”是潘盛。
大家收了议论。
他只是路过,检查工作的。
-----------------------------------------------------------
但是又过了一天,他们在面壁吃饭的时候,有人来了。
“墙上有什么?”背后一个声音。
但显然不止一个人。穆公任听得出脚步声来。他发觉最右侧的吴湛,似乎有些始料未及,连手里的碗,都差点落下来了。
“掌门。”
-----------------------------------------------------------
穆公任也回头,人群当中的那个人:就是他么?
他盯着,非常失礼的盯着。
这个人便是申有赖口中的唯一对手么,那个武林盟主白曾青?
竟然普通得和村子里上了年纪的人一个样子。
眉宇、眼神都那么普通。
和身旁的三个师弟,李问道、何寻情和***业相比,更显平庸。没有一份威严,一份飘逸,一份内敛。便是和申有赖相比,也少了一份专注孤僻。
简单地说,更亲近。
“你们俩个,是刚来的?”
“是。”孙良回答。
“你是孙良?你们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们都想要学武。哈哈,算了,你们先把饭吃完,等一下到树下来见我。”
-----------------------------------------------------------
三个人扒了几口饭,赶了出来。这时,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弟子。
他们发现掌门过来了,自然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少人还以为掌门要惩罚他们呢。
三人过来,他们自然地让出了一条道。
穆公任远远便听见,白曾青和弟子的交谈。
“那你的武功学得如何?”
“我资质不好,学了五年,只学了一套学了一套拳法一套剑法和一套内功法门。”这个弟子所说的,乃是星相派的三大入门功夫。
“这卫止拳法包含方圆动静攻守的分别,讲求转化随机应变,光靠师父传授自行练习是不够的,你们要多和师兄弟切磋,思考得失,才能精进;这行意剑法,口诀上说重行不重意,但意在行之中,意在行之外,有行而无意,无行而有意,你们无需领悟,只需常加练习,这套剑法看似零碎断裂,你们只要能够练到连贯了,也就差不多了;周恒心法便如这周天星宇,你们可以自行对比。这三套武功,虽然是我派入门武学,却包含了身心意。大家莫要以为是基础,便放松了。”当白曾青点评之时,莫说周围的弟子,便是几个师弟,也是聆听受教。“好了,你们先散去吧。”
因为他知道,他们三人已经来了。
“你们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吴湛,你来了有快七年了吧。你学了卫止拳法,可是我禁止你与人比试;你学了行意剑法,可是我禁止你用剑;一套内功心法,我也只让人传你一半。”
“掌门。”
“说。”
“我觉得,那已经是一整套心法了。”吴湛不清楚,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但他只有一搏。
白曾青笑了。“等你找到了另外一半,也就学成了。好了,你们两个呢,这些日子又学了什么?”
“我没有资质,所有只能练习扎马步。”孙良说的当然是气话。
可是白曾青却并不生气,继续问穆公任。
“你教什么,我便学什么。”
白曾青笑了,“好,你们既然都心有不满,那很好。我星相派有三大武学。吴湛,你便去学《六壬无方》,孙良可去学着《太乙生水》,穆公任便随八师弟去修《奇门遁甲》吧。三位师弟,就麻烦你们了。”
“掌门师兄,可他们都不是内家弟子。”八师弟***业提了出来。但是被白曾青出手给阻拦了。
无妨。
但是白曾青也没有列他们入门。
穆公任心说,莫非这奇门遁甲是什么阴阳术数之类的书么?那自己可不想学了。而且他不愿意终生困在这里。他只想练一身武功,然后回去。要是真的练成了武功,他们不放自己离开,真的和申有赖所说那样,非要废了自己武功可就麻烦了。
“我是万万不敢的。”穆公任赶忙回答,“我还有家人在,只想练好一身本事然后回家的。这奇门遁甲既然是星相派的绝学,我是万万不敢学的。”他并不想成为星相派的弟子。如果一定要选,他宁愿是外家弟子。
“你们大可以试试,学成也罢,不成也罢。都无所谓。你们也不必为此加入星相派。”白曾青这话一出,传业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可以?可是看五师兄,寻情却没有说话。
三师哥李问道也未说话。
“好了,犯了错还是要接受惩罚的。除了练功之外,一个月的禁闭还是要关的。该干的活,也还是不能落下的。”他拍了一下穆公任的肩头,起身离开了。
远处,还有弟子在“无意偷听”,没想到掌门竟然会让他们练习这三种武学。而他们三人可能并不清楚,这三种武学对于星相派的意义。
“对了,那面墙,你们看到了什么。”白曾青突然转头问他们。那些偷听的弟子,也刚好找机会跑掉了。
那本是一面白墙,不知道多少年过去了,已经变得肮脏了,但什么都没有,连一个字一个笔画都没有。
-----------------------------------------------------------
白曾青离开了。
而三个师弟却慢走了一步。
他们也不知道,为何师兄这次有如此举动。
“师兄为何会把镇派武学教给他们三个外人?”***业还是不太懂。
“是外人就对了。”何寻情似乎有了想法。
“是啊,师兄传他们武功,却不纳他们入门,这才是该奇怪的地方。”李问道也说。
“你们打什么哑谜啊。”***业可不喜欢猜来猜去。
“你觉得他们能够学得会么?”寻情反问了一句。而且掌门师兄对此应该很清楚的。
所以师兄的目的,并不在这里。
“那可说不准。你们忘了师父么?”
他们四人的师父,是元经天。上一任星相派掌门,上一任武林盟主。
-----------------------------------------------------------
他们都离开了。只剩下那些弟子,聚在一起,说起了刚才听到的话。大家对他们三个是又羡又妒。这三套武功,乃是星相派的镇派武学。这些人当中,便是内家弟子,也没有机会修习,可是他们三个却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第二天,他们便各自找自己的师父去了,只有穆公任晚了一步。因为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做完的时候,已经中午了。
他这才赶过去,***业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那是一间简陋的房间,里面生有一盆炭火,他刚进来,便感觉一股热气。
他要学的是《奇门遁甲》,但是这似乎不像是一种武学。小时候,他便听他爹说起过这个词,后来又在和算卦的那个怪老头那里听得一些方术,也就包括奇门遁甲。他的印象里,那更像是一种术数神通。
“你识字么?”他开口便问。
“识得几个。”穆公任刚迈进来了。
“这几个字怎么念?”
“蓬……”第二个字,他便不认识了。
“芮。继续。”
“冲,辅,禽、心、柱、任、英。”
“见过北斗七星么?”
穆公任摇了摇头,抬头仰望星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在北天上,有七颗星排布成斗勺状,称作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和摇光。”
你看,前面四颗星星,就像弯弯的勺子,叫做斗魁,魁就是首,是前头。后面三颗星星,就像勺子的柄,所以叫做斗柄,或者斗杓。这星星永远在北边,以后出去找不到回家的路,看了他就知道方位了。
穆公任的脑海里,唤起了儿时的回忆。那是他还躺在爹娘的怀里乘凉的夏夜里。凉风习习。式仪还没有出世。
“这北斗七星,又有另外的名字。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再加后面两者之间的右弼、左辅,合称九星。也就是你刚才念的。”蓬、芮、冲、辅、禽、心、柱、任、英。
但这有何意义呢?穆公任不敢开口询问。
“那这几个字呢?”他又打开了一卷纸。
“这是天干地支。”
“这个呢?”他又展开了一张纸。
“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他好像听过。
“这是八门。诸葛亮便依此布置过八阵图。见过算命的么?”
“见过。”穆公任点点头。
“那这个呢?”在房间里,有一支架,上面有一圆盘。是一个原木的截面制成的。***业将之翻转,穆公任发现,这原木一吋厚度。背面上写满了字。有八卦八门九星天干地支……就像是一个罗盘司南一样。
穆公任觉得有些眼熟,却又不敢说见过。也许在算卦的怪那里见过,像一个命盘。但他并没有多少印象。
“砰”的一声。
穆公任吓了一跳。
***业一掌打在木盘之上,顿时木盘便碎成碎块。
滴滴答答的,碎片掉落地上,还弹起来,敲击着,发出响声。最终全都躺在地上了。
穆公任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何突然生气了。
但是他并没有生气。
“奇门遁甲,奇,乃天干的乙丙丁三奇;门,乃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将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甲隐遁在戊己庚辛壬癸六仪之下,就是遁甲的意思。其中变化繁复,难于穷尽,你方才说识字,这里有一本书,你自己看自己琢磨吧。还有,这地上的木块,把它们给拼接起来。”说罢,便离开了。
桌上的几张纸,也都被扔到炭盆里,焚烧殆尽,不留痕迹。
穆公任绕过炭盆,发现遍地木块。他拾起一块,上面有一个“艮”字,他有印象,那是八卦之一。然后又翻了另外两块,木块正中间正好写着“伤”和“冲”二字。他发现,每一块,都那样的整齐,一块,便正对应一个格局,一个符号。
一块块,绕着树轮圆滑地裂开。但横断处,才最见功力。穆公任知道,他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厉害得多。
落在地上,碎成碎片的,就好像是整个世界。那样的复杂。难于琢磨。
这本书,有很多字他不认识,不明其意。可是***业已经离开了。他只能自己钻研。实在无法理通,想起妹妹读书时候的方法,将之作为一个符号带入理解。
花了一整天,终于在日落前,将这命盘给拼好了。
他的肚子已经饿了,可是却不敢离开。
***业回来了,看了一眼,衣袖一拂,拼好的命盘又散落一地。“重来。”
穆公任拼好了,对照那本书里的描写,应该就是这样的。但他不敢确定。而这时,他又来了。并且再一次打散了一地。“重来。”
他想不明白,哪里有问题。但好像还是和第一次一样,没有差别。有问题么?他找不出来。所以还是同样的命运,没有差别。
一连五次,天已经黑了。
眼见他走过来,穆公任知道,同样的事情,又要发生了。
“哪里错了么?”他相信纵然错了,也不会全都错了,也不至于非要全都推倒了重来的。莫非也和林大夫那样,是在耍我考验我么?
这是第七次了。他左手一推命盘又碎裂了、衣袖一卷将之收入袖口,然后纷纷抖落入炭盆内。“这天地间没有对错,只在于你是否愿意接受,是否要去改变。没有一盘棋是重复的,看你要怎么下了。好了,今天便到这里了。”
他挥手让穆公任下去。他根本就不想教他。他不想让一个外人去窥测自己门派的最高绝学。这里面的步骤演化,是推陈出新的基础。他并没有让穆公任去推演。
-----------------------------------------------------------
穆公任回去了。
他的肚子早就饿坏了。
“给你留了饭。”孙良开口。
吃过饭,天快午夜了。
躺下,穆公任不知道那个“师父”究竟想要教自己什么。
“你今天都学了什么?”
“拼罗盘。”
“那是什么?”
“我也想知道。”
“那妳呢?”知道从穆公任的嘴巴里也敲不出更多的东西了,孙良又转而问吴湛。
“师父他教我一套掌法和一套步伐。”
“什么掌法,什么步法?”
“六合掌法和零星幻步。”
天已经晚了,又都躺在床上了,否则孙良是一定会让他演示一番的。
“那是内门弟子修炼的功夫。”但也算不得多神秘的功夫。吴湛也不知道,这和《六壬无方》有何关联。不过他没说,李问道还让他学了一个功夫: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一心二用。
“你们都没什么意思啊。”孙良说起了自己一天所学。“我师父的轻功可真是厉害呢。在林子里飞天遁地,没有什么是他抓不住的。鸟儿落在他的掌心,都飞不起来。树叶放在掌心,掌心朝下都不掉下去。他在林子里放了很多鸟,让我闭上眼睛去听有几只。”
穆公任心说,难道是要教你听声辩位的暗器功夫么?他学的应该是《太乙生水》。
在樊南山,穆公任是见过申有赖的暗器武功的。他能够听见一只蜘蛛沿着蛛丝垂下,能够听到一只毛虫吞噬咀嚼嫩叶,能够听到动物释放毒气的声响。这样才能听声辩位,有的放矢。
-----------------------------------------------------------
第二天,他们还在睡觉,穆公任已经开始干活了。穆公任水缸的水都装满了,他们这才醒过来。发现天还很早,院子他也已经打扫好了。
他们二人洗漱好,吃了早餐,便去学武了。可是穆公任却还要把院子里的一担柴给劈了。
“对了,山下菜地里还有一担柴。”潘盛过来告诉他。
因为穆公任这个才刚来不足一月的新人,竟然能够有机会学镇派秘籍,大家当然是嫉妒了。少不了要刁难他。
他只能加快劈柴的速度。
“记住,劈好点。别太大了,也别太小了。”太大了不好烧,太小了又不经烧。
穆公任只是点点头。自从爹娘死后,他变得沉默孤僻,很少和人说话。可是在师兄们看来,这是足够嚣张自负的表现了。潘盛离开了。
他赶着去菜地里担柴。有一个弟子过来帮忙。
“昨天我师父都教了你什么啊?”那人,原来是***业的弟子。
“看书。”
“什么书?”
“《奇门遁甲》。”
“这本书啊,我好像也看过。你没骗我吧?”那个弟子将信将疑。
穆公任没有再搭理他。他知道,那人不过是想要从自己这里打听一点东西而已。根本并非出自好心。
他继续劈柴,可是发现斧子不见了。
他能感觉到旁边的人,在嘲笑。虽然装作根本没有在意自己这头的情况。
“大家快走。掌门让大家去操场呢。”有人来和他们打招呼,这些人急冲冲赶去了。
在草丛里,穆公任终于找到了那把斧子。
-----------------------------------------------------------
当穆公任赶去练武的时候,看到操场那头,不少弟子在练武,有些在比试,有些人围观者,盟主白曾青便在一头点拨讲解。
他想停下来多看两眼,可是他知道,自己早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他要赶去书房。
***业见穆公任来了,也不责备他来晚了,只是让他读书,自己则出去了。
穆公任心说,早知道路上就多待会儿了。
一天,便这样的过去了。***业只教了他五个字。生生硬硬的五个字。比他爹教他的时候要不耐烦得多。
只是他只能专心地去学。哪怕不知道所学何用。
-----------------------------------------------------------
夜里,三个人又交流起了白天所学。
孙良依然是在山里,靠着耳朵去听声辩位,用手去抓林子里的飞虫;而吴湛,也只是继续练习他的掌法和步伐,以及一心二用。
第三天,没有人再去找穆公任的麻烦,因为这些没能入选的弟子,这次也有机会能够得到掌门的点拨,所以都早早地赶去了操场。
穆公任看到了那个弟子,叫做道成的。他是路过柴房喝水的。他比自己还小些,似乎并不怎么聪明。而且不少弟子对他能够进入内门都有异议。
为什么白曾青会看上他呢?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么?穆公任虽然有些好奇,可现在的穆公任也不想和人靠近。
做好了工作,他要去练武。
可是练习的内容依然是读书。
一连五天,穆公任都在看书。看一本其他弟子也都看过的书。
穆公任很怀疑,这是否真的便是那所谓的《奇门遁甲》的武学秘籍。莫非和白曾青教导吴湛一样,给他一本错误的或者残缺的秘籍,让他自己去领悟?
他翻过这本书,并没有缺漏。以他的本事,自然是没有办法从书的内容看出端倪的。如果那个写书人在就好了。
他有很多机会的,除了他爹和怪,大夫那里,申有赖那里,都有书,都可以看。可是他并没有认真过。奇怪的书,他也见识过。但从来没有深究。
在他烦躁的时候,另外两人,似乎都有了进步。孙良开始是闭上眼睛,去听何寻情在林间穿梭的声音,判断他的位置,而且也开始练习行星掌力。偷懒的他,都会练得一身是汗。而吴湛则开始连续爬山。是倚山宫附近最陡峭的一座山。一天都要上下好几个来回。手磨起了泡,鞋子也破了。
穆公任每天都睡得很晚起得很早,躺下了便睡着了。睁开眼睛便爬起来。他很累。
他担柴的时候,吴湛开始生火做菜,是四个铁锅同时生火,而且有李问道在旁看着。一条细长的竹竿不时敲打着他的手臂。就像在练习翻炒功夫一样。他去挑水的时候,也看到大冷天的,孙良凫水,而且何寻情便在身边。偶尔会投出一枚石子,落入水中。他便在水里去找寻。
但穆公任依然只能是读书。
吴湛是用锅在炒石头,孙良是熏坏了眼睛下水的。而他只是看书。
孙良已经开始练习行星掌力,并且学习敛气,也听过无中生有、以风化水的武学道理了;而吴湛也学习将六合掌法与零星幻步融合,一心两用,学习出掌的原理。
“我算是知道之前练功的意义了。”吴湛很是高兴。“虽然我手法再巧可能被人看破,但只要脚法无从琢磨,对方依然不能阻止我的攻击。”爬山,便是练习他手脚并用。确切的说,是下山。这才是最主要的练习。
他是闭着眼睛摸索着爬山下山的。
“你呢?”穆公任问孙良。
“师父不让我再多说了。”显然,何寻情也知道这个弟子太多话了。“而且,他也不让我叫他师父。”
虽然是如此,但是从孙良的表情,还是可以知道,他肯定是有所收获了。他已经不再提下山的事情了。
他要习武。
-----------------------------------------------------------
又过了一天。
吴湛却不说话了。
“你怎么了?”穆公任内心迫切,想要知道他们两人的进展。
“我以为这《六壬无方》乃是将两套功夫融合。可是我猜错了。今天,师父才教我真正的六壬无方。”
穆公任说起他看过的一本书《六壬九天课》,但是吴湛说,李问道说过,这武功无需知道太多庞杂道理,心意所到,无师能通。
“上下左右前后,称作六合。两相对立,犹如阴阳。但有阴自有阳,是不需要你一心两用的。我让你一心两用,是要你学会身心一体。这套武功可以让对手身心俱毁,但是元神不存,也会让自己身心俱毁。所以不能有杂念。现在我教你第一段,看清楚。”吴湛还记得李问道对他的教导。
穆公任并没有开口,但是孙良却也开口了。“你们找个师父也是够倒霉的。我就简单了,练武都不需要思考。昨天让我熄蜡烛,今天让我和他交手。”
“你?”连吴湛也不敢相信。他竟然到了那种程度。
“你想多了。我虽然练的是掌法,可是比得却是剑法。”
但他的这个说法,让另外两人更感吃惊。但是吃惊的还在后面。
“他用的是白刃剑,我用的是柳条。”
“那你能赢?”
“只要我的柳条断了,便算我赢了。他还说明天,要和我比掌了。那妳呢?”他又问穆公任。
“还在读书呢。”
“那可要抓紧了。”孙良盖了被子。“过几天,掌门就要考验我们的。”
这个消息,也只有何寻情才对他说起过。另外两人都不知道。
-----------------------------------------------------------
想起他们两人所学武功,和这些术数之间并无多少联系,又想起有一个弟子曾经说过,他所读的书,其实其他弟子也曾读过。他开始怀疑,***业是否真的有心传授他武功了。
***业自然是不希望把镇派武学传给一个没有入门的弟子的。
纵然知道师兄的目的,不过是要考校三个师弟的本事,可他依然决定这样做。
他不想做掌门。
所以当穆公任迟到了,他并不生气;当穆公任表现出不耐烦的时候,他也没有责备。
“师父,我想学武功。”
“这本书,你真的看懂了么?”
“看不懂的地方,我再花更多的时间,也还是看不懂的。”
“可是你真的想过么?为何乙丙丁称作三奇?八门如何开合,如何演化?六甲六仪,如何隐遁……”
为了选择乙丙丁作为三奇呢?好像是涉及五行生克的道理,他在怪那里听说过的。八门如何开合,怎么走呢?他好像听林大夫说起过不同走法有不同结局。遁甲,六甲,六仪,如何隐遁?中州的那个伙计胡吹海侃时候也说起过变化多端。
只是听着神怪玄乎,他并没有在意。
如果真的相信那些话,相信那些道理,那些运行规律,就像那个命盘,绝非一成不变,他要做的,不是复原它,也不能穷尽其变化,而是不问其然而知其所以然,顺势推演。
“还有,你并未拜师。”
所以,他还不算自己的师父。所以他可以漠不关心地离开。
穆公任其实更高兴。他根本就不想叫别人师父的。
-----------------------------------------------------------
想要推演变化,这并非他之所长。他的手里只有一本书,只能到里面去寻找答案。
***业吃饱了,看着穆公任在思考,似乎颇多不解,却显得很高兴。
穆公任装作借光,稍稍将身子扭过去。
“我从未见你画过一张图。”***业铁钳一抖,一块木炭飞了过来。他伸手接住了。
但是炭火并没有熄灭。他马上就被烫得把木炭丢了出去。
穆公任是看出来了,他根本就不想教自己。
他没有再画一张推演图,他宁愿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劈柴挑水。
甚至在路过操场的时候,看看白曾青如何教导弟子的。
所以当大师兄于冠中让他去锄地的时候,他反倒没有一丝情绪。
***业大部分时间都在这房间里,却很少教导他。穆公任不问,他便自行打坐。
穆公任甚至想过,掏出墙上挂着的剑,给他一剑的。
书在桌前,而炭火就在身旁。他可以付之一炬的。
他可以装作失手。他相信***业也不会生气的。因为那根本就是一本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书。根本称不上什么秘籍。
但他想起了那一次,他烧书,妹妹因此汤伤了手。
所以他忍了。
直到那一天。他突然开口对穆公任道:“你觉得我没有教你。怪我。但是这套武功,本来就没有招式,甚至和另外两套武功相比,也都没有运功法门,却可以任何招式都为其所用。这便是我不曾教你任何招式的原因。招式的推演转化,是活的,不是传授的。”
“学得怎么样了?”是白曾青过来了。
穆公任明白,只是因为白曾青过来了,所以他才说了那一番话。否则,他根本不会教导自己任何东西的。
“还在学。”穆公任自然是不能说他坏话的。
“明天早上,你先到操场去。”
不然,穆公任是要把工作做完的。
“我想考校你们三个一番。”
***业知道,这个“你们”,并不是穆公任,而是自己。
-----------------------------------------------------------
累了一天,他终于可以早点回去休息了。
他很久没有洗澡了,虽然天有些暗,他还是偷偷一个人溜出去洗了个澡。然后早早地躺下来,静静地,思考着什么。
连另外两个人的聊天,他也都没有听到。
“不知道这些日子学的武功到底有多厉害。”孙良除了和何寻情比试过外,还没有真的和别人交过手呢。
“我也想知道。到时候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说话的是吴湛。
“比拳脚还是比刀剑呢?”孙良有些在意。
“拳脚吧?”吴湛至今没有用过刀剑。
“拳脚的话,我觉得我会吃亏。”孙良一直都很油滑。“你个头那么大。我可很吃亏的。”虽然是这样说,可是何寻情早已经给他分析模拟过这些可能性。
虽然是孙良自己的要求,不过不论他怎么说,何寻情都答应着。
吴湛尴尬一笑。他只是怕用剑伤了人。毕竟,刀剑无情,还不像拳脚那样可以收发随心。
“你怎么不说话?”
但穆公任已经睡着了。
凉凉的夜,微微的光,风刮来,一股清晰的气息。
翻了个身,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