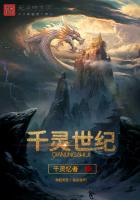明灭不定的光芒,被一少年人徐徐按在掌中,透过手指间的缝隙,白色的光芒中发出压抑的雷鸣。他的眸中冷光如电,“呵!”,脚下劲力一吐,烟尘腾腾,身体反若苍鹰般飞腾在练武场的半空。另一位中年人摆出防御的姿态,上受下合,是苍龙引水的起势,背后隐隐有虎啸之声。风云四起,忽然间,天空爆发一阵闪光,染得半个练武场一片茫然的白色,转眼间又恢复正常。那少年人的身影不见踪影,中年人严阵以待,左右四处扫视,却始终没有发现。正当台下观众议论纷纷时,天空轰隆一阵巨响,紧接着一道霹雳划破湛蓝的虚空,伴着天崩地裂般的响声,少年人身影显现,他手中的电光脱手而出,在空中划出一条轨迹,直取向台上中年男子的左肩。
此时正值初秋时节,天边残晖拂拂,层层如裂绯残帛。风自西山一路而下,排过练武场上众人,吹得衣襟咧咧作响。
练武场的演武台上二人斗法激烈,练武场的东边也有两人坐着观武。上首是个三十余岁的青年书生,锦袍玉带,面若朗日,他左手握着半卷金属质感的书卷,面上生辉,神情甚是得意。下首是个五十左右的清瘦老者,粗衣短打,面色铁青,肌肉微微抽搐,神色紧张多过愤怒。两人的座位上下渭泾分明,上首垫着斑斓虎皮,下首是寒碜碜空无一物,其中相隔一丈有余,中间却了茶几,身后又各站了二十多名弟子,也是绷紧了脸面。
两人的座位位居练武场东边正中,两侧皆有数列座椅,椅上是宾客三十余人,衣着各异,打扮不同,老道士,老和尚占了大半,或唱诺,或稽首,和和气气,面露微笑,一派高望长者之相。其中有一肌肉浑虬的中年人,颇有威风,见那少年人腾空而起,不由叹道:“这招雷法气势雄浑,威力不凡,但此子心思太急,从空中击下,成了便是定了胜负,可若是一击不中,失了先机,恐怕胜负就难说了。”周围宾客多点头称是。
这中年人眼中隐有青色雷霆浮现,是越州小有名气的紫电门的门主,平日经营的是运镖保镖的买卖,一手紫篆神雷运用得出神入化,他对雷法的评价,自然极少会有人反对的。结果只在下一瞬间就被揭晓,是成是败众人面前看得分明,宾客中一身袈裟,宝相庄严的慧法大和尚却皱起了眉头。慧法和尚是离此地三百里外的飞来寺的现主持,素来与越州各个世家大族交好,此次应陆家家主的邀请前来,是为罗家“药王神碑”的归属之事做个见证。
见那慧法和尚皱起眉头,边上一身披貂皮外套,气派是个富商模样的老者忍不住上前低声解释道:“紫电门主家传紫篆神雷,对雷法颇有研究。”言外之意不言而喻,是提醒慧法和尚那中年人的评价很受别人的认同,他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慧法和尚转过身来,对老者行了一礼,低声“阿弥陀佛”,然后认真地说道:“小僧对紫电门主的评价并无二意,只是为那孩子又造杀孽感到惋惜。”
老者抬头看了眼满脸严肃的慧法和尚,低笑一声,没有说话,心中暗暗道:“这小和尚甚是迂腐,就不去管他了。不过那少年人一连两场比试,场场把那罗家人杀死在场上,果真心狠手辣,而且天资过人,是个可造之才。现在这场若是再胜了,那罗家就没有理由再把那药王神碑留着了,凭陆家家主的承诺,我与几位同道也有机会参详一番了。”想到这里,老者不由脸上露出了笑容,心中欢喜了不少。他向主位走了几步,对那青年书生拜了一拜,转头看那少年人正占上风,压得罗家的那人连连后退,顿时松了口气,笑呵呵地对那青年书生说道:“陆阁主这位弟子真是天资卓越啊!”
那青年书生一摆手,面色一正,嘴角却情不自禁带上笑容,说道:“陶相公谬赞了!”
陶相公接着说道:“可惜雷法虽气候俨然,气象法度更不是那一般人能比得上的,但终归功法欠缺,无法发挥他的天赋啊!”他话中明的是褒中带贬,其实却是为了引出关键的功法一事。
果然,青年书生手中书卷一收,面露叹息:“我这徒儿天资极佳,却是我这师父拿不出合适的功法来,白白荒废了他大半的天赋!”书生说得自责,但字里行间的语气无一不在说功法一事。
陶相公上前一步,叹道:“陆阁主体恤弟子,果然仁义之名当之无愧啊!”他说出仁义之名时,青年书生面上顿时笑盈盈,于是心中大定,补上一句,“素来上古珍宝有德者居之,陆阁主这位弟子怕只有上古功法才能配得上啊......”
“哼!”只听到一声冷哼,陶相公全身一颤,迟钝似的看向那青年书生。书生“呵呵”笑了声,掏出书卷往茶几一放,陶相公顿时如蒙大赦,不敢丝毫久留,退到宾客席间。
发出冷哼的正是下首罗家那清瘦老者。只见老者面色冷得吓人,仿佛结了层冰霜,他望了一眼陆家家主,没有说话。那老者姓罗,名盛清,是若耶溪罗家的首席长老。而那青年书生姓陆,名正山,是山阴县镜湖中十里烟波翠烟阁的主人,也是陆家的当代家主,他三十余岁时因有奇遇,年纪轻轻便修成不老,得入先天之境,此时看似年纪不大,却是比罗姓老者还要年长上几年,是越州有名的高手。
罗家与陆家同居会稽山两面,虽一个属于会稽县的治下,一个归于山阴县的管辖,但山南山北遥相呼应,倒是常有往来。四十年前现任陆家家主横空出世,斗法越州数十门第,屡战屡胜,于是陆家名声大噪,地位也是水涨船高。加上三十年来,罗家人才凋零,此消彼长之下,从十年前罗家上任家主因海外猎兽一去不归后就再难与陆家相比,近年来更有被陆家吞并成附属的趋势。
今年年初,罗家门人从若耶溪中挖出一块刻有上古文字的石碑来,经罗家几位长老反复研究,才堪堪译出药王二字,只知道刻有上古功法,却无论如何都没法再有寸进。罗家把这个秘密保存了不到三个月,便有内鬼把秘密传了出去。从陆家到水家,越州大小几十个世家大族,没有人不知道罗家挖出上古功法。几天后,陆家家主就差人来信,说要借药王神碑一用,说是借用,倒让一帮子弟子家丁声势浩大地到罗家来取。现任罗家家主懦弱胆小,怕陆家借口生事,吞并了罗家,只得定下今日的三战之约。那中年男子与少年人的斗法已是本次约定的第三战了,少年人连番获胜,罗家再没有借口留住药王神碑了。
正当上首那陆家家主陆正山化解罗家长老对陶相公的威势之时,从罗盛清的身后跳出一个人来,不服气地说道:“什么有德者居之,你们这不是明抢吗?而且那药王神碑是我从若耶溪捡的,你们要抢我一个后辈弟子的东西,还要不要脸?”那人身穿罗家弟子的服装,滚圆的身材,一头零碎的短发下一双满是怒火的眼睛狠狠地盯着陆正山的脸。
“哦?”陆正山颇有兴趣地看着那名罗家弟子,语气反而更加温和:“我那弟子是天生雷灵之体,修那上古功法是命中注定,怎么不是有德者居之了?不过看你这修为可怜,定是罗家功法欠缺,难以培养人才,不过只要你弃姓改陆,我倒是可以破例把你收入陆家门墙,也算是你的发现之功!”
宾客席间有关注主席间的情况的人,待听到陆正山说出雷灵之体时,顿时一片哗然,雷灵之体?这可是百年一遇的修道体质,那台上打斗的少年人竟然就是,果然是天资不凡啊。这世界从上古开天辟地以来,林林总总多少英雄豪杰,虽然浩劫几载,有功法在历史中渐渐涅没,但现在如数家珍的英雄人物哪个不是天生的修道之体?就单单这百年前创立越州的主人杨潜真,统领包括在场陆家,罗家,还有花家,水家,刘家,张家等数十个大家族的先辈的传说中他化自在天境界的人物,传闻也只是厚土冥体的天资,却因自带神通,有借兵阴府之能,故能战无不胜,赶走蛮夷,打下越州山河。台下宾客的目光不由都集中在场中打斗的少年人身上,想要见识见识那少年人有何能力。
不说那个罗家弟子如何愤怒地盯着陆正山,且说场中那少年人雷法打下,对阵那中年男子也是面色一变。却没有乱了方寸,手中结印,口中连珠几句咒语,立刻撑起一道流光四溢的防御盾牌。只听得轰隆一声,电光烟花似的在中年男子的前方爆炸开来。中年人的前方气流涌动,周围嗡嗡作响,震声不绝,他接连退了三四十步,只差半步,就落到演武台外,才堪堪定住身形,嘴角却已经流出血来了。
中年男子两目怒睁,刚才那招岂止是输了半筹,心中暗道,这少年看似年纪不大,却修为惊人,怕是比自己这个炼骨化阶的修士都高了一阶不止。他知道自己硬拼绝不是这少年人的对手,但这次的胜负关乎罗家兴亡,若自己因为前几个师兄弟的死就退缩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他们的期望?“看来只能智取了。”他心中暗道,脑子拼命思考,想要找出一星半点的胜机。突然,他大喝一声,说道:“黄毛小子,竟敢伤你爷爷!”哇哇大叫几声,像是为自己壮了胆,张牙舞爪,全无套路扑了上去。
台下宾客纷纷叹息,心道这人真就是气急攻心,乱了章法,这还哪有获胜的可能。那陶相公手捋胡须,点了点头。慧法和尚紧闭双眼,低念“阿弥陀佛”。那短发少年口唇紧闭,没有说话,他站在清瘦老者身后,像是憋着一口气,只看着自己的二师兄快被击倒,自己无能为力。他望向清瘦老者,只盼他能救自己师兄一命,得到的是满面怒容,狠狠瞪了短发少年一眼。短发少年失去力量般站在原地,茫然地转头看向台上。
台上正当紧要关头,中年男子佯装乱打一气,到了少年只有一米远的地方,身形便是一错,灵活好比鸟儿,两只胳膊像老鹰的翅膀,缓缓扇动,一起一落,柔中带刚,身上气血翻腾,隐约中一只斑纹猛虎张开血盆大口,“吼!”拳头霍然击出,似用尽全身力气,向才落地的少年的面门打去。
少年不闪不避,面带微笑,夕阳下,一双冷眼,却入木三分。
眼见那中年男子的拳头猛然向少年面门打去,少年却不闪不避,在场的宾客这一刻无不屏住了呼吸,心想中年男子虽然法术修为不敌少年人,但毕竟几十年的斗法经验也是不可小觑,催动自身修炼几十年的灵纹,怕这少年触不及防之下是要败了。
便在众宾客以为中年人已然翻盘时,主座的那位清瘦老者突然叹了一声,转身对那青年书生作揖道:“阁主果然教导有方,罗家认输!”话音刚落,台上那中年男子已微微一晃,身体扑然倒地,只差少年面门半分的拳头却再也打不出去。
晚风渐歇,演武台上少年面无表情,冷冷地看着中年人倒在地上。玫瑰色的晚霞从阳平山翠绿的山后升起,浸入越来越浓的墨色的夜空,彩光给起伏的山峦镀上了一层金色的霞带,于是山川连同这演武场也渐连成了一块。演武场上的少年静静地站在中年人的边上,苍茫的暮色在他的后面燃烧着,把他寂寞的背影拉得极长,没在群山中不见踪影。
席上的宾客交头接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觉这场胜利来得如此突然,好似出了纰漏的戏剧,戛然而止,教人摸不着头脑。过了好久,陶相公才半猜的口气说道:“莫不是,莫不是刚才......”话音还没落下,就有人惊呼一声,“脖子!那汉子的脖子!”原来电光确实打中了中年男子,透过屏障的电光只不过稍稍割开了他的一条血管。只不过当时只有主座上的两人看清楚了胜负,连中年男子自己都未曾发觉。待到中年男子倒地,血从颈部的血管喷出,宾客们这才恍然大悟。
那陆正山满脸得意之色,微微一笑,说道:“陆家已经胜了三场,这场场都是我这徒儿胜利,看来这药王神碑确实是该我陆家来参详啊,罗长老,您说呢?”坐在他下首的罗盛清咬牙切齿,既悲痛罗家有失去一名弟子,又恨这陆家做事狠毒。但此是万事已定,说什么都晚了,何况自己这儿自身难保,谁知这陆家会不会赶尽杀绝,他要保存跟他一道来的弟子就必须低头。罗盛清一字一顿地说道:“药王神碑自然是陆家的!”青年书生脸色一正,对四周宾客朗声说道:“诸位见证!”宾客们纷纷点头答应。
其它所坐的人士都是越州德高望重的名宿高手,这次陆家请来,也是为了共同见证。两人身后的二十多名弟子,则是各自带来的观礼或参战的,不过陆家家主只派了少年一人罢了。那少年是陆家家主的得意门生,姓陆,名欢,是陆家的旁支所出,修为过人,天资更是非凡,性格冷淡,少与人言。此次胜利,也多是他的功劳。
罗家长老自知战败,只是对着席间宾客拱了拱手,就打算离开。他对身后的弟子说道:“把你们大师兄抬来!”几个弟子眼中隐有泪痕,悄然站出应诺。刚才那短发少年现在反倒在躲弟子的队伍中间,没有去抬。那微圆脸庞上两双乌黑的眼睛含着复仇的火焰,然而又有些捉摸不定的目光。他微微笑着,眼睛打量着台上站着的那宁静着的少年,双唇抿动,什么也没有说。罗长老面无表情,径直领着一帮弟子匆匆出了陆府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