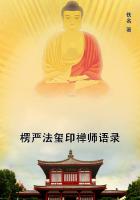今晚的巢南酒吧比平时热闹了好几倍,高远、高晓波、阿乾姐忙碌的身影穿梭在人群里,就连高翔也在帮忙招呼客人。
来的都是高远、田葡萄的一大帮好朋友。客串乐手、歌手、服务生的,听歌的,喝酒的,跳舞的,乐队总监金石头成功地把现场气氛调动起来了——
狂欢夜,走起!
“呼叫口瓜,呼叫口瓜。”从阿乾姐平时休息的小房间里,传来田葡萄的声音。估计喝了不少酒,执着地一遍又一遍地用微信语音呼叫瓜瓜。
“干嘛?”过好半天才有一个又好气又好笑的声音回复她。
葡萄马上开启了视频对话,很得意地举着一个红本子凑到镜头前面。田葡萄的嘴本来就大,今晚又涂了很惊艳的大红色,视觉效果很惊人,丁瓜瓜一下子把手机举得远一些。
“结~婚~证!”田葡萄的血盆大口里一字一顿地吐出三个字。
然后,从这个血盆大口里唧唧咕咕地传来一大段语无伦次、兴奋的话,瓜瓜大致听明白了,田爸爸终于同意葡萄和高远的婚事,他们如何闪电般地领到结婚证。
“瓜瓜,故意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然后葡萄又开始稀哩哗啦地流眼泪,“开心吧?为我高兴吧?”
“停!叫高远来!”,田葡萄挺听话,打开房间门就扯着她高分贝的嗓子叫“高远!高远!瓜瓜叫你,瓜瓜叫你!”那种语气,好像被丁瓜瓜召见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
高远很快和高晓波进来了,找了个借口准备把葡萄送回家。
瓜瓜小声地问高远,如何取得的胜利?高远凑近镜头,悄悄地说了四个字“收买老辛!”
这天半夜,瓜瓜的手机微信提示不停地闪烁,睡眼惺忪中看见田葡萄发的微信:
于菲昨天结婚了,新郎不是你的他!
瓜瓜摸索着果断地关掉手机,翻个身,很快又陷入甜美的梦乡。
秋天的达瓦措是极美的。周围的森林植被丰富,各种颜色的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彩斑斓。矮处的灌木丛上稀稀疏疏地结着一种不知名的小红果,旁边偶尔探出几株刚绽开的格桑花。湖水极清,森林倒影在湖水里,湖水也染成五彩的了。
也许山路难走,来雪山乡的外人太少了;也许是深藏在山林间,还没有太多人发现——人迹罕至的达瓦措,它不像是人间的一个森林湖泊,倒像是从仙境坠落下的一颗明珠。
从雪山小学后门出去,有一条小路一直通向湖边。路不算窄,可以容得下两三个人挤挤挨挨地并排走。
瓜瓜跟在一群同事后面,心里想,不知道是哪一位前人开辟的这条小路。如果要给这条小路设置一个路标,也许可以写上:
此路通向诗和远方!
达瓦措湖边有一片空地,间或有几个大石头稳稳地立在那里,就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雪山小学教职工秋游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
从昆明来支教的几个老师,除了瓜瓜和托尼,全部由小李老师带领着,环湖而行。
瓜瓜原本准备去帮桑珠他们拾柴搭灶的,结果被轰走了。
蹭到洗菜做饭组,又被友善地拒绝。
远远看见托尼在捣腾他的单反相机,小李老师她们也走远了。她终于发现自己没什么事可做,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地往森林里走去。
茂密的原始森林是没有路的,丁瓜瓜顺着树木稀疏的地方走走逛逛,边走边拿个棍子扒拉着。
从小就喜欢极了这样的郊游。在她爸爸老家的后山上,雨季可以捡菌子,冬天可以拉松毛。而春天,大片大片的野山茶开了,深红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开满了半个山坡,远远望去很是壮观。她小时候想,书上说的花海,可能说的就是爸爸老家的后山。她那时候有一个梦想,她应该成为一棵树,天天生长在这样的山上。
其实达瓦措旁边还有一块比较平坦的空地,只是面积小多了,被树木围成一个圆圈,就像一个天然的小舞台。
周末黄昏,天色渐暗,田葡萄走在丁瓜瓜她们大学校园。她要穿过校园正中的山坡,去到山坡另一面,和瓜瓜汇合。这条道可以节省一半的路程不说,这个季节,山上的银杏树金黄一片,走在银杏道上,就像走在一个童话般的梦境里。
这天快到坡顶的时候,遇到了三个不像是学生的人。看见只有她一个人,几个人相互使了个眼色,很快又折返回来,追上了葡萄。
“子栖!快跑!子栖!快跑!”半道来接葡萄的瓜瓜远远看见了,对着葡萄用尽全身力气地喊。
田子栖没有跑,她转过身像个泼妇一样厮打着那几个人,拦着他们。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头也不回地对着瓜瓜叫。
瓜瓜带着保卫科的人赶到时,那几个人跑了。田子栖躺倒在地上,衣服都被撕烂了。
大二那一个秋天,像极了此刻。
没有风,银杏树静立无言。
它就像锁在心底的一个梦魇,永远静静地潜伏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看见子栖衣冠不整躺在地上的心情,没有人知道她看见田敬梓变成惊弓之鸟后的自责。
“我宁愿躺在地上的是我自己,我宁愿是我自己。”每一次不小心触碰到那个梦魇,她在心里一遍遍地说。
托尼轻轻地拍着她的背说:“没事,葡萄没事,你一边跑一边叫,那几个人被你吓跑了,早就被吓跑了。”
“他们把子栖的视频发到了网上!”丁瓜瓜委屈地对着托尼哭诉,像个孩子。
“他们是在诋毁葡萄,可以追查到底的。你不要哭,葡萄什么事都没有。高远娶了葡萄,他们现在结婚了,从今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脑子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轻轻击打,耳膜“替嗒”地清响了一下,丁瓜瓜一下子清醒过来。
——她还在刚才的森林舞台,靠在旁边的树桩上打了个盹。不远处,炊烟袅袅地升起来,同事们“咭咭呱呱”地边说话,边做饭。
树林里一丝风都没有,太阳正好。
“Hello,瓜瓜。Hello,瓜瓜。”托尼带磁性的声音离她越来越近。
往常托尼这样说,瓜瓜就会瞪他一眼,叫他说中国话!
“我在这里。”此时瓜瓜没有说多余的,很快应了一声。
这一声里,竟有些弱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