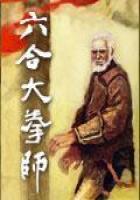太阳还没有完全的给整个世界带来万丈光芒,二爷和小不点儿已经走在了回家的路上,路上,祖孙俩听到了“哒哒”马蹄声,那是昨夜在城里巡逻的近卫军“夜骑”胯下的马匹在结束一夜的巡逻后返程,马蹄踩在青石板上,发出的声音。
末了,小不点儿问了二爷一句,“爷爷,你心疼么?”
“爷爷不心疼金子,心疼的是那两个孩子,他们俩很有可能活不下去。”
“爷爷,我已经向神明祈求,希望他们能好好地活下去。”
“好孩子,咱们走吧。”想起小不点儿,二爷心里暖暖的,这孩子虽然跟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可他聪明伶俐,乖巧懂事,很让二爷省心。自己若是留下将军给的十根金条,或许自己和小不点儿能生活的更加容易些,但二爷也是一身本事,凭本事吃饭的人,可是,那两个刚刚出世的孩子怎么办?二爷知道,自己过不去自己心里这一关,还好小不点儿懂事,这让二爷感激神明,赐给他一个好孩子。小不点儿现在只有四岁,还没到测定是否能感知武源之气的年龄,未来的路还长着呢。好在时间还有,他想陪小不点儿走下去,走的越远越好。
二爷牵着小不点儿的手,俩人走在雪地上,一步一个脚印,深深的。此时,太阳已经跳出了地平线,经历了昨天一整天的风雪,今天的特克斯帝国,终于迎来了晴天。
呼延将军府,只一夜,夫人生了两个被特克斯帝国最负盛名的“神算”柯二爷认定为“药命”的孩子这一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呼延将军府的每一个角落。
将军呼延绰虽是这个这个大家族中最闪耀的那个人,但,家族权力的核心,却不在他手中。呼延将军虽然在外威名赫赫,听得他的名号,能吓得敌人魂飞魄散,但在家中,将军的父母高堂,则是这个家庭的真正权力核心。此时,将军的父亲与母亲,正把家中所有的下人们都召集到一起,训话。下人们站在院落中,对面,就是正襟危坐,坐在会客厅的首位的太老爷与太夫人。太老爷是呼延将军的父亲,名叫呼延孝正,是现任特克斯帝国国君云长天的父亲在位时赫赫有名的武将,武功卓绝,开创了帝国黄金时代的重臣,劳苦功高,虽然现在已退居二线,但在朝中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更何况,虎父无犬子,及至呼延绰这一代,更是为国家夺取了大片国土与资源,打退了敌人无数进攻,挫败了敌人无数次阴谋的英雄。太夫人文氏,年轻时出身于官宦世家,持家有方,恩威并施,到了花甲之年,依然精明强干,呼延绰将军是家中独子,经常领兵打仗,家中的大小事务,不可避免的都落在了太老爷和太夫人的肩上。这处豪华的府邸,是两代人积累下来的。除了呼延孝正一脉,还有呼延家旁系的一众亲友居住在位于特克斯帝国京畿的大宅子里。先管好下人,至于对家人的告诫,还是放在私下里吧。
“昨晚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这是我们的家事,本与你们无关,我们呼延家的事情,还烦请各位不要与外人说,你们小范围的议论议论也就罢了,若是哪一天,我们从外人口中听到这些议论,别怪我们无情,小心你们的小命!”太夫人的一番话,吓得众人得得索索。有的胆小的下人,脑门上甚至出了汗,一直在擦拭。一众仆人站在冬日的阳光里,耷拉着脑袋,即使被雪地反射的阳光照得睁不开眼睛,都不敢抬头,还得强撑着眼皮,有的人眼睛受不了强光的照射,甚至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倒是太老爷,坐在那里,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别看老太爷一言不发,可但凡在呼延将军府待的时间稍微长的人都知道,太夫人的狠,狠在面上,太老爷的狠,狠在里子。
老人家虽然已不问世事,但有些时候,该出面,还是要出面的,而呼延孝正家又是独子,太老爷和太夫人只有呼延将军这一个儿子,加上这一家族在特克斯帝国特殊的地位,自然不允许有什么绯闻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
仆人们是从各大房临时叫过来训话的,不能说的太多,也不能说的太深,起到警示作用即可,这一点,太夫人做的很到位。训话的时间很短,但仆人们都选择了对昨夜的事情保持缄默,毕竟,还得要命啊。
仆人们散了,留下一地凌乱的脚印。很快,就有仆人把这宽敞的大院前那堆令人讨厌的脚印和无辜被踩踏的白雪打扫的干干净净,雪也被堆放在固定的位置,整整齐齐。
“快,跟上,快!”急匆匆的脚步声打破了此时的宁静,伴随这声音的,还有那种人穿着盔甲跑动时所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
“咣”,毫无征兆的,院门被暴力破开,士兵们哗啦啦像潮水般涌入了这间院落,列队两边,站的整整齐齐,昨夜蒙尘染垢的盔甲,不知何时,被这些平日里被人们认为五大三粗的汉子们擦的光洁如新,闪着寒光,就连他们手中的兵刃,也是寒气森森。
过了好久,将军才从院外进来,一步一步,走的很缓慢,仿佛这里比他的战场还要残忍,恐怖,血腥。
“按原计划行事。”将军身旁的副官应了一声,就带着一部分人走了。
没过多长时间,士兵们驱赶着仆人,侍女,等等等等,从院落的各处出来,一路上,鸡飞狗跳。“将军,求求您了,夫人是好人,她没错,求您让我们继续服侍她吧!”
“将军,请给夫人一条生路吧,求求您了!”
这样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不想听,也不愿多想,只是摆摆手,士兵们会意,把这些人带走。
不知是谁,力气这么大,竟然挣脱了士兵们的控制,向将军冲去,旁的士兵怕他伤了将军,拔出佩剑一搠,他立刻吐出鲜血,一大口。即便如此,他依然向前挣扎着,爬过去,朝将军的方向爬过去,边爬,边求情:“将军,给夫人一条生路吧,求您了!”身后拖着长长的血迹,手臂尽全力向前伸着,笔直笔直地向前伸着,他想去触碰将军战袍的一角,可眼前的视线渐渐模糊,力气随着血液不断地涌出而被抽干,说完这话,便断了气。
随后,又有几个仆人也加入了这寻死的队列,撞墙死的,扑刀死的,连这些平日里在战场上大杀四方的战士们都快看不下去了。可是,军令如山。
最终,本属于这个院落的仆人们都被清走了,一个都没有剩下。死人是对世间任何秘密最忠实的保守者。
整个世界仿佛都恢复了宁静。只是,满院未干的血迹,昭示着这座院落,刚刚经历过一场屠杀。只是,这世间万物,没有一样,可以对抗得了时间。即使今日的上位者,也会在某一时刻烟消云散。
满地血迹,在夏天,一场雨过后,可以被清洗的干干净净,即使在冬天,被厚厚的冰雪覆盖,待到雪化时,不过是尘归尘,土归土。世间万物,无一可以有超越自身时限的存在。
副官向将军报告了任务的执行情况,将军反倒是沉默了。
不知过了多久,将军终于动了。
他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很慢,从外到里,他每走一步,都像跨过了千年。身上穿的还是昨日在战场上对敌厮杀时的那身铠甲,敌寇的血液早已凝固,尘土把铠甲光亮的外壳打磨成了磨砂,将军一双眼眸,布满血丝,他,怕是一夜没睡。将军一步一步,终于走到了那扇门前,颤抖着双手,推开了那扇门。屋内的陈设如旧,一切还是记忆中的模样,脚下的地毯柔软温暖,即使隔着厚厚的战靴,他仿佛还能感受过到那种曾经美好的触感,穿过长长的花廊,走了十余步,才穿过外间,再走十余步,是里间。
终于,要见到她了么?将军停在了里间会客室与她的卧室的边缘,不敢再进一步。
“你来了。”虚弱的声音,即使虚弱,依然熟悉。没有半点怀疑,只是因为熟悉。
将军终于跨出了那一步,进入了她的卧室,那个他曾经无比熟悉,令他感到无比温暖的地方。
一进到她的卧室,将军皱了皱眉头。还没见到她人,一股子血腥的,难以言说的味道就扑面而来,刚想叫下人们来打扫,一回头才发现身边并没有人跟着。
许是隔着帘子,她的声音有些飘忽,他是这样想的。
“不来看看孩子们么?他们睡了,很可爱的。”
他此时多么想看看她,看看两个孩子,可是,他不敢,他忌惮于药命的威力,即使那些威力是他道听途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也忌惮他父母的权威,父母昨夜与他长谈,权衡利弊,条分缕析,令他无法辩驳,他和他的父母,更忌惮的是权力与地位的不保!特克斯帝国虽以胸怀宽广,接纳各国难民称道,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可以接纳药命者,因为,那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因为,这种命格的人没有任何价值!
怀中的休书早已被汗水打湿,呼延绰从怀中掏出那封提前拟好的休书的时候,手还在不停的颤抖。他是特克斯帝国的战神,是呼延家族的骄傲,年少时随父出征,大杀四方,斩杀敌人首级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在朝堂上,文也可舌战群儒,口若悬河,而今,在自己曾经朝夕相处的妻子面前,他退却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狠下心来,渡一道武源之气在那张休书上,朝那张华丽的,卸下重重水晶帘幕与帐幔的床挥去,那张薄薄的纸儿,就这样飞去,停在床前。
隔着重重的帘幕,她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那是他的武源之气。“是你么?你终于肯来看我了么?”她的手颤抖着,想揭开近在咫尺的帘幕,却又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