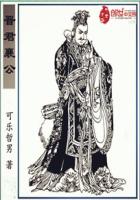众人听到太监高喝,皆是一惊,兴阳长公主也就罢了,但是三镇将军同来赴会却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镇北将军独孤七杀,北地接近蛮族,蛮族向来行踪不定,是最重要的地方,不知何时蛮族就会来犯,虽然蛮族被大将军王当年兵出北地打怕了,但是蛮族从来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一旦元气稍复,必然引兵来犯,最近几年也是大战虽无但小仗不断。
说话间,四人已经顺着红毯到了御前,四人跪拜行礼,慕楚云笑道“平身入席吧。”
四人落座,宴会继续热闹起来。虽然气氛依旧浓烈,但是众人心间都被阴霾笼罩,在座的都是权臣世家,政治嗅觉都是相当敏感的,三镇将军同至,连兴阳长公主都来了,兴阳长公主虽然不在朝中,但是却对朝局有极大的影响,当初慕楚云承继大统若无兴阳长公主慕楚璇鼎力相助怕是也没那么容易登上帝位。
正在众人疑心间,武英殿大学士金顺德出席对高高在上的慕楚云奏道,“启禀陛下,今日众臣毕至,欢聚一堂,臣本不该出来扫兴,但是此事关系甚大,臣不奏寝食难安,还望陛下允臣禀奏。”这金顺德五十岁上下,一身华贵朝服,身材微胖,虽只是个大学士无甚实权,但是这大学士一般都是饱学之士,在士子文坛颇有威望,所以也是朝中重臣。
慕楚云脸上浮起一丝笑容,说道“众卿家难得欢聚一次,金爱卿又是明日早朝再禀可好?”
金顺道一愣,旋即跪奏道“陛下不可,古人有训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陛下乃是圣主,万不可弃天下之事为一晌之欢而不闻。”
这是岑安也出席对慕楚云奏道“启奏陛下,金大人所言有理,若置国事不闻,恐于陛下声威不利。臣请陛下听奏。”
岑安言语落地,一大片朝臣皆起身奏道“臣请陛下听奏。”
慕楚云也不生气,笑了几声,道“金爱卿,你有何事便说吧,正好今日来人都是能臣勋戚世家豪门,定然能解决让金爱卿寝食难安的…国事。”随后,慕楚云摆摆手,示意李福将舞乐停下,李福上前一步,将拂尘一甩,乐师当即停下,众舞姬便识相的退去了。
金顺德闻言奏道“启奏陛下,臣闻大将军王慕楚寒路遇恶匪,未免受辱燃车而薨,不知陛下可知此事?”
慕楚云面色一沉,冷声道“此事朕早已下旨不得外传,以免扰乱军心,金卿这是要为天下而乱天下吗?”
金顺德急忙回道“臣不敢,只是此事终要处理,臣知大将军王遗体今日便可运抵京城,不若乘此机会诏告天下,已安群臣之心,已安天下之心。”
慕楚云冷声问道“这就是金卿要奏的天下大事?”
金顺德继续奏道“回陛下,此事只是引子,昔日先帝溺爱大将军王与其权力甚多,陛下即位三年,其为臣不来朝觐是为不忠,家中无父则长兄如父,其为弟不来事兄,是为不孝。大将军王慕楚寒不忠不孝忝居高位,臣请削其大将军王爵位,肃清朝中不忠不孝之气,否则何能为天下表率。还望陛下以天下为念,准臣所奏。”
金顺德言毕,只见席中出列一位武将,张口便骂“什么狗屁大学士,你学的都是狗屁吗?说的话竟如放狗屁一般!你这些话大将军王平定三十六属国之乱时你怎么不奏?大将军王北击蛮族的时候你怎么不奏?大将军王改革军制为朝廷每年省下数百万两军饷的时候你怎么不奏?瀛台乘乱侵我西境的时候你怎么不奏?大将军王活着的时候你怎么不奏?儒家的学士都是你这般忘恩负义只会说死人坏话的人么?”众人循声望去,说话的是一位威武将军,三十五六岁,一身铠甲闪闪发光,面目英武非常,手按青锋宝剑,一脸怒容,双目圆睁似要立马杀了这金学士一般。
“独孤将军慎言。”一声沉稳的言语压住了众人的窃笑与骚乱。
“哦?岑相?呵呵,难道你也是这般儒家之人么?”独孤七杀转头嗔笑道。
岑安冷笑一声,道“独孤将军,金大人是二品衔,世袭宁远伯,你一个三品将军竟然在圣驾前出言侮辱,你可知罪吗?”
独孤七杀笑道“哈哈哈……宰相大人你当我如你们一般天真么?想治我的罪?治我什么罪?像宇文贪狼一般?我告诉你岑安,镇北军拉练之军就在兴都以北五十里处,本将军一声令下不到一个时辰就可进京勤王护驾!你们这群乱国贼子,谁的罪大还不知道呢!”
众人闻言大惊,如果真是这样,以镇北军的战力,若是全军点齐,尽管兴都形胜异常,但是拿下没援军的兴都依旧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好多大臣都面色难看,生怕岑安激怒了独孤七杀让其杀进兴都,到时候府邸能不能保住就是问题。
岑安闻言却不以为意,回身对席间唤道“许将军。”
席间一位伟岸将军出列,高声道“奉陛下密旨,五万镇南军已于兴都南城门外驻扎。”
听闻许国义如此说,慕楚炎心中一怔,想道,沐欣羽果然不肯以身事许,不然以许国义对沐欣羽的情意,今日这个头许国义一定不会出。如此,这仗非打不可了吗?就算许国义带了五万镇南军,可是还有十万镇西军呢,镇东将军孙恒也没有说话,但是就是他不说话也不会帮岑安,如果这三镇同时发难,一个许国义加上五万羽林军,根本就没有胜算,更何况西境还有瀛台二十万铁骑,以传说中瀛台大长公主对七弟慕楚寒的情意,必然星夜杀奔兴都,鸡犬不留。想到此处,慕楚炎心里寒意顿起。
就在慕楚炎思虑之间,钱王胖胖的身子却挡在了两伙人之间,笑道“哎呀,哎呀!多大事啊,值得你们一群重臣这般吵闹,陛下可在上面看着呢,你们这般胡闹成何体统,有什么事自有陛下圣裁,你们争得面红耳赤做什么,传出去不得被他国耻笑嘛!和气为先,和气为先。”
众人闻言皆回头像台上望去,却见慕楚云一脸笑容,神色玩味的看着底下争论不休的众臣,看众人都望向自己,慕楚云轻笑道“古之贤主不禁臣子之争,朕虽无德,亦想相仿先贤,众卿今日之争万勿以朕为念,朕今日大宴就是为众卿欢娱办的,众卿愿意为国分忧朕自然不会阻拦,此处也不是朝堂,众卿畅所欲言,朕不会怪罪的。”
言毕众人却不知如何是好,继续争吵还是就此作罢?皇帝真的不会怪罪?出身儒家的陛下今日做了许些不合礼数之事,俗话说反常必夭,陛下今日如此做派,是真心想看朝臣争论还是在等事情闹到无可收拾的地步再做处理?众人心间本就是疑云重重,大将军王就算已死陛下也下令封锁消息,连尸体就未运进京城,就有人笃定大将军王已薨。三镇将军携手入京,镇北军搞拉练到了兴都北城,镇南军半数驻扎在兴都南城外,镇东将军一言不发,兴阳长公主居然来这选秀大宴。慕亦城和勋臣联姻,慕天金要娶儒家泰斗爱孙,而看钱王的脸色似是不知道儿子会做这件事。宴会短短几个时辰,皇帝的态度,事态的发展没有一样是与会者之前预料到的,如果不是巧合,那就只能是一句话,山雨欲来风满楼。而这么都的偶然,就算是偶然,也不能真的是偶然了。
场中鸦雀无声,整个宴会都沉浸在众人心头的阴霾和现场的尴尬中。
与会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大家看看那红袍烈烈的镇北将军,又看看一身华贵朝服的岑相爷。可是两边都没有说话的意思,皇帝依旧是舒服的靠在龙椅上,玩味的看着底下。众人心中不禁想道,难不成今日这宴会就这么瞅下去?瞅到太阳落山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金大人,方才不忠不孝之人说谁?”语气冰寒刺骨。
这一句话打破了宴会的寂静,也打破了众人思绪。众人循声望去,却是左席一位少年,浅色华绸衣袍,墨色轻纱冠,面容清秀,眉目之间一股英气迫人。
金顺德一愣,却立马回过神来,行了一礼,道“原来是亦城小王爷,刚才下官之言说的清楚,不忠不孝之人乃是为臣三年不朝,为弟不事长兄,而忝居高位着,难道亦城小王爷不知此人是谁吗?”
“亦城愚鲁,还望金大人不吝赐教。这不忠不孝之人说谁?”慕亦城不卑不亢道。
慕天衡在席间一脸迷茫,心道“这慕亦城搞什么鬼,大家听得清清楚楚,金顺德点名道姓说是七叔,为何慕亦城要这般在问一遍,莫非想以诬陷王爵治罪吗?”
金顺德冷哼一声,心道,量你一个没实权的王族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便答道“不忠不孝之人说你父亲慕楚寒。”
慕亦城微微一笑,道“大人,御前可说不得假话,不想名闻天下的大学士竟是不忠不孝之人,可悲可叹呐。”
金顺德闻言一愣,却发现场中不少人都在掩嘴偷笑,慕天衡更是在席间笑的花枝乱颤,登时一股怒气涌上心头,怒喝道“慕亦城,你父亲嚣张跋扈,目无朝廷,朝廷依旧与其高爵厚禄,你不知报答也就算了,竟然言语戏谑重臣,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真是蛇鼠一窝!”
此言一出场中哗然,岑安更是眉头大皱,刚要说话,却见钱王黑着脸说道“金大人,我倒想问问什么叫蛇鼠一窝?什么又叫有其父必有其子?”
金顺德闻言大惊,自知方才怒极失言中计,伏地不敢答话。
慕天衡却跳出席间蹲在跪倒的金顺德面前,将身子俯下,想要看到金顺德的脸,金顺德稍一抬头,慕天衡便冷笑道“金大人,七叔是蛇是鼠,那我呢?我父王呢?我五伯呢?陛下呢?对了,还有先帝皇爷爷呢?”
金顺德闻言额上登时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子,身子不住的颤抖,伏地不敢申辩,生怕自己一个失言又说了什么着了道的话。
“老臣启奏陛下,金顺德出言不逊,辱及陛下及先帝,有失臣节,有辱儒家圣贤教诲,本该处死以谢天下,但金顺德入朝多年有微功与国,故老臣请奏将此狂言之贼削去爵位官爵,以显陛下宽宏之德。”声音虽然苍老,却昂扬有力,极有威严。
慕楚云闻言笑道“陈老国公所请,自无不允,来人,将此狂言之贼押下去,削其爵位官职,永不录用。”
众人皆齐声道“陛下圣德。”只是众人未曾注意到,慕楚云虽然都按的是陈玄的说法,但是却加了四个字,永不录用。跟着宰相而不跟着皇帝的重臣,在皇帝眼里自然是不能用的,永远不能用的。
慕天衡看着面如死灰的金顺德笑道“金大人,所谓无官一身轻,陛下可真是心疼你啊,这辈子都甭想做官了。哈哈……哎,金大人,不对,金百姓,怎么还不谢恩呐?”
一滩烂泥一般的金顺德强打精神颤声道“草民谢陛下隆恩。”说完,两个内侍上前,将烂泥一般的金顺德拖出去了。
席间,钱王向睿王低声问道“老六你今日怎么不说话啊。”
睿王苦笑一声答道“金顺德这个笨蛋,慕亦城几句话就激的他胡言乱语,岑安怕是要镇不住场面了。不是岑安无能,是儒家这帮书生看不清局势啊。要是再这么胡来,镇北军一入京,朝里的人就要换一遍了。”
钱王大惊,急忙低声问道“不会吧?独孤七杀还真的敢带兵入京?”
睿王答道“你听他说要带兵入京么?他说的是勤王,是清君侧,他说的不对的话最多就那几个狗屁。可是那些话也在理,老七的军功谁人不知,他如此一说倒像是儒家要过河拆桥。只怕现下众臣心中也是起了恻隐之心,我倒真是小看他了,我当他和宇文贪狼一般是个武夫,不想还有此等手段,怪不得当年老七非要让他做这个镇北将军,倒是个有本事的。不过岑安怕是还有后手,一个大学士伤不了儒家筋骨。”
钱王胖脸上的短眉皱成一条,问道“那我们怎么办?束手待毙?看着岑安他们欺负亦城啊?”
睿王略一思忖,说道“看着吧,你我今日都不要再说话了,恐怕今日之事,不是你我能搀和的,怕是会有剧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