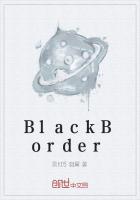待到野苑城破,眼见着敌人潮水般涌入城门,驻守镇南大营的北辽兵士方知南越大军早不在巨阳城了。许多人叫乱枪刺中,弥留之际仍想不透:
到底来了多少人?
还是叶添意料中的那些。只是到得忒快了些,不枉八万将士风餐露宿了一整个月,也不枉司马伯男帐下精兵死伤过半。
那日乔松随辎重粮草同往赤地城,巨阳城的全部人马都就着夜色跟来了。只有军士,没有武器,倒也行无影去无踪,在赤地城二十里外的山坳下了营。
刀枪棍棒给乔松押运,这般金蝉脱壳本该早为细作察觉,无奈他一到戍北大营便搞了个拙劣的声东击西,被叶添识破了招摇过年的一层,却还有藏之深山的另一层。
八万军队,也不练兵,为了节省粮食,每天除了睡就是睡。武艺虽有生疏,精神却很饱足。
期间不是没有偷偷过去请战,乔松只回稍安勿躁。军令如山,不敢不从。
终于等到除夕良夜,月黑风高,宣节校尉通报先遣开拔,许多将领心痒难耐,竟然带着帐下兵士跑了起来。到了空无一人的戍北大营,斧钺钩叉早已静候多时。正整装待发,两个细作探头探脑,当下成了刺猬。数日以来首次见血,众人皆道杀敌太爽,非要再弄翻他百个千个才能解渴,士气不是一般的旺。
一个时辰便冲到西南城门,守城兵士只三三两两,人还没砍痛快就攻进去了。大家进门之后一边乱刺一边咒骂:
“都是司马伯男这个好大喜功的,把北辽的鞑子全引到自己那边,一仗下来还不得升到明威将军啊!”
有消息灵通的。
“别这么说,听说司马将军背上铠甲都被刺烂了,从城楼掉落,生死未卜呢。”
“怎么回事?”
却说司马伯男帐下五千军士策马扬鞭,马尾绑了树枝,扫得尘土纷扬,仿佛身后千军万马一般。北辽斥候见状,慌忙回报,才说了一句“南越蛮子全营出动”,便听得鼓声阵阵,见得燃火无数,城下弓弩箭手已一字排开,矢石如急雨。待到守城军士布阵回射,对方盾牌已立起来了,迎着枪林箭雨缓步向前,朝着东北方向,一步一步到了城下。
此事也怨不得北辽守卫,司马伯男鸣镝起事之时,年夜饭正上桌,多少要吃一口,谁曾想南越会挑此刻来袭。
“两万大军,怎来得如此快?”
“这……属下不知。”
“巨阳城有无异动?”
“这……像是没有。”
“延怠军机,军法处置!”
守城的定远将军荣开见南越主攻东北,盘算一下敌我兵力,调了两万人马过去,其他各处留了一万。他到底谨慎,担心还有后着,遣人去了陶郡。
但见南越先起云梯再起飞梯,放下盾牌,拿出其中裹着的生牛皮来,十人一队披着,接连向上爬去,刺也刺不动。荣开愣了一愣:
“火攻!”
浓油泼下,炽炭扔下,不多会儿惨叫阵阵,几个攀在上面的摔落下来,掉到地上听得声响,不闻哀嚎。料想司马伯男军纪严明,怕扰乱军心,疼死也不让叫出来。
可还是瘆人的。云梯上一时再无动作,有胆大的扔了牛皮,贴着墙皮避着箭矢继续向上,当中一个身量较小,动作却灵活,蹭蹭几下到了望楼。余下兵士见得有人登城,颇受鼓舞,纷纷前仆后继。
到了上面,何华方知司马伯男说得极对。在城墙上,首要是让自己不掉下去,其次是多挑下去几个敌人,至于枪法剑法棍法,大部分是使不出的。她提着一柄抓枪,胡乱比划,也捅死了不少。只是北辽人多势众,怎么杀都杀不完。何华满脸是血,右臂似不对劲,或许伤着了,却来不及疼。
苦战了不知多久,听得城门屡受撞击,鼓声愈发激昂,才缓过神:乔松来了。
身后突然出现一人,她正待回身挑下,却是司马伯男。
“你受了伤,先下去罢。”
方才他在下面看得清楚,何华被北辽鞑子刺了好几次,整个人却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感觉他也遇过,是杀红眼了。他担心何华不知不觉流血过多,赶紧取了锥枪爬上云梯,十步八步就上了城。
只是何华一马当先冲得极远,他不知道打下了多少敌人,方才追到身后。
何华却不管不顾。
“我没受伤。”
“何华!”
话出口,司马伯男悔之以晚。之前节节败退的兵士,准备下到城下的兵士,几近万念俱灰的兵士,听闻此语尽数趋步向前,眼里闪着狠厉,神色完全疯狂。
他们听见了一个名字,那个杀了他们上百弟兄的蛮子,此刻就在眼前。
所有枪尖灌注了全部力气,指向那个人。
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