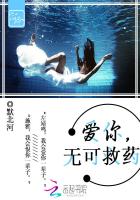三人入殿,也分不得主宾,席地而坐,张举侍在一旁。无咎子内力精深,故所受蛊毒之害也颇深,但终究不是华阳路数,此刻虽不敢妄动真气,但未蒙心智,思绪依然清晰。一手紧握住玉虚真人的胳膊,道:“道兄,殿外飞灰落地生根,显是凝聚了你的真元,眼下玉真已逝,华阳四杰分崩离析,难道你也要撒手而去么?”
张举听闻“啊”的一声惊叫道:“掌门师伯!掌门师伯……”却又不知要说什么,只是簌簌的落下泪来。
玉虚真人轻出一口气,道:“举儿,不可作此情状,一代新人换旧人本是天道,我已虚活七十余载,虽未证道,但也看破世俗,不觉遗憾。但眼下有两件事最为紧要,张举,你要谨记!”
张举拭干眼泪,正色道:“张举明白,请掌门示下!”
玉虚真人微微含笑,道:“其一,天王山招揽中华各派的奸谋虽未得逞,但山下的凶徒必要冲上山来,趁我等中毒之时,屠戮中原精英翘楚。”
张举猛然想到此关节,不由得心惊,纵使自己功力大盛从前,也照顾不得这几千中毒之人,届时,同门至亲在眼前被人屠杀,却救之不得,想想便不寒而栗。
“华阳开山之时,早有计较,你速去大殿东首,击碎第一纵,第三、第四块石板,其内有龙头扳手,两者同时拌动。”
张举虽不明其中道理,但见掌教真人态度平和,显是信心满满,方才放下心来,依言而行,果见其中有两根黄铜所铸的龙头扳手,分别朝向南北两侧,张举用劲将龙头合至一处,只听见齿轮咬合的声音,却不知发生了什么。
玉虚真人接着道:“此乃玄武巨阵,为华阳真人亲制,后经历任掌门修制、完善,方成规模。眼下,入山各个道口的机关都已触发,迷雾、怪石、青松相互掩映,不知其理,就算武艺通天也无法入山。这阵法唯华阳宗历任掌教所知,就连我那师弟也不知道。”
无咎子心中感慨,但见玉虚真人气息越来越弱,怕是大限将至,心中又想到十几年前共御外侮的豪气干云,又不胜悲凉,道:“道兄,你且休息一会儿,不要乱了真气。”
张举心中明白,掌教师伯修行通神,早已到了身外惊雷而胸中平湖的境界。眼下其体内真气微弱而且运行不得章法,显是寿元已尽,再也掌控不得了。
玉虚真人慢舒一口气,叹道:“这第二要紧之事能否做成就要看华阳的造化了!”
玉虚真人接着道:“张举,你对我不可有所隐瞒,你这一身霸道的修为从何而来?”玉虚真人模样突变,语气严厉,双目如炬,恶狠狠的瞪着张举。
张举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玉虚真人如此模样,吓得当即跪倒,连连叩头。想着这几日的怪事,一时心乱如麻,自己也是糊涂的很,不知该从何说起,心中骇然,只是不住的磕头。
玉虚真人见状更气:“可是玉真传给你的?快说!”
张举心中惊惧,冷汗直流。忙道:“不是……不是……”
无咎子见状,连忙从旁帮衬,:“玉真道兄的为人,你我都是明白的,绝做不出此事,绝做不出此事!”
玉虚真人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哎!我糊涂了,玉真若真有如此恶行,又怎会遭了他们的毒手。举儿,你且起来吧。”
玉虚真人接着道:“如今所中蛊毒者甚众,若不得救治,别说是华阳,整个中原武林都将元气大伤,届时胡人南侵,谁人可御敌?谁人可以保民?举儿,你可知这其中的利害?”
张举见掌教言辞不再激烈,放下心来,但仍旧怯生生的道:“徒儿明白……”
“为今之计,举儿,你便是破解眼前困局的唯一希望!”
“什么?!”张举不禁愕然,但张举本是聪明之人,回味起前前后后的事,也猜中了关节。刚刚与魁木相斗,便发觉有异,好似自己的一身功力与魁木相差无几,只不过运用起来就是云泥之判了。张举试探着问道:“难道您说的是我这一身的古怪真气?”
“不错!正式如此,适才天王山三人说的明白,若想解毒非其本门真气不可!”话到此处,玉虚真人与无咎子对望一眼,无咎子面色凝重,向玉虚真人一颔首。玉虚真人接着道:“举儿,你所料不错,你这一身内力正是天王山一脉!”
虽已想到有此可能,但张举还是难掩心中诧异,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张举,老夫与天王山明里暗里激战数十载,你一出手,我便看的清楚,绝不会错。”无咎子突然拔高了嗓子,道:“你看我面色乌青,难道是天生的不成?!全是拜天王山那帮胡鬼所赐,当初被石国人伤了经脉,若不是掌门师兄无誉真人和玉虚道兄合力施救,早就没命了!”
张举听出无咎子口气不善,显是认定他与天王山有些许瓜葛,无咎子与天王山有生死大仇,眼下他真气受制,若是不然定要拿住自己好好质问。张举心中无奈却也不以为意,眼下大局为重,心存疑虑,不禁问道:“掌门师伯,徒儿刚刚对敌之时全凭一时激愤,并不懂得搬运之法,这真气在我体内乱涌乱撞,我无力牵制。若是聚于体外还好,但若是导进体内,而无法牵引,岂不是害人性命?!”
“举儿,今日若要成事,非你我三人通力而为不可。”玉虚真人面向二人,道:“举儿,我华阳宗虽不懂天王山的真气运移之法,但所幸门中前辈留下一部《知常经》,或可搬运外门真气,但其文晦涩难懂,一时你也难以尽明,我现下传你总纲,你需谨记,有不明处,我便解答。你听好了:致虚,守静。思万物并作,以观其复……”
听到此处,无咎子费力的站起,跌跌撞撞便要向殿外走去。
玉虚真人忙停下,劝道:“道兄,你不可回避,如此非常之时,还有什么门户绝学之防?”
无咎子虽嫉恶如仇,但终究修行日久,性情豁达,听闻此言,也便反身坐下,共同参悟,约莫过了一柱香的时间,张举将《知常经》的总纲反复默诵了三遍,但其言语拗口,意思晦暗,主旨与华阳多年所学似有想通之理,但又大相径庭,只得反复向掌教请益,遇得十分难解之处,又有无咎子从旁点播,也领悟了十之七八。
“掌教师伯,恕徒儿鲁钝,徒儿觉着这《知常经》的枝枝节节越是深究,便越是糊涂!刚摸到头绪,却发现离得更远。其中大部分与华阳义理相通,但若附着这其余内容,就面目全非了。”
玉虚真人听罢,含着笑点点头,却没有急着说话。
无咎子初一来对张举很有成见,囿于他身负天王山真气,虽挽回大局,却也可疑!而此时与自己共同剖析义理,发觉其人态度诚恳,而且聪慧异常,不由得大声赞赏,道:“华阳有此人杰,老道羡慕啊,羡慕啊!”
张举却更是糊涂了,道:“无咎真人,您指的可是著这《知常经》的前辈高人?”
“并非是他,而是你啊!”无咎子和玉虚真人对视一笑道:“我也是经你点播,才看出其中端倪,这《知常经》与华阳的武学相似,也与我真武阁的武学相似,只怕是与天下的武学皆相似,如此模模糊糊,似有似无,似真似幻的法门确实能驾驭天下各门各家之术啊!”
无咎子转向玉虚真人,道:“道兄,这《知常经》恐怕也算不得是你华阳的绝学,我料想是无人愿学吧?”
玉虚真人不以为忤,反而含笑应答道:“确是如此啊,凡学武之人,都追求内力精纯,有几人能兼收各家之学,习那庞杂不精之术,以似是而非的章法运移各家真气。这《知常经》的著者我也不知是何人,只是年轻时,气盛要强,觉的这著述难明难解,非要跟自己一较高下,待我修炼一半时,心中释然,便会心一笑,搁置一旁了。”
玉虚真人接着道:“举儿,既然你以通晓其中大意,稍后,你便用此法为无咎道长运气解毒!”
张举还未来得及应承,玉虚真人便对着无咎子道:“无咎道兄,全场之人内力最为精纯者非你莫属,虽中这蛊毒,运转确实不可,但抵挡一阵或还可行,若是待会举儿掌控不得,还请无咎道兄多多担待,提起精神,及时抵挡,以免心肺受创。”
无咎子道:“道兄,此法已是最佳的选择,我定勉力而为,让师侄摸索出这运气之法。”
张举道:“可是,我体内真气有些霸道……徒儿怕……”
话为说完,无咎子便打断张举,道:“小子,看你面貌爽朗,怎地如此婆妈,你师伯是当今天下武学泰斗,你照他说的做便是!”
张举无话可说,只得低垂下头。
玉虚真人,言语平和,道:“举儿,天命使然,你不可心有旁骛,如今而讲,你且尽人事,这天下百姓便交给天命吧。”
张举只得依玉虚真人所言,伸出双臂,推至无咎子背后,将真气缓缓注入其体内,以《知常经》所载之法运移真气。而玉虚真人,单手搭在无咎子肩部,感受张举的真气在无咎子体内的一举一动。
备注: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