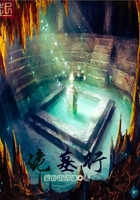第八节被逼道歉
满堂叹了口气,返回原地,把串串叫了出来,俩人一前一后走到远远的土崖下。满堂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串串。串串摇了摇手,满堂递烟的手在空中僵持了一会,无奈地收了回来,把烟放到自己嘴里,点上。
“你准备怎么办?”满堂问道。
串串不吭气,往土崖下一蹲。满堂也顺势蹲下,面对面盯着串串,等待着他的回答。
“你说吧,提个条件。”满堂猜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趁这个机会,也许串串会狮子大开口,狠狠宰一下粉周妈。埋藏多年的怨气好不容易有个发泄口,他怎么会轻易让“机会”从眼前溜走?
串串还是不吭气。
满堂急躁了,被串串的闷声闷气逼得有些着急了,他实在猜不出这个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家伙的脑瓜子里到底咋想的。眼看着在这冰天雪地里冻得直哆嗦,时间也不等人却这么不言语地干耗着,满堂忍不住劝道:“粉周家,一个村的,这几年你也看见了,光景过得不容易,恓惶地很,老俩口能这么大年纪了家也不要了跑到雲城去打工吗?村南村北地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人都死了,你难道还要把活人逼死?”
……
“说吧,你开个数,加到之前与你说好的毁青费里,只要他们家承担得起。”满堂也没了抽烟的乐趣,把烟头扔到雪里,狠狠地用脚踩住拧了拧。
……
串串还是一言不发,蹲在崖下,脑袋低着,似乎要钻到裤裆里去。
知人知面不知心,在这一刻,满堂打心眼里瞧不起串串,别看同一个村的都在二里湾住了这么多年,他在今天才算真正看清楚贾串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怎么样的城府和花花肠子。
他这就是典型的趁人之危。满堂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他知道串串就是在故意刁难粉周妈,串串在发泄着多年前受辱的毒气。串串他心里很清楚,过事过到这份上,粉周妈如果想去别处再选墓地根本不现实,即便现实,时间也来不及了,最后还是只能选在他家的地里。对于粉周妈来说,这就是个单选题,再无别的选项。因此,串串他要通过坐地起价来发泄闷气、怨气、毒气。
满堂看着串串的闷不吭气,真想冲上去揪住他的脖领,美美地扇他几耳光。
但是满堂觉得那太唐突,就在内心发了毒誓,等帮粉周妈把大木的事情撩了,别看和串串在一个村呆着,他再也不愿意看见串串一眼,不想和串串多说一句话。
“阴阳先生也是闹了鬼了,怎么非要把大木的墓地算到这块地上?这地风水好?”满堂从崖下站起来,皱着眉头望着远处那块浇不上水、并且不怎么肥的土地,“都怪这个贾串串,心思歪了,心眼坏了。”
“我一分钱也不要,我就想叫她给我赔个礼、道个歉。”就在满堂在心里狠狠地咒骂贾串串的时候,贾串串终于开了腔。他这一开腔,把满堂愣住了,满堂以为没听清楚,忍不住张大了嘴巴,甚至都露出了抽烟熏黑的后槽牙,重新蹲下问道:“啥?你说啥?”
串串盯着满堂的眼睛,又一字一顿地说了一遍,“他们家欠我的,欠我一个道歉。必须给我赔个礼,道个歉。”
这次,满堂听得很清楚,“给我赔个礼、道个歉”从串串的嘴里一个个爬出来,掷地有声。
满堂没想到串串的要求会这么简单——不牵扯到钱,自然简单——但是简单却不容易执行,粉周妈是那么容易低头的人吗?况且当年是他们家的大木打的你,你却叫粉周妈给你道歉?粉周妈会乐意吗?
“哎!你们都是爷,都是难伺候的主。”满堂考虑了下,叹了口气摇着头,用手在膝盖上一拄站起来,一滑一滑地从土崖下走回到挖掘机前。
不知道什么时候,粉丽也跟着从家里跑来了。站在挖掘机的履带旁边,抱着她母亲斜靠在挖掘机上,眼睛盯着地面,透出一股恶狠狠的怨气。
“串串啥要求也没有,就是一条,若想人埋在他地里,必须道歉。”银学正等着满堂的消息,满堂把他叫到别处,轻声说道。
“哦?!”银学也感觉到惊奇,和满堂一样,他也没想到串串会提出这么个要求来,“他要怎么个道歉法?”
“说声对不起?鞠个躬?还能怎么样?”满堂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个可得问清楚,别叫这怂娃再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银学觉得还是该谨慎些。
在凤凰塬,这个位于晋南腹地的地方,不像城里人那样,做了错事,说声对不起以取得对方谅解;也不像古惑仔,冒犯了对方,要不饭店里请喝一顿和解酒,往事一笔勾销。在凤凰塬,人们没那么多形式上的礼貌,更多在于内心的谅解——今天当街吵了架,第二天见面远远地打声招呼,亦或哈哈一笑,也许啥事都没了。这个哈哈一笑,就代表着尴尬和难为情,甚至掺杂着道歉不好意思的成分。
这或许就是江湖上所谓的“一笑泯恩仇”吧。
虽然有时候只是小拌嘴,小红脸,也压根上升不到“恩仇”这个地步,但这一笑,这一打招呼,所有的恩怨都消散已尽。
也有个例出现。也对着笑了也打过招呼了,却仍然得不到对方谅解,越闹越僵;也有压根不想打招呼的,做了错事,爱认死理,就认为自己全对都是对方的错,第二次见了面,脸一扭,鼻子一歪,甩给对方一个后脑勺。
百人百性。当然,也有比较隆重的。就像古惑仔的那样,专门跑到虞镇的食品加工厂,称上二斤点心,用那种绿纸的方块纸包严实喽,再贴上一块红色的封面,用灰色的纸绳一绑,拎起来跟在中间人的后面,专门跑到对方家里认错。
林林总总,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是认错的形式,关键是得有认错的态度。
就今天这事,银学觉得棘手,男人们之间的矛盾,好处理。怕的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爆发的矛盾,处理起来比较麻达。况且今日这事,还是要女的去低头给男的认错,吃了这么多年的馍馍饭,这事对银学和满堂来说,估计都是头一遭。
但是,银学反过来想,站在中间人的立场来说,一切都是“回报”吧。有句俗话不是这么说的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也不能说串串做的过分,谁让当年大木欺负人家呢?但是在今天这个时候,串串把陈年旧事再提出来,就有些刁难别人的意思。但碰上这事,你年轻时候再气盛,也得低个头。你再不愿意认错,也得低个头。
考虑再三,银学拿不定注意。他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觉得再不能耽搁下去了,顾虑不了那么多了,只要硬着头皮走到粉周妈跟前,把串串的要求说了出来。
说完话,银学注意着粉周妈的表情——这个微胖的老年女人并没有想象中会引起多大多剧烈的反应。兴许,在这一段时间里,粉周妈已经想通了。
“道歉就道歉。”粉周妈有气无力地说道。说完,抬起眼皮望了望远处的墓地,那眼皮似乎有千斤重,拉扯着粉周妈僵硬的脸。墓地位于一片积雪的洁白当中,露出一块黄褐色,打墓师傅估计也跑过来看热闹了,顺手把铁锨插在那黄褐色的土堆上,孤零零的,感觉风一吹,就会一头栽倒下去。
粉周妈愣愣地眼睛眨也不眨地望了半天。等了一会,拽着粉丽的衣服就欲起身,想往那土崖那挪。可还没起来,就瘫倒在粉丽的怀里。
粉丽扯着嗓子嚎哭起来了。
粉周妈制止住女儿的哭声,又强行往起站了站,还没站稳就又瘫倒了下去。
“妈——不就是个道歉吗?我去啊,我去道歉。”粉丽哭喊着,挣扎着抱起妈妈,把她安顿在挖掘机的履带上坐好。完了,抹着眼泪朝串串呆的土崖下跑去,一跑一滑,爬起来再跑,一跑又一滑,跌跌撞撞。
银学和满堂看粉丽恓惶,怕有什么闪失,叫三多子照顾好粉周妈,也一起跟着跑了过去。
一跑到崖下,粉丽再次跌倒下去,她也就没再起身,用手抓着被雪压住的草,往前爬了几步,爬到串串的脚下,大声地哭喊着:“叔啊,我是粉丽,大木的女儿给你道歉啦,我粉丽给你磕头。我爸当年做的不对,对不住你了。”
说完,粉丽脑袋砰砰砰地磕在那雪地上,因为动作大,那雪都跟着飞扬起来。
串串被吓了一跳,噌地一声站了起来,靠在土崖上,手里正抽着的烟都掉在了雪里。
“你——你——你这是干啥呢?那会你还小,大人的事,和你们小娃娃没关系啊。”串串想去拉粉丽起来,但根本拉不动。
“满堂,这是干啥呢?”串串一边拉着粉丽,一边用求助的眼神望着跑了过来的满堂和银学。
“你不是叫道歉吗?大木他娃娃给你道歉的啊。”满堂冷着脸,瓮声瓮气地说道。
“道歉也不需要这样啊?况且,我吃了一年酸馍馍和这娃娃没关系啊。”串串说道。
满堂没搭腔。
银学走到崖下,拉着粉丽说:“快起来吧。”完了对着串串说,“陈芝麻烂谷子的,多少年都过来了,非要在今天再提起,差不多得了。”
“我让道歉,他们有个态度就行了,也没必要动起这么大的声势啊。”串串觉得委屈,这些村干部都不理解自己吃酸面粘馍馍的苦,忍不住嘟囔着。
“你刚才千阻扰万阻拦地不让打墓,说是要人家道歉。临了到这会,歉也道了,头也磕了,你却说要个态度。你这也太难为人了,这个度可不好把握啊!”满堂站那,手擦在兜里说道。
“呃——”串串还想争辩,却半天没憋出一个字来。又低头去扶正哭得稀里哗啦的粉丽,可哪里扶得起来,只好手一挥,从崖下走了出来,“算了,算了,你们打墓吧。”完了,手一背,往来的路上走去。
银学冲着满堂使了个眼色,满堂不情愿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人民币,追上串串,硬塞给他。串串不要,俩人又在那雪地上来回推让了一番,最后,满堂往串串口袋里一塞,小跑了回来。串串握着那把钱,愣在雪地里,冲着满堂的背影“哎——哎——”叫了几声。见满堂没回应,只好又重新把钱塞进口袋,往村里走去。
银学等满堂跑回来,一起走到崖下,拉起粉丽从崖下走了回来,冲着三多子喊道:“招呼师傅开工吧。”
三人相跟着走到挖掘机跟前,粉丽啜泣着抹着眼泪,架起母亲的胳膊准备回家。
“歉道了?”
“嗯。”
“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啊?”粉周妈在女儿的搀扶下,干嚎一声悲戚地哭了起来,在哭声里,粉周妈来来回回数落着大木的不是。
粉丽试图劝劝母亲,但没一点效果。母女俩忍不住,抱在一起,呜呜痛哭。
那哭声掠过冰冷的雪面,在冷寂的二里湾上空盘旋。惊起了远处树丛中几只过冬的乌鸦,噶啊噶啊地叫着在雪地里跳来跳去。
银学和满堂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二人劝住,粉周妈提出想去那墓地看看,被银学和满堂拦了下来,“你就放心吧,被串串插这么一横杠子,也耽误不了多少,误不了明天的午时下葬。”
粉周妈犹豫了半天,勉强同意了银学和满堂的意见,擦了擦脸上挂着的泪,被粉丽搀扶着一瘸一瘸回去了。
满堂扭身冲着那挖掘机师傅挥了挥手。那师傅估计早等不及了,就在驾驶室候着,一看这手势便立刻发动了机器,小心翼翼地沿着串串的田地往墓地里开去。
机器挖得很快,三铲子、两铲子便挖出了墓地的轮廓。银学和满堂在那看了一会,又对三多子交代了几句,和那挖掘机的司机师傅打了招呼,也一起相跟着踏着积雪回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