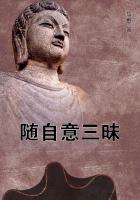2
车厘子被他的盲父跌跌撞撞地拽到家里时,他的那个狐朋释灵欢见势不妙早已经在半路上溜之大吉了。他看到一手拽着他一手推着车的他爹满脸怒气。此刻,他爹正坐在一张破竹椅子上,一言不发。车厘子站在门边更是不敢抬头。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让他爹去解救他了,以往不外乎是由于车厘子欺负了女孩子、小偷小摸的孩子式的淘气行为,可今天他犯的可是要命的事。车厘子也似乎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已准备好去接受老爹的一顿臭骂了。
可是老爹并没有骂他,只是默默地吸着水烟袋,呼噜呼噜的响。良久,只听他爹冷冷地问:“你那个牌子哪里来的?”
“捡的。”车厘子并没敢承认自己偷的事实。
“拿过来。”盲父命令道。
让车厘子庆幸的是,他爹并没有再去追问如何捡到的这个并不存在的事情,要不然还得费一番口舌去继续扯谎。车厘子好像是害怕他爹会追问似的赶紧从身上掏出那块白银的牌子,放在他爹身边的桌子上。
他爹的一双眼睛完全是瞎的,车厘子从小看见的他爹就是这个样子。他爹将牌子拿在手上,只是用手一摸,便将牌子摔在桌面上。
“拿这种玩意儿还敢去招摇撞骗?”车厘子听他爹这样一说,知道这块偷来的牌子肯定是假货无疑了,虽然父亲眼睛看不见,但是见多识广的父亲是不会看走眼的。想到自己甚至用这一块假东西就骗得那个酒糟鼻子一愣一愣的,车厘子在心底也不禁洋洋自得起来。
他用眼瞥瞥他爹,只见他爹的面色由怒转悲,叹口气说,“唉,你这样不学好,怎么对得起你的母亲啊?”
只要车厘子在外闯祸,他老爹到最后总是会搬出车厘子的母亲来说事,他对他爹无可奈何的老套路已经习惯了。车厘子小时候他的父亲就告诉他,说他的母亲刚生下他就去世了。车厘子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母亲,就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的难过。他有时想,自己甚至都不如释灵欢,虽然说释灵欢现在是一个孤儿,但是他母亲却还有一个在他伤心时可以去掉掉眼泪的坟头,可是自己的母亲却连一个坟头都没有留下。
车厘子忽然想起那些骑士在追查一个叫什么苏摩遮的人,就好奇地问:“爹,苏摩遮是谁?为什么骑士要抓他?”
“苏……摩……遮……”老爹好像在喃喃自语般一个字一个字地叨念着,又轻轻摇了摇头,却不置可否。
见父亲正在气头上,车厘子也不敢再多问了。
父亲的烟袋咕噜咕噜的响过一阵后,车厘子只听他爹随后说:
“看来,必须得搬家了?”
搬家?车厘子吃了一惊。虽然日子过得苦,但是这里有铁哥们释灵欢,还有那一些诸如鸢鸢一样他欺负惯的女孩子,要是搬走了可就不好玩了。
“为什么要搬家?”车厘子不解地问。
“因为,”他爹说,“因为,你已经被浮世镜照过了。”
“被那个破镜子照一下就得搬家?以前我还看见那些骑士们在大街上见人就照呢,还有,释灵欢也被照过了呢,他们怎么不搬家?释灵欢怎么不搬家?”
“你和他们不一样。”
“可是……”
“不要再说了!”父亲打断了他的话,没有给他再次说话的机会,并且斩钉截铁地说:“明天,搬家。”
院子里的地上散落着一地的水果,东一个,西一个,是刚才父亲进院子时用力摔下车子掉落的。他看到墙角栓的那只父亲买来跟他作伴的小羊,正拽直绳子想吃到眼前的那颗红果,由于绳短给够不着,急得小羊蹦来蹦去。车厘子走过去,拾起地上的那个红果塞到小羊的嘴里,小羊立刻安静下来,躲到一边啃嚼起来。
小羊啊小羊,爹说别人跟我不一样,也就是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小羊?
车厘子正若有所思地看着小羊吃水果的憨萌模样时,忽然发觉有人在门口一闪,他定睛一看,原来是那个逃跑归来的释灵欢,现在又来,想必是想看看自己在老爹面前出的洋相吧。他看见释灵欢在跟自己招手。
车厘子回头看看老爹正在犯困,烟袋也不抽了。他就蹑手蹑脚地来到门外,只听释灵欢在他耳边低声说:“听说抓住了一个狼人族的刺客,今天要游街示众,咱们不去瞧瞧?”
一听来了好玩的事,车厘子眼珠子一转,对释灵欢说:“你等我一会儿。”
随后,他再次蹑手蹑脚地进了院子,先捡起一颗红果塞到小羊的嘴里,然后又把三五颗红果放在小羊将够却够不着的地方,又蹑足进屋从桌子上拿走那块牌子,最后又轻轻走出院子。
释灵欢在门口看见车厘子出来,问:“一会儿你爹就发现你不在了。”
车厘子讪讪一笑说:“一时半会不会,因为院子里我留下动静了。”他说的当然是院子里他设计好的小羊的动静。
车厘子掏出那块牌子,对释灵欢说:“今天一定要把它卖掉!我就不信这个邪!”
他俩这次选择的是一家名叫醉仙居的酒楼,选择这家位于十字路口的酒楼,目的有三,一是在酒楼上居高临下,便于观看楼下大街上的游街人群,他们倒要看看狼人族的狼人到底长个什么模样;二是来酒楼的人非贵即富,都是有钱人,货好出手。
他俩从门口上楼的时候,顺手从一群酒足饭饱面红耳赤的人身上偷得了一块银子,现在全用在了他们靠窗而坐的那桌酒菜上了。别看他们不大,还没到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年纪,但是只要给钱,酒家掌柜的可不管这些。
他们边喝酒吃肉,边眼望四下,寻找着他们的目标买家。
这层酒楼上排满了酒桌,不少酒桌上的人们要么在高谈阔论,要么在划拳行令,要么在窃窃私语,好么在哈哈大笑,要么在吹拉弹唱,因为有一个弹琴卖唱的老头儿带着一个小女孩儿正在挨桌献唱讨钱。反正是乱哄哄的,好不热闹。
但他俩看到有一个例外,在不远处靠窗的一桌上,只有一个人,自斟自饮,丝毫不被周围的嘈杂所干扰。令车厘子惊奇的还不是他的定力,而是他奇怪的装束。只见他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背后背着一口黑把大刀,但从宽大的黑色刀鞘就能看出,此刀非一般的兵器可比。此人年纪并不大,顶多比车厘子大五六岁,面皮白净,黑眉朗目,左耳垂下缀着一个大大的银色耳环。此人我行我素的自斟自饮着,似乎身外的任何事都与他无干。
这时候,那对卖唱的爷孙走到他的那桌面前,老头儿躬身施礼,未及开口说话,只见此人掏出一锭银子,一甩手,那银子不偏不倚,正落在那个女孩儿手中托起的破瓷碗里,当啷一声,落入后,转都不转,牢牢地定在了碗底,似乎在碗里马上就生了根须一般。那老头儿先是一惊,随即赶紧拉着小女孩儿倒身便拜,如捣蒜般以示感谢。
眼前的这一幕,别人都没在意,只有车厘子看到了。他用手推推释灵欢,示意他他们的财神爷就在眼前,因为他目测了一下那人刚刚撇下的那锭银子,足足有十两之多。
那爷孙俩千恩万谢的去了。
又待了一会儿,车厘子瞅准机会,来到那个刀客的桌边,大言不惭地扯过一把凳子坐下了来。嘴里说:“这位兄台,请了。”
那刀客似是没有看到有人来,更似是没有听见有人说话,还是缓缓地自斟自饮。
车厘子还想再说什么,刚一开口,还未说出一个字,只见桌面上已然多出了一把长刀,那刀是什么时候从背后结下的,是怎么放下的,快如疾风,迅如闪电,车厘子根本就没有看清。
车厘子再看看那刀客的脸,只见那刀客镇定自若,双目微垂,好像车厘子根本就是他眼前的一阵毫不起眼毫无意义的风,仍然手端酒壶将壶中酒缓缓倒下,继续轻酌慢饮。
好古怪的家伙!车厘子心想。虽然那刀客直到现在都没说一句话,可是车厘子还是感受到了来自面前的巨大的压力,一种几近窒息的压力。他晃晃脑袋,心想,总不能被他的气势给压倒吧,好,那就看我的绝招吧!
车厘子从怀里摸出那块银色的铭牌,“啪”的一声,一下子就摔在了桌面上,可是须臾之间,他又快速地将牌子收回在了腰间。他是一个惯偷,从别人身上偷取东西已是迅疾无比,神鬼莫辨,从自己身上拿点东西放点东西那自然是更加迅捷了。他做完这一系列的动作后,微微晃着脑袋,眼睛斜睨窗外,那神情自是洋洋得意。
也许是看到那块牌子,也许是看到车厘子迅疾的身手,那刀客手中端着的酒壶和送至唇边的酒杯竟微微地顿了一顿,眉梢一挑,也望向了窗外。
车厘子心中正自暗笑,刚想开口说话,忽然听见楼下大街上一阵人喊马嘶的声音。循声从窗口往下一看,只见从十字大街南面黑压压过来一队人马,因为那些马上的骑士都是一身的黑色装束,头盔、铠甲、盾牌、剑鞘、马鞍都是清一色的黑色,如暴雨前的一团浓重的黑云,滚滚而来。他们是黑铁骑士。
看来是押解狼人族刺客游街的队伍过来了。
在酒楼上吃喝的人们,都停箸伸脖,甚至是挤到窗口往下观看。车厘子也在队伍里寻找那个狼人族刺客的身影,他要看看狼人到底长个啥样?他看了半天,才在密密匝匝的队伍中间找到一个囚车,因为囚车是黑色的,狼人所穿的衣服也是黑色的,难怪让车厘子找了半天。
在队伍的前面是十几个开道的军士,手持盾牌短剑,驱赶着街道两侧拥挤上来的人们。后面是八对骑着黑马手持长矛的黑铁骑士。在他们的后面是一匹红色的鸑鷟鸟,那鸟兽高大威猛,五彩的羽冠神采飞扬,上面端坐一个身穿红衣服的年轻人,赤兽红装在队伍中格外显眼。
车厘子正看得发呆,忽然感觉眼前白光一闪,自窗口一闪而过。再看看自己桌旁的那位刀客已然不见踪迹,原来是其飞身跃出了酒楼。
这时候释灵欢也挤到车厘子身边,搂着他的肩头一起往下看热闹。车厘子忽然想到了什么,用手一摸腰间,那块铭牌早已不见了。
车厘子大惊失色,那块假铭牌丢了倒是无所谓,主要是他丢不起这个脸,他自诩在上都城里偷遍全城无敌手,现在自己竟然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了东西,这让他以后可怎么混?他想了又想,刚才释灵欢到来之前,只有那个刀客在自己身边,对,肯定是他干的!
车厘子和释灵欢往楼下一看,那个刀客现在已经稳稳地站在队伍的前面了,只见他双手抱着肩,一脸不屑地挡住了骑士们行进的道路。
最前面的几个开道的兵士见状,都将木盾短刀挡在身前,做好围攻准备。后面马上的黑铁骑士们也都将手中的长矛紧握在手上,只等那个骑着红色鸑鷟鸟的赤衣人下达进攻命令。围观的人们见到这种架势,都纷纷躲到远处去了。
可是,双方一直在静静地对峙着,都没有发起进攻。
一群恋春鸟倏忽飞过,从空中带下来一阵微风,将那刀客的黑色长发轻轻吹拂了起来,如几缕翠堤的柳丝,在空中飞舞。
“辟疆大人,下命令吧。”其中一名黑铁骑士按捺不住,对那个赤色衣服的年轻人说。
人们这才知道,原来这个身穿红衣骑着红色鸑鷟兽的年轻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辟疆,他是帝国国王呼獠王的义子,掌管着五十万宫廷禁卫军,大名鼎鼎的辟疆,无人不知,只是人家贵为皇亲国胄普通百姓只能望闻其名,那得有缘相见?今天一看,才知道这个辟疆竟是如此年轻神俊,英武不凡。
辟疆轻轻一抬手,制止住了那位黑铁骑士的问话,只是轻轻拔出腰间的长剑,缓缓将剑刃指向那个刀客,轻声问道:“你是何人?”
拿刀客站姿依然没有丝毫不变,像一尊冬天里的雕像,冰冷而坚硬。
“涯——破——”那刀客缓声说道,虽然声音不大,但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异常清晰,可见此人内力的强大。
那个在黑色囚车里的狼人族刺客原本是被黑布蒙着眼睛的,现在一听见刀客的声音,就疾呼一声:“涯破,救我。”还要再喊,马上就被旁边一名兵士当头抽了一马鞭,被迫住了口。
“涯破?你就是涯破?号称狼人族第一勇士的涯破?”辟疆问道。
涯破轻哼一声:“请问你的辟疆之名是真是假?”
一名黑铁骑士听涯破这样一说,立刻就想擎刀策马冲将过来,被辟疆的一个眼神给制止住了。
眼前的一切,车厘子在酒楼上看得一清二楚,原来那个拿走自己铭牌的刀客叫涯破,他转头对释灵欢说,“哎,盯住这个涯破,无论如何也得要他还了咱们的牌子……”
大街上人未动,马未动,刀剑未动,但剑气却越来越重,直刺天空。
又一群恋春鸟盘桓而来,越来越近,如一片白色的云朵飘了过来,忽然像是被剑气所惊般飞快地俯冲下来,在人们身边扑棱棱疾飞而过,吓得人们都赶紧抱头遮面。
正在恋春鸟疾驰而过的刹那,原本对峙的双方突然间有了动作,一阵刀剑撞击之声瞬间不绝于耳。
恋春鸟飞走了。
车厘子看到,在那群恋春鸟飞走之后,街面上除了满地的断刀、断剑、碎盾和蜷缩呻吟的兵士,黑色囚车空了,原本伫立于原地的涯破也不见了,只留下一串恋春鸟飞过后的暖暖的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