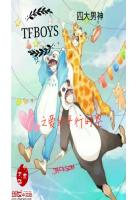他便存活到了昨天,嘴巴念经一样念念不忘。在走廊在教室在课上课下。车轱辘话碾压得耳朵都感到平坦裸露得就剩俩洞洞了,到处是拿着问题和拿着篮球走来走去的人群中看见凌雪在冲她笑,他的心也放下了,头不出汗恢复了他大脑正常运转脸上笑得很乖。很挤的距离,许生挥洒汗水擦着走廊楼梯,李晓彤赶着上楼,嘴里挂着一连串的英文。没有对许生说一句话,目光只静静投向她耳畔冒出汗珠从身边擦过,没有喊住他,他转身洋溢着没有烦恼的笑也没有叫住她,静静的看着她,就那样的看着她。
不再像往日那样贪玩,好像她们都很忙,来得越来越少。少得明明快要和李晓彤相遇明明眼神快凑到了一起,都来不及打招呼,就随着钟表一秒一秒划过的指针消逝了。
忙里偷闲的时候,也没有空去看彼此相爱的人,不知是昨日的感慨激发了灵感,还是明日的离别不想再见。但愿真的是。。。真的是暂时的离开,不然谁能忍受那晴天霹雳的煎熬。但,如果遇错了人,长痛不如看电影。人生的哲理有时是从哪里出来的,即便有虚虚美言,权且安抚自己吧。人嘛,不是大神,病了可以不用药,心病吃药也不顶事,毕竟生活哪里都有可能蹦出几句良药苦口,吓出几句善意谎言,冒出几句好听话。看在大战在即的份子上
比起红色的奋斗条,红色的情书确实在雪白的卷子中数不清是多少份子。外露的不要,悄悄的送到。
一天天的消逝眼看快来了最后的寒期,学习成了他的唯一,凌雪对我说下午会来,可惜我们班老是很忙很忙的阵势,她就在门框外偷偷看着他认真了就放心的溜走了,许生似乎也很满足,没有感到老天对他不公平。静下心来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家过得很认真,,枯燥乏累就揪揪头上的草,托托下巴、耍耍笔才等来冰冷的走廊传进耳畔听到的电铃声,那是可以让我们透心爽的雪碧。它有时候很沙哑,我们不会天天去看它,有时候路过仅仅瞄一眼而已。它知道我们心里装着它。
忽觉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到了寒假,老师也没有留太多太多的作业,大家的心情渐渐好点儿了吧。
“真到了放假,”凌雪听着广播不知是谁发出的声音,都不小心笑出了声,搞得周围人看她,笑得老师都要问到底,
“放假了放假了。。。。。。”
喜悦声中爆发出了强烈的磁场,好像明日便是中考结束,跑的、跳的、扭的、喊的、叹息声、感慨声、铿锵声、默言声。
放假了,真的放假了,时间总是会有急促的心跳,也有用阴晴的温度来表达它的慵懒。寒冬好像真正才来临了,某些人应该值得高兴吧,下得周围成了一片片雪岭,银白的肤色反照到天上,阳光沐浴着它们,这是在给它们理理头上多余的白发?
捧着一杯咖啡站在天台上,痴痴地看着云彩在顽皮马上要遮住阳光,就被许生拽下来同他去理发,滑着脚步五分钟就可以到,半道许生和我还遇到一对双胞胎姐妹,许生失脚滚了下去,闭严的门狠狠被他撞开,进的很顺利,门也狠狠合上了。好像他明明不会进去的,是门补了一刀才让他如此顺利。
我滑了下来,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但不知道为什么有着很亲切的感觉,脚下的印记很眼熟,很快它在流不尽数不清的小雪花下埋没了,再也看不到。门突然打开了,吓得打了一寒颤。风把门吹开了,里面果然好熟悉。
“你怎么了来了,来理发吗?”
“嗯,你也来弄啊?”
他在和凌雪聊天,原来这是她家开的店,“走走走,我们出去。”凌雨打了个哈欠,看着不远处几步就到的最矮斑秃的雪山,好有趣的俊俏。
雪花飘荡在两个人的中间,没有了间隙只好欣然落到了肩上,为他们祝福。又不知不觉隔了距离,来晚的雪花没有了机会,奋力也没有落到的也只好擦擦肩,站在风条的晃动下看着他们的神情好像不像是情侣啊。
凌雨冻得紧紧地靠着我,很像粘在了一起。他们在前面为我们清雪,凌雨也不罢休,还冻得呻吟了起来,我实在无法接收她的怪音,只好依了她,把围巾给了她,幸好俺的大衣是毛领子,“给我。。。给我。”在她偷偷开始奋力要扯下我的大衣的时刻,雪停了,她又把快要湿透的围巾丢我一脸雪。
浩大的雾浓,看不清对方,望眼不见踪影,头顶上一处好像是筋骨的松林,郁绿的屹立在山峰旁没有挡住怀远绿色前行的数不清的千里眼,雾流动,忽然比刚才清晰了许多,没有窒息在看前面好像不知道我们在后面,一会拉着手,一会给对方留下了能装三个人的距离。玩个捉迷藏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