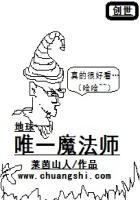那是一个寒身的春天、也是一个寒酸的春天,据说这样的春天已不是一年两年了。
就在这个春天的正月初九十一点左右,一个湘西北的丘陵地带,张家界和慈利城的中段,距离澧水河谷不远处的山台上,一只破旧的木屋青瓦房下,“(⊙o⊙)哇、(⊙o⊙)哇”,一名婴儿的哭叫声惊动了这只小屋的左邻右舍。
我,很不情愿地降临到这个世界。
“呃,好冷,外面怎么这么冰凉?”我打了两个寒颤,第一次感觉着这样的世界——饥寒交迫。两只小乳**换着一个劲地踢着,想一脚抖开寒冷的空气,抑或是要争吵着重返妈妈的卵巢。然而却永远也回不去了。这时的我,若是有丁点欣慰的话,那就是我的抖动和哭泣,给母亲带来的痛苦的面容,略显了一丝微笑。邻舍的伯娘婶婶们看到我的降生,也紧张的帮着忙这忙那,一个劲地呵护着我。这又让我多少嗅到了人间的温情和暖意。但这一天我不知道是阳天、阴天、雨天还是雪天,但肯定是寒天。那是公元1956年,中国的大地是社会主义的大集体,人们生活贫穷困苦是第一大特征。我的出生让家里有了六口人,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我。这时的父亲在离家50多公里远的县城药材公司工作,大哥8岁、二哥6岁、姐姐3岁,于是生产队里的出工和家庭的打理就全落在了我妈妈一个人的肩上。那么,这个家的负担沉重、日子寒酸应该是可想而知了。我张开眼,怎么也记不起周围的环境,妈妈脸上的笑容?打补丁的蚊帐?缺口的澡盆?喧闹的瓦屋?室外的霜冻还是雨雪,抑或是冰冷的阳光···
我想,所有婴儿出世的第一声哭闹,为什么会成为必然,那是有千万个理由的。比如:惧怕陌生、创碰凡界、不舍襁褓、诉说憋屈、惊扰上苍、娇哭求宠、宣泄个性、不满现实···
我出生的年代,吃的真的是大锅饭的年代,叫“集体食堂”。我住的那个村子小地名叫杨家台,拾多户人家一百多号村民组成一个生产队,占用一户村民的房子作为生产队食堂,全生产队里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一起吃饭。所有的成年人和绝大部分大龄儿童白天进行着生产队里的大集体劳动。一年四季创作出的劳动成果,供着全村子里人儿吃着用着,并还向国家交着公粮。这儿的人吃的用的还全都是生产队的自给,但又不能自足。主食是稻谷、麦子、红薯,主菜是萝卜、白菜、瓜果。吃饭时按人按工(劳动工分)定量凭票,到月尾了家家总是缺几天饭票,家里只有种一些小菜作为补充。记得我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饿得好厉害,可家里没有饭票了,妈妈说要给我煮青菜吃,我实在是不想吃,就发脾气捡起一颗小石头朝妈妈扔去,“我不吃,我打你”,可妈妈没怪我,就叫大哥给我到食堂去借饭,饭当然没借着。我还是一个劲的哭闹着,妈妈一边哄着我,一边就把收藏的一点点葛粉全给我冲调吃了。然而妈妈他们全都吃青菜。在我的记忆里,生产队里的食堂好像只开一两年就没有再开下去。把粮食分到各家各户,让村民(那时叫社员)家庭自己盘算着吃。可是,饭,还是吃不饱。每到新年的春末,青黄不接时,几乎家家都断炊,那就天天吃白菜、兰头,全村子好几十号人吃得全身水肿。记得有一个远房伯伯水肿病严重,无钱医治,给活活的肿去了。生产队里的儿童们一个个都吃的肚子大大的,而手脚四肢却细细长长的,像一只只大肚子的蚂蚁漫画。这时的糠粑、野菜也成了粮食。糠粑吃多了,大便都解不出,当人蹲在茅厕,那副憋胀的面容,表现的就是对这个世道的憎恨和厌恶。野菜、野果子也有更难吃的,我们吃的那种野菜煮稀饭,那就是典型的猪臊味。有一次,我的两个哥哥在山里打柴,肚子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找到一树血桑子野果,饱吃了一顿,哪晓得回到家后,又是呕吐,又是拉肚子,整整折腾了两天。这种吐、拉,也不正是对这个世道的吐槽和宣泄么!
农民们住的是木瓦屋,灰黑而陈旧,看上去就是一种旧时道的延续。木板拼装的屋壁稀稀拉拉漏出不少缝隙,夏天,烈阳扫射着每间居室。冬天,寒风穿透着整栋房屋。屋下的主人不能改变什么,却也不埋怨什么,因为他们连饭都吃不饱。还有住茅棚屋的,那就更是穷酸样,茅草的屋顶,干枯霉变生虫,老鼠做窝。逢上下雨天,那就是房外大雨,内屋小雨,屋里地面上摆满了家里倾其所有的盆盆钵钵,叮叮当当的漏水声响彻在整栋茅房,溅满水后的地面湿泥巴一直延伸在床脚底下。碰上大风一刮,房顶就掀开了,一家人只好卷缩在一堆躲避风雨、相互取暖。这样的茅屋,还必须三两年翻盖一次。否则,茅屋垮塌,你就会流离失所。
人们的穿着普遍是土棉布,并且补丁加补丁,大小孩穿着大人们的陈旧褴褛衣服,弟弟妹妹穿着哥哥姐姐不能再穿的破旧童装。我们的衣着和叫花子比,没什么两样,只是没有那么脏而已。每个农家还有那棕麻蓑衣、篾制斗篷和稻草编鞋一应俱全。劳动工具是锄头、镰刀、犁、耙、牛、箩筐、背篓、石碾、石磨、石舂···
我想,这一切大概与封建社会没什么两样。
这年代,说是穷苦人翻身解放了,也许是我没有经历的某一方面吧。唉,我内心的感觉还是穷啊、苦啊,真让人辛酸和寒颤。
当然,新中国诞生也就十来年,旧时代千疮百孔,百废待兴。那不是十年就能解决的,我能理解。但总不应该让人们年年饿着肚子干“集体”、过日子!
这时的我,哭多了,人们也就习以(为常)置若罔闻了,妈妈更腾不出多少气力哄我了。
人们的麻木,我索性不哭,谁能渴望伟人新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