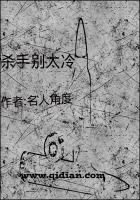一、借船实习
一九五五年夏,我从武汉市一中初中毕业后,为争取早日能挣钱养家,没考高中,报考读书不收学费的中专。却名落孙山。正在无策无颜时,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武汉河运工人技术学校。这也是不收学杂费,而且吃饭住宿全免费的学校。算是好运气光临到了我的头上。
这是一所由长江航运局主办的,仿苏联伏尔加流域类似的河运技术学校,用以培养一批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的专业技术工人,来充实日趋发展的长江内河航运事业。生源由长航局所属的上海、芜湖、武汉、重庆四个分局,及沿线各个港务局的职工部分应往届初高中学生子弟为主,及驻地部分中考落选生,还有若干从志愿军部队退役的转业军人或调干生。学校是创办期,校长由长航局张明局长兼任,专职副校长是人民九号轮的张船长担任。全校设五个专业十个班。
这所座落在武昌喻家湖畔的技校,因长江干线航运发展用人在即,学生速成结业后,即可上船顶岗。一改历来师傅带徒弟的旧式传帮带制度。在我看来,这算是为我这样的贫寒学子,开辟了一条快捷就业的生活出路。
我一九五五年八月入学,进了轮机内燃机班,次年八月结束在校学业。以十七岁的年龄,离开校园,踏入社会。开始了寻求养活自己和家人的生涯,担当成年人的社会责任。相较于我已故的父亲,他在这个年龄,尚逐日徬徨街头或做学徒、打小工压得吐血的凄惨遭遇来,我真是个幸运儿。这所学校第二年就搬迁到江苏南京继续办。“文W革G”后期,这所学校升格为大专院校了。
离开校园,走向务工,其实是我最无奈和最不堪的选择。读技校不收学费,吃住不要钱,一毕业就上船挣钱,马上就可以养家活口,却是我当年最紧迫的需要。又没什么无奈和不堪了。那时母亲没有正式职业,为抚养我们四个子女,只有抛头露面为人佣工。为街坊大户人家洗衣浆衫,令我心不忍不堪。在我上船工作前,母亲还在北京路一个里弄为人家做媬姆,一个月工钱十一二元,加上街道办事处一个月救济金八九元。除了我,还有三个年幼的妹妹,靠这二十元维持生活,实在是苦不堪言。所以,我渴望挣钱,以帮助含辛茹苦、守寡多年的母亲,来抚养三个幼小的妹妹长大成人,以期摆脱每月到三官巷内街道办事处领取救济金的狼狈场面。尤其不想看那街干部递钱给人时,那令人难堪的眼神。虽然,政府发放救济金,体现的是国家对贫困穷人的体恤和关怀。但我始终想避开那令人羞愧的姿态。我自幼就处于弱者的地位,它养成了我低眉顺眼,敛息倾听的习性,让人没有了自信心。我一直想挣脱它,男儿要自当强,要有血性。要靠自己养活自己,赡养家人,天经地义,责无旁贷。揣着这种心境,我急盼早日上船。
岂料好事多磨,当学校通知我,到汉口民生路江边,长航武汉分局船员调派科时,遇到了不省心的事。班上的同学,依来校前的地籍大都哪来哪去。上海、南京、芜湖各地籍的同学已经分回去了;重庆、宜昌籍的同学也已走了。就是武汉籍的几位同学愿意进川的也去了好几个。还有几位分别去了青山船厂、长江航道局、长航燃料站、武汉港。到后来,只剩下我和何宗远、张时来、柳英联四个人时,人事调派员关任远告诉我们说,武汉分局大马力内燃机船己配满了实习同学,只剩下一两百匹马力的小拖轮和交通船,问去不去?我们大失所望,开始挑肥拣瘦,因为人多,我们有四个人,仗着抱团群胆群威,好说歹说,软缠硬磨,赖着不上小船。让关先生也觉得船太小,作业量太少,养老倒适合,于年轻人没什么好处,就没勉强我们去。他答应找武汉港借条大船去实习。条件是,实习期满后再回分局,到那时有么船就上么船,不得讨价还价。我们只好点头答应。几经他联系,说是武汉港船舶办公室有大马力拖轮可以让我们去实习。于是我们一行四众,急匆匆地到武汉港船舶办公室,又简称“船办”的人事股,开了实习调条,一起上了港作船长江1003轮。在长江1003轮实习三个月,即从八月中旬到十一月底,期满后,又回到关先生那里去了。又经过一番折腾,讨价还价,到了年底,那三位同学先后分配上了汉宜线区间班轮民享轮、分局工务交通船和港务监督1号艇。而我则请求调到武汉港船办去,再次回到实习过的长江1003轮。由长航分局调到港口,有人说我糊了心,是自甘吃亏。其实这也是我当年必然的选择。因为母亲怕我这个独生子漂泊在外,她心不安,怕先失去丈夫,再舍弃了儿子,留在港口是最佳选择。
我重上长江1003轮当加油,直到两年后的一九五八年底。船进上海浦东造船厂大修,我才起坡回船办,等待另行安排工作。这艘船是我踏入社会人生的起点。船上轮驾两部门的船员,又多为富有航海经历的江浙人氏,船来汉后又补充了若干本地船员。我初入社会,就结识许多见多识广,饱经风霜,沧海人生的外乡人,令人眼界大开。丰富多采的口音,远胜同一乡音,意态雷同的小圈子。说得直白一点,那些异乡同事,待我这满口汉腔的小伙伴,亲切得不得了。开口“阿弟”,闭口“小弟弟”的叫唤着。而船上同是汉腔汉调的同事,对我要冷淡多了,有的还要找我的麻烦。这人群性情上的地域差异,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虽非天壤之别,却也悬殊得不可思议。
举一个小例子吧。一九五七年三月,我刚转正,同事们吆喝着要我买喜糖吃,分享我转正的喜悦。我到商店买了斤把什锦水果糖。开完班前会,拿出来放在餐厅长桌上,请同班师傅们尝尝。几位江浙籍的老师傅一人取了两三粒,还剥开糖纸塞嘴里,还一边说,味道蛮好,“真崭”。而一位汉腔的老舵工,却不顾还有人没拿到糖,竟不管不顾地把桌上的糖果,一把把地抓起来,塞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几乎一粒不剩,扬长而去。令我目瞪口呆。
长江1003轮,当年是武汉港马力最大的拖轮兼消防船,名气也大。要上这条船的人也特别多。我在船两年间,进进出出的船员多达四十几位,而船员编制定员不超过二十五六人。时至今日,我虽已年过七十四,离开这艘船已然五十八年之久,可几乎所有同事的姓名都记忆犹新。许多同事上船不到半年又调离了,有的与我同进退,直到五八年底船进厂才分手。他们中不少人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乃至家境状况,至今还令我难以忘怀……我不久前还曾戏作一首七律,将同事的名字编排成趣。我至所以喋喋不休地叨念这些同事,除了怀旧寄情,其实还想证明一点,即我记忆力之强势,离痴呆尚远矣。
————
二、惜遭埋汰
我想,在这里简略回顾一下长江1003轮的前身后世。
长江1003轮,按长江内河港口作业的船舶算来,当属马力大、吃水深、拖力强的拖轮,且具备救捞、消防、抗风等特殊功能。它能抗九、十级大风暴。是艘适洋过海的拖轮。它来武汉港之前,就是上海的海上救捞船。却困于长江内河港口,确实埋汰了它的能力,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也。
它建造于二战后期的一九四四年,它的两台主机“恩特普莱斯”铭牌上就镌刻1944年号,主机为四冲程柴油机,每台637匹马力,木壳船,长约34米、吃水3。7米。型宽型深的具体尺寸我已不复记忆。主机并不直接连接尾轴带动推进器,而是带动直流发电机,经配电柜程控,再驱动两部串联直流电动机运转,通过离合器带动尾轴推进器。两部直流电动机功率换算均为五百匹马力。即使两台主机失灵,它强大的蓄电池柜储蓄的电能,也足以保障船舶航行一两个昼夜。机舱右舷设有两台功率达二百马力的离心式高压消防泵机组。只是由于使用它的机率少,我甚至连如何启动它的程序都没见过。算是我学艺不精,我无法确切知道这消防泵究竟有多大排水能力。
全船的电气化程度很高。采用电动液压舵,船首两部大功率绞锚机、绞缆机,船尾亦有电绞盘,收紧钢缆也是电动化。驾驶台顶端还有大功率探照灯、摩斯信号灯。这种装备在当时的一般拖轮上是很罕见的。
我们这一代人,按如今流行的说法,“80”后的,“90”后的,我是“30”后的一代。在青少年时代,受过的教育说,当年蒋委员长是个“运输大队长”,把美国人援助他打共产党的飞机、大砲、枪枝、弹药、坦克、军舰,都拱手送给了共产党解放军。这长江1003轮,也是美国人在二战后,军援***打内战的战略物资之一。在****国G军J”的海军序列的“中华民国”编排中,“中”字号即大型登陆艇,“华”字号即中型登陆艇,而像长江1003轮这一类型的拖轮,则归为“民”字号。据老船员告诉我,长江1003轮原来就叫“民331号”属救捞船。下面还有“国”字号的小马力船,只是我没有见过。解放后,这些在长江内河的船,交由长航局统一接收使用,成为早期国企的主要生产资料,那些“中”字艇、“华”字艇,更名为“人民”号并编以序号或“沱江”、“涪江”号。我记忆中,大约只有一艘“中”字艇叫“金沙江”号,一直沿用到报废。“中”字艇的型体,同前些时央视屏幕上,出现过的菲律宾蕞尔小国,企图吞并仁爱礁而坐滩的那艘破烂舰模样相同,只是要小些而已。
我说它是军用改民用,许多人恐怕心存疑虑,但我却找到确切的印验。那年,长江1003轮,呆在上海沪东船厂码头待修已五年多,主机更新计划迟迟没有着落,船办领导也非常着急。他们不知听谁说,驻沪海军某代号单位的装备库里有储备的柴油机,与长江1003轮主机“恩特普莱斯”同机型。领导上就急切要机务股去联系,看有否调拨或转让的可能,以谋求解决长江1003轮待厂换机事宜。机务股谢股长要我前往。他以同学名义写了封信,央其在长航上海分局任职的同学缪女士帮忙。向她介绍我的使命,请她出面找上海分局办公室开介绍信,派我去驻沪海军某装备单位的仓库。至所以绕这么个圈子,是怕部队单位给外地单位吃闭门羹,毕竟同城单位有军民联谊关系好说话些。那家军用仓库在军工路上,我居然找了进去,管库人员接待了我。也听了我的情况介绍,但他明确地告诉我,库存确实有“恩特普莱斯”柴油机,甚至还有配套的辅机“布达”柴油机。但不能整体外拨,易耗件尚可少量调剂。事没办成,空手而归。但确验证了我当年的猜测。
类似长江1003轮这样的美国造,“中”字艇也好,“华”字艇也好,长航局多用作主力货轮。这些船马力大,续航能力强,而且舱容量大,前者载货量一千五,六百吨,后者也在六百吨以上。特别是华字艇,马力在三千匹以上,进川江过险滩急流不用绞滩,单船就可自航过滩,而且还可绑带八字头的满载驳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船的主机、辅机型号是清一色的美制GM系列柴油机,零部件互换率高。这些船舶,在长江干线一直使用到八九十年代,船龄普遍达到四五十年。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客运站工作期间,有几年的春运,由于客船运力不足,长航局还批准使用中字艇,开统舱运送旅客返乡。而在没有零配件供应的情况下,长江1003轮成了例外。它的寿命只有十四五年。
最近,时事报道说,美军卖给菲律宾的二手舰船,是在美军中已经服役四十年以上的旧舰,估计卖给菲军后,至少还可以服役一二十年没有问题。为什么同为美国造,长江1003轮与之有如此悬殊差异?以我的观察,究其原因至少有三。
首先是人的因素。当然不是指人的人格品质,而是指操作者的随意性。举个例子来说吧,当年船上配备有供拆装主机缸盖的,有紧力刻度的套筒扳手。每次检修缸盖螺帽时,需要三个人同时用力紧固。所以,需要把握拧紧螺帽的力度,用这副套筒扳手可以控制力度,以防止因过紧或过松而影响机器的正常运转。每次检修时使用它,应该是很必要的。当年张连发轮机长就累次用它来紧固缸盖螺帽。后来,他调到远洋公司上了海轮。后来的继任轮机长、大管轮,他们在检修时,就不用这套工具了。只凭个人手感和经验,不按规定操作,不按科学方法办事。这说明使用者的层次,处在随意性上。
其次,是适航的问题。这条船的尾轴套筒是铁梨木制的,不是金属材质,因而具有良好的耐油性及防海水侵蚀。可它却不适于内河水域。因为江水含有大量泥沙,泥沙沉积渗到套筒里,对尾轴产生磨耗。磨损后的铁梨木套筒,与尾轴之间的间隙就会不断扩大,导致江水渗进尾轴舱形成积水,一旦积水涌进过多,危及船舶安全。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时,船进438厂,即武昌造船厂,起坡修船。就是为了解决这尾轴套筒渗水的问题。
其三,是船体、轮机的零部件没有替代品。长江1003轮是木质船体,无论船壳、龙筋、龙骨、身底板,全都是美国木料,武汉的几家船厂要拆换一块船壳板,都难以找到替换材质。由于当年美国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对华实施极其严厉的经济制裁,根本不允许任何美制设备、配件向中国出口。所以,船上轮机设施及易耗零配件找不到更换件。当时,我在机舱当班时,就多次看到张连发轮机长在机舱工具间,对喷油嘴的柱塞进行研磨调试,就像挪用物品似的“十个坛子九个盖”,调过来换过去凑合着用。
这样一来,这艘适洋适海的船只,困顿于武汉港,陷入无用武之地。尤其是一九五七年间,还发生一次左主机飞车失控的机务故障。再后来,又发现左主机出现曲轴裂纹,加速了它的损毁。以致出现五八年九、十月间,被安排进上海沪东船厂作基大修,即更换铁质船壳,更换主机的更新工程。我以为,这样的工程项目的提法,只是为保留船籍的,一个遮人耳目的说法而已。
后来,机缘让我为长江1003轮的存在,尽了最后的心意。一九六五年冬,我参加八机部(即农机部)在北京虎坊桥饭店举办的,全国性的生产资料潜在物资调剂会,奉命在北京停留期间,找交通部基建司,去申请到六机部(即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前身)的联系函,联系落实长江1003轮更新主机的计划指标。主要是申请落实,由上海柴油机厂生产的两台6350型柴油机,及两台4135型柴油机的主、辅机指标。几经交涉,终于得到六机部的批准。并按六机部的批文,又赶到上海,找到六机部华东配套办事处落实供货指标,把长江1003轮主机更新落到实处。我又到浦东,找到长江1003轮新任的熊轮机长等人交付落实计划,让他们尽快联系厂方主修完成调拨计划。
那天,新派去留守的驾驶部的船员钟某人,看我南来北往马不停蹄地奔走,还专程陪我过江,在西藏中路一家汤圆熟食店,接我吃了一碗上海汤圆。至今我还记得那碗汤圆的味道真好。回汉的第二年,我已被调到港务局机关去了。再过一年,长江1003轮以崭新的面貌,从上海回到武汉港。此时已物是人非了,与我没有了任何相干。
如今,长江1003轮尚在何处,我已无从打听了。只是我难以忘怀,它是我踏入社会的摇篮和起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