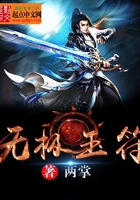车停在一个岔路口,四周雨水茫茫,分不清方向,看看时间,已经晚上七点了。
三人在车中犹豫不决时,雨却停了,夜空中繁星密布。忽然,北斗星中突然出现了一颗妖异的红星,闪了一下,迅速消失不见。
“看,前面有灯光。”苏俏惊喜地指向左边的岔路。大约二百米外,有一片星星点点的微弱灯光,赫然是一个小小的村落。车子开到村口再也无法开动了,满满一箱油竟然一滴也不剩。司机嘟囔了几句奇怪后下车,走到亮着灯的农户家,敲开门,说了什么,便垂头丧气的回来。“我问了,最近的加油站在国道上,有二十公里。我这一宿只能在车上过了”司机道。
“那我们只好去村子里借宿了。”孟轻云看着苏俏。
“好吧。”苏俏答应道。二人从后备箱拿出行李,向村子里走去。
村里的路铺的都是青石板,星光在水洼里晶莹夺目。
孟轻云敲了敲亮着灯的农户家的门。门内一阵窸窣,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低声问道,“不是说了嘛,加油站离的远呢。”门吱呀一声开了个缝,探出半个脑袋。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看见孟轻云,愣了一下。
“对不起,我们从外地来,因为赶路遇上大雨,迷路了,能不能借宿一晚。”孟轻云客气地问道。
中年男子打量了一番孟轻云,刚要开门,忽然看到孟轻云身后的苏俏,脸色一变,“哐当”一声关上了门。孟轻云和苏俏不由地一怔,看来这家人戒心很重。
顺着青石板路,走了大约二十来米,孟轻云又试着敲了敲一户的门,门开了,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男人左脸颊一道疤,黑夜里显得狰狞无比。男人一嘴酒气,醉醺醺地问道:“谁?干什么?”
“对不起,我们迷路了,想借宿一晚。”醉汉恶狠狠地瞪了二人一眼,重重的把门摔上,隔着门大声喝到:“老子就是一个人,还见了鬼了!”说完便没了声响。
孟轻云,苏俏相视苦笑。
前面不远有一家亮着灯,孟轻云敲门,门里传出一阵男人的喘息声,接着一声呻吟,隔了片刻,门内走出来的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男人的皮肤苍白,但脸色却泛着潮红,好像刚刚很兴奋的样子。
男子打量着孟轻云,忽然看到身后的苏俏,目光一下子古怪起来。
“什么事?你们是外地人吧。”男子盯着苏俏。
“我们是外地人,迷了路,想借宿一晚。”孟轻云连忙说道。看这个男人委琐的样子让人心里很不舒服,可是也没办法。
“咳..咳..你们?不行不行不行,你们另找别家吧。”男人说完也不等孟轻云解释,把门关上,只是恶狠狠地的盯了苏俏一眼。
孟轻云刚要转身走,男人忽地打开了条门缝,隔着门缝道:“这里不欢迎年轻男女,要是一个人的话还好,哎呀..多嘴,莫怪莫怪。”门又紧紧关上,听到男人在屋内不停地自言自语:“莫怪莫怪。”
孟轻云和苏俏感到这个村子透着古怪,可又说不出来有什么不对。
又找了几家,只要一看到门外是一男一女,都把门紧紧关上,还不停地“晦气晦气”地嘲骂着。就这样由村南头走到了北头,就剩最后一户人家了。远远看去,门缝里透出屋内明亮的的灯,让人心理一阵放松。
敲了敲门,屋内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老人很和善,问明了原因,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唉,进来吧,想你们也无处可去。”
二人走进屋,看到屋里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姑娘模样倒是清秀,只是口角流着口水,痴痴的盯着屋顶明晃晃的灯泡傻笑。
老人招呼二人坐下,斟了碗水,递给二人。
“我是这里的村长,姓洪,老伴死的早,这是我闺女,从小这里有问题。”村长指了指脑袋说。
“洪村长,谢谢您了,我们赶上了大雨,迷了路,只好在这里借宿。”孟轻云道。
“是啊,洪村长,问了十几户人家,都把我们拒之门外了,真是谢谢您了。”苏俏连忙道。
“唉,其实不是村民门小气,而是不敢啊。”洪村长叹了口气,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们看着像坏人吗?”苏俏问道。
“不是的,姑娘。我们这里穷乡僻壤的,就是来了坏人,怕也给穷跑了。”洪村长解释道。
“哦?那是什么原因?”孟轻云好奇地问道。
“唉”洪村长叹了口气,“你们敲开了几户人家,难道没发现,村民没有年轻人吗?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啊。”
“是啊,您这么一说,真地没见到年轻人。”苏俏点头道。
“我们这个村子啊,是受了诅咒的。”洪村长神情黯然,又有些紧张。
“啊?什么诅咒?到底怎么回事?”苏俏紧张地问道,自从医院里看到诡异的一幕后,苏俏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着世人所难以想想的东西。
“这要从十五年前说起,十五年前,我们村和别的村一样,人丁兴旺,全村有六七百人。那年..”洪村长讲了一个故事。
十五年前,这个村是附近十里八乡有名的富村,周围的姑娘都争着往村里嫁。有一年,村东头的王家娶了一个姓刘的姑娘,叫刘秀妹。要说这刘秀妹是这些年嫁进来的姑娘里最漂亮的一个,又贤惠,姑娘媳妇都喜欢她,王家小子也能干,跑起了运输,日子挺红火,可就是有一样,小两口一直没孩子。时间一长,就有人说闲话,说王家小子不行。王家也是着急,可越是着急,越怀不上。闲话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到最后竟然还有人说因为王家小子不行,刘秀妹和别人好上了。王家打那时开始,对刘秀妹的态度开始慢慢不一样了。刘秀妹受了不少委屈,终于有一天,小两口子吵起了架,刘秀妹气地直哭,把两口子的照片都给撕了。有一张两口子结婚的照片,不知道为什么刘秀妹竟然拿剪子把照片里丈夫的脑袋给煎下来了。王家小子也是气昏了头,开车出去一夜未归。第二天,派出所来人了,王家小子出车祸死了。一个小面包坐了六个人,五个人都没事,就死了一个。王家小子死的很惨,车在路上翻了,王家小子的脑袋被车和树挤碎了,身子却好好的,连衣服都没破。
刘秀妹看着丈夫的尸体,眼直勾勾的。直到火化那天,刘秀妹都没哭一声,回到家,当天晚上就上吊死了。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警察在对刘秀妹进行尸检时,发现,刘秀妹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王家一连受到如此打击,老王头第二年一口痰没咳出来,活活给给憋死了。老伴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儿子儿媳,老伴儿,还有没出生的孙子,一个接一个的没了,老太太隔了没一个月,也病死在医院里,跟着老伴儿前后脚走了,原本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就这么给毁了。
刘秀妹横死,死之前又收到流言蜚语的冤屈,传说这样的人死去会带着极大地煞气,结果,刘秀妹也没埋到王家的祖坟,王家只是在过了村外五里的白水河,在河对岸的树林里埋了刘秀妹。可是,自从刘秀妹死了第七天开始,村里开始每个月都死人,都是在,死的都是年轻的丈夫,尸体都找不到头,而死亡时间都是每个月的阴历十五,十五那天,月亮最圆,也是阴气最重的时候。
村里人这才慌了,而死了第三个的时候,年轻夫妻们都搬走了。有人说,死人的那三家,半夜里都有人在大门口哭,是个女人的哭声,一定是刘秀妹死得屈,回来报仇,因为闲话都是从这些小媳妇嘴里传出来的。打那以后,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谁也不敢回来。而村里,剩下的都是上了年纪的和没结婚的光棍,混混。
缺了人丁,村里的活没人干,也就慢慢穷成今天的样子了。
大家都认为是刘秀妹的鬼魂作怪,村里也从外面请来几个道士和尚,可结果,三个道士,一个和尚,去了刘秀妹的坟作法,结果都没出来那片小树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不过,自从村里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夫妻搬走后,村里果然再也没出过事。
讲完故事,洪村长叹了口气道:刘秀妹死得屈,整个村子也跟着遭殃。
“是不是村子里的人以为我们是夫妻,怕留宿我们惹来祸端啊?”苏俏问道。
“三年前,一对北京来的小夫妻,迷路借宿这里,半夜里,男的就失踪了,第二天发现死在村外的水沟里,脑袋也不见了。那个小媳妇一路哭回了北京。唉..”洪村长又叹了口气。“打这以后,就连遇到外人,只要是年轻的,村民们就绝对不敢再让留宿了,毕竟,死在谁家,谁都觉得晦气。”
“那您为什么还同意我们住在您家里?”苏俏问道,心里有些害怕,紧紧拽着孟轻云的胳膊。
“你们不住这里,还能去哪里?这里都是山路,黑灯瞎火的,你们在山里更危险。”洪村长说的对。
“洪村长,我们不是夫妻,只是好朋友。”孟轻云安慰地拍了拍苏俏的手,向洪村长解释道。
“那好,那好!”洪村长放心道,“要知道你们不是夫妻,别人家也不会拒绝了。”
“可是,我这里..你们只能住一个屋子里,我闺女有夜游症,半夜会掐人,你们只能在对面屋将就了,现在的年轻人,没那么多在意的。”洪村长一番话说的苏俏脸通红,心头如小鹿撞坏。
村长拿出了两套被褥,笑呵呵道:“将就吧,这算是最干净的了。”
接过被褥,孟轻云笑道:“太客气了,给您填麻烦了。”
“不麻烦,不麻烦,不早了,不打扰你们休息了。”洪村长出去的时候,把房门轻轻带上。
苏俏接过孟轻云手中的被褥,铺起床。我这不像妻子给丈夫铺床吗?想到这里,苏俏的脸更红了。我这是怎么了,心中顿时局促不安起来。
看着孟轻云一边淡淡的笑容,苏俏心头涌起一丝失落。孟大哥对我很好,也很细心,却好像对什么事都是这么淡淡的样子,唉……
苏俏忽然感觉根本看不透孟轻云,或者孟轻云似乎隐藏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