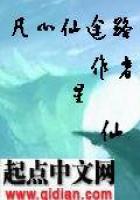“啪、啪”两记响亮的耳刮子声响了起来,小凤压在嘎子的身上,嘴角处还在慢慢的流血,随着天空黄昏的余光斜洒在木棚边上,数十条细线顶端悬在顶棚上面,垂洒落于地上,而其中的一根线上,还栓着一颗根部带血的白色牙齿。
“嘎子你混蛋!呜呜!”小凤一边哭一边将嘴里的淤血吐在硬邦邦的土地上面。
雷锋没做成,反倒成了罪人,嘎子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小凤呐,这也不怪我啊,我这不是怕你上吊嘛”
说话之际,这小子赶紧用自己泛着油光的棉袄袖子去给小凤擦嘴,这不擦还好,一擦,小凤哭的更厉害了“滚!离我远点!”
说着,她连推带嚷的把嘎子给哄出了院门,其实这事也怪嘎子,也不想想,自己那棉袄袖子是专擦鼻涕的,这没事要往小姑娘嘴边噌,那不是擎等着挨骂嘛。
“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再说啦,你不是上吊,你弄这么多绳子干什么啊!”嘎子在门口一边嘟囔,一边好奇的向院里面张望,确实不知道这棚子上的好几十根细绳是做什么的。
“编绁都不知道,真是个混子,要是没你爹,你早饿死了!滚滚!”说着,小凤一下子关上了子家的木头门,既而咕噜一声,还别了插棍,这让嘎子瞬间觉得没了面子,不过自己到也不太在乎这个。
小凤自己在院子里找来凉水漱口,随后又把被拽掉了的下槽牙扔到了房顶上,这是村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上槽牙掉了埋土里,下槽牙掉了仍房上去,其实主要是心理安慰,虽说有个讲,如果把下槽牙埋到土里,或是把上槽牙仍在房顶上,新的牙齿就不会长出来了。
在处理完自己的牙齿之后,小凤对着门口又愤恨的骂了两句,自己这牙掉的太冤了,要是没嘎子,自己也不至于有这样的遭遇,所以心里一想起那双不大的三角眼就狠咬槽牙。
小凤这个工作是编绁,这月刚开始接手,这个工作是村委会从位于京西郊的一家编织厂那里接到的活,这个工作适合村里的妇女座,每天编两根,便算上一天的工分,如果多编一条,就能拿到几毛钱的额外奖励,这个编织程序很复杂,三十二根线并排悬挂在房梁上,并且在编之前,还要先给这些线打上一遍蜡,之后要十个手指跟嘴都得用上才能将绳子编出来,小凤手巧,素面的能编,带花的自己学学也能编,最主要的是自己每天都能多编出一根赚几毛零花钱。
那个年代的人的思想和现在的可不一样,那时候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琢磨赚钱的事,没本事的踏踏实实赚工分,有脑袋的要琢磨一些外块,但在八十年代初期,外块这种事,在农村是很难的,毕竟条框太多,弄不好就违法,但无论哪样,他们都十分乐意将休息的时间换成金钱,而嘎子则是,很讨厌将时间换成钱,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兜里有几毛够去县里的百货商场买布头的就行了,至于赚工分之外的赚钱路子,并不适合自己。
嘎子在赚工分的手艺上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秋收的时候,自己轮开手中的一把镰刀,能把左右两拢割麦子的竞争者远远的落在身后,自己则是长长以此为吹嘘的资本。
这几天嘎子比较自由和享受,因为他的大哥和二哥都去了邻村挖沟,挖沟这个活在那个年代是纯人力操作的,能干这活的都得是各村年轻的棒小伙子,几把大铁锹,一个小推车,便能成立一个突击小分队,干的狠的小队,真是拉车的飞奔,身后的用铁锹铲满土快步跟上,随着小车离近土堆,身后跟着的抬锹,将铁锹里的土高高的抛出去,最后车里的土和铁锹里飞出去的土能同时落在土堆上,但这样一次两次成,要是一天全这么下来,任他身体多棒,要散架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苦活,也是挤破脑袋抢着干,为什么,因为挖沟管饭,而且是馒头,并且在满工分之外,还要给几毛的奖励,纵然是累,但这个工作的待遇,就当时而言,那是真不错。
嘎子的大哥在挖沟小分队里面比较老实,一天到晚除了干活就是看书,但是他的二哥就没那么老实了,挖沟之余的最大乐子,就是带着本村的小伙子和邻村的对着干,工作时候看着都十分本分,可这一动起手来才知道,没有谁是善茬
铁锹什么的往沟里一扔,纷纷跑上沟沿的草丛里,顺手一胡啦,棍子、鞭子、镐把子,十八般老样式的传统兵刃那是应有尽有,尝尝是餐饭过后,某个村的小伙子和别村的小伙子一犯照,随着一声招呼,双方身后立马能聚齐数十个光着膀子的小伙子,随着几句骂声开始,有手黑的就从地上摸起石头往对面人群扔过去,跟着便是一阵大乱,双方对着一冲,散了的就跑沟上面的草丛里找事先藏好的家伙,赢了的也去找家伙,跟着又是一场械斗,最后是谁手黑谁占优势,手不黑的经常被开了脑袋。
嘎子二哥是这里的王者,自己不仅手黑,而且力气还大,把别人打的跪地求饶是常事,他的名气一天大过一天,最后连挖沟小队的队长都得给他几分面子,否则他就消极怠工,他一怠工,就有一大帮本村外村的年轻人跟着怠工,这进度一慢,小队长是要被上级骂的。
这两个哥哥不在家,嘎子的伙食量自然分配的多了一些,最起码的,自己的饭菜不至于被二哥切走一部分,而且不用给大哥跟二哥刷鞋了,他在家里的地位最低,虽然老太太宠他,但也不敢当着大儿子二儿子面给他好吃的,这下好了,他不仅足吃,还能偶尔吃到一个煮鸡蛋了。
第二天早上,嘎子在张宝贵的叫骂声中起了床,穿上自己的那身稍显肥大的衣裤,塔拉着大毛窝,打着哈气,跟着老爷子的二八后面,一路小跑的向锅炉房冲了下去。
睡前,老爷子给他敲定的月工资是二十,标准是全厂最低的,但这二十元的工资已经让嘎子的眼睛放光了,但还没等他乐出来呢,老爷子后话跟上了,每月给家里十八元,留给他两块钱零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