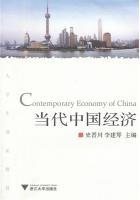漆黑的密室,伸手不见五指,偶有女子微弱的抽泣声传来,顺着水声滴答滴答,让人觉得一阵毛骨悚然。
密室外,花姐双膝跪地死死拉住王婆婆的裤脚:“婆婆,我求你了!求你了!怜儿必竟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她不懂事我会教她,无论如何,请婆婆看在我的面子上饶她一回,我保证她下次再也不敢了。”
王婆婆面色阴冷,额头青筋迸露,似在压抑着极大的怒气,一身黑衣称得她像极了地狱的勾魂使者,她有些厌恶的看了看哭花了嘴脸的花姐:“花姐,你是个明眼人,怜儿犯了多大的错你不是不知道,你觉得我饶了她,主上会饶过我吗?”
花姐惶恐,松开拉住王婆婆裤腿的双手,怜儿今晚固然有错,但罪不在死,不知道王婆婆为何如此震怒,这中间会否还有其他隐情?
“好!婆婆如果一定要惩戒怜儿我无话可说,但怜儿罪不该死,请婆婆饶她一命!”
王婆婆轻拉嘴唇,一抹古怪的笑意在面上漾开:“我看你是在飘零楼舒服日子过惯了,竟不知道怜儿所犯何事,你这侄女聪慧是聪慧,但就是太过耍小聪明了。”
花姐疑惑愣愣看着王婆婆:“怜儿心气强,花魁竞选她确实锋头太过了,但是清灵姑娘艺压全场,所幸也没坏主上大事。”
“如果她只是犯这点小过错倒也无伤大雅,大不了将她送入哪家府邸伺候几个糟老头,但是她错就错在生了不该生的心思,你这个侄女好大胆啊,想着花魁落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居然企图在覃国使臣的杯里下药,然后再来个投怀送抱!”王婆婆越说越来气,这楼中好久不曾出现过如此胆大妄为的人了。
花姐一个踉跄摊倒在地,不敢相信怜儿竟然背着她去做这等事情:“不可能,不可能,怜儿不会这么大胆的,而且我并未告知她覃国使臣就是覃国的三皇子覃子睿,她不会做这等傻事!”
王婆婆冷笑:“她不知道那是三皇子?我看未必,这丫头今天说什么也不能留了,我们樱云会不需要这种不听从安排的探使,念在你的面子上,我留她个全尸,你也不要再纠缠于此了,再过上半个时辰进去给她收尸吧!”
“婆婆!婆婆!”花姐还想说些什么,但很快被王婆婆身边的两名黑衣人架开。
王婆婆调头欲准备离开:“你也收拾一下情绪,此事如果再闹腾下去,怕是主上连你也不会留了!”
花姐无力靠坐地上,泪水沾湿襟衣,静静听着怜儿在密室内发出一阵一阵撕心裂肺的凄叫声。
从密室出来的王婆婆,换掉了身上的黑色长衫,对镜理了理有些凌乱的发丝,脚步沉稳朝姚清灵屋内走去。
屋内的姚清灵已经等了三个时辰,茶水已经喝了十杯有余,她舔了舔依旧干润的嘴唇,内心的焦躁越来越明显,不知道清云清韵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她已经如约按他们要求夺得花魁,对方到底会不会食言?
“姑娘久等了!”王婆婆踏进房门,给姚清灵微微行礼。
姚清灵起身,王婆婆坐在圆桌的对面,二人相互打量了几眼,终是姚清灵忍不住先站起来,她走到门边开了门,屋外郝少波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
“少波,你先下去休息,我和婆婆聊点事情!”
少波一脸担忧的看了看姚清灵,继而又斜眼瞟了瞟屋内正襟直坐的王婆婆,一脸的不情愿退下。
姚清灵关上门,屋内只剩她们二人:“婆婆,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急着找婆婆过来,是想马上知晓我那俩位姐妹的情况。”
王婆婆但笑不语却答非所问:“姑娘是要做大事的人,这般急躁不耐不是可取之计,我既已经答应姑娘,就一定会信守承诺,姑娘大可放心!”
“诚意!我要看到你的诚意!”姚清灵字字逼人,不怒而威看着王婆婆。
王婆婆倒也不怒,从袖内掏出一封信纸递予姚清灵。
信是姚清韵写的,从信纸及信上工整清秀字迹判断,写信之人应身处和境并无大碍,信上内容简单,无非就是一切安好,姐姐勿躁等,但从头至尾并未透露她们二人身处何地,姚清灵笑笑,将信放在桌上。
“婆婆真会戏弄人,还是婆婆觉得我姚清灵好戏弄,一封没有署名且无法判断的信你就想要我相信你?清灵不笨,婆婆还是别拿清灵打趣了。”
王婆婆给自己倒了杯水,不急不慢:“现在这个情境,你信我也罢,你不信我也罢,或者你还有第三种方法?”
说时迟那时快,姚清灵右手夹住婆婆还未来得及送至唇边的茶杯,稍稍提力,茶杯磕在桌沿边上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王婆婆愕然,既而露出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清灵姑娘好手法,又快又稳,我老婆子居然一点防犯都没有。”
姚清灵浅笑:“婆婆过奖了!我知道这飘零楼里都你们的人,我不能拿婆婆如何,但是命是我自己的,我既已夺得花魁对你们定是相当有用,试想一下,如果我死了,而且是死在婆婆手上,你说接下来的戏会不会很好看?”说完,她蹲下身子挑了一块大片的茶杯碎渣拿在手里把玩。
王婆婆一阵心惊,这丫头远超乎她算计,看她刚才说话那股狠劲,怕是真的有可能说到做到,而且她也分析得确是没错,她既夺得花魁确实每步棋都走得万无一失,如若真在她这里出了什么差子,主上的怒火怕是谁也顶不住。
“清灵姑娘好胆识也重情义,那两个丫头也是有福气能遇上你这样的女子,你这招威胁确是对我有用,如果姑娘愿意再信我一回,就请姑娘放下手中的利器,我保证再过上不用三天,姑娘一定会见到你的姐妹。”
姚清灵端详对方不似说谎,再说了她也只是想吓她一吓,不会真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利落的将手中的碎渣片丢在桌上,拂了拂衣袖好整以暇的看着王婆婆。
“姑娘今夜献艺实属辛苦,不妨这两日就好好休息,三日后就是玉后的册封大典,届时姑娘以舞伎身份随我一同入宫,自然你就会见到姚清云和姚清韵了。”
入宫?姚清灵皱眉,朝堂之上,后宫之人,哪个不是权倾朝野一身富贵,那些个龌龊还有勾心斗角历任朝代都屡见不鲜,如果说此番穿越到古代她最怕什么,无非就是入宫,一入宫门深似海,对于这个陌生的朝代她完全一无所知,就算有现代人的智慧怕是也寸步难行,但是不入宫,清云和清韵会怎么样?她不敢想像,姐妹是她到古代来的第一个软肋,她做不到那么绝情也没办法绝情。
“婆婆让我入宫意欲为何?”
王婆婆喝水,这一次她总算是安心喝到了茶水:“无意欲,你只要将今日在花魁竞技上的舞艺在大殿上献于天子,剩下的事情我们自然会安排。”
姚清灵苦笑,献舞?如果让她顶着李贝文的模样献舞她倒是无所畏惧,但是这姚清灵生得倾国倾城,一舞下来怕是要大乱,她想过藏拙,只是这等貌相只怕是藏拙也无法掩盖其光华,一时间感觉陷入阴霾之中,前路一片迷糊看不分明。
“哦!对了,这是这个月的解药,明日就是十五了,该是樱毒发作的时候,姑娘趁着睡前服下此药,明日可少些痛苦。”王婆婆想起什么,从内里掏出一个白色瓷瓶,瓷瓶内只有两颗黑色药丸。
姚清灵接过药丸,想起那日白衣女子给她下的樱毒,算算时日,明日果真是十五毒发之日,无力感和愤怒再次涌上心头。
与此同时,正从飘零楼出来赶往云来客栈的途中,一辆全身黑色又华贵的马车内,覃子睿和杜云帆相对而坐。
“你说今晚也真是扫兴,咱们花了五千两白银居然没迎来清灵姑娘,倒是把那怜儿姑娘迎了过来。”杜可帆打量着对面黑脸的覃子睿,哪壶不开提哪壶。
覃子睿冷眼扫了他一眼,想到先前屋内出现的怜儿,衣衫半裸满眼春色的模样到现在都让他感到一阵恶寒,还好他不敬酒色,否则还不知道会怎么着了那女子的道。
“依我说那怜儿姑娘也是秀色可餐,只是眼神不太好使,像我这等翩翩君子她居然没看上,硬是褪了衣衫只为你这根木头,可惜真可惜!”杜可帆一脸失之可惜的模样。
覃子睿冷哼一声:“那女子显然是知晓我的身份,否则怎么会左一口三皇子右一口三皇子,我见也是包藏祸心之人,识破她是为你好,要依你这脾性不早上了人家贼船。”
杜可帆微微叹气:“唉!也不知道那老鸨会不会将玉佩送给清灵姑娘?我可是亲眼见着清灵姑娘进了那姜若岩的厢房。”
不理会杜可帆,覃子睿掀开车帘,寂静的街道上杳无人烟,马儿吐出的冷气在夜色中生生打了几个圈,他一个快身从马车上闪下,只丢给一脸无可奈何的杜可帆一句话:“马车这东西我坐不惯,你慢慢享受,一个时辰后客栈见。”
杜可帆捂着胸口不忘再嘲他一句:“你最好不要回来!”
姚清灵独坐室内,身上还穿着那件来不及脱掉的蝶裙,一闪一闪的烛火将她面色映得通红,她小心翼翼的从袖内拿出那块黑色玉佩,先前匆忙来不及细细观察,这会在烛火的照耀下,玉佩月芽一侧一个清楚的覃字映入眼帘。
覃国之人?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