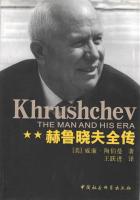“娘子,你‘热脸贴个冷屁股’,纵有万般风情,人家对你不理不睬,你是枉费心机了。”掌柜的看来也不是甚好鸟,一对狼狈为奸的狗男女。
“哼!我‘毒手娇娃吕娇娘’出道十几载,勾魂摄魄从未失手,这个愣头书生不解风情,是他的命数尽了,但我要他死还未简单到一刀杀了他的地步,我要剜了他的心!”
刘伯温无言以对,只得怪自己时运不济,自寻了一条死路。
一股黄烟带着奇香从屋外吹进,当刘伯温闻到香味,心中暗叫不好,但为时已晚,他瘫倒在地,人事不省。
他感觉身在迷雾中游荡,昏昏沉沉的,突然,周身上下一凉,好似坠入了冰窟中。
他睁开双目,一张杀气盈天的脸映入眼帘,正是“毒手娇娃吕娇娘”,旁边一张胖脸也是凶光毕现。
两张脸离刘伯温不过尺余,刘伯温恨不能张嘴一人咬上一口,他挣扎着想要坐起却发现手足都被捆,根本动弹不得。娇娘握一把寒光闪闪的牛耳尖刀,挑破刘伯温胸前的衣裳,露出白嫩的肌肤,用刀尖比划比划,高高举起,就要将刘伯温开膛破肚,剜出他的心来。
刘伯温心里一翻个儿,完了,完了,“出师未捷身先死”。自己死不瞑目,但也只能把眼睛闭上,不想再看见人世间这两张丑恶的脸。
老半天过去了,刘伯温并未感到撕心裂肺的痛,大概是刀太快了,自己死了还未觉察到,再一想,这不对劲呀。他用力一睁眼,不禁被眼前的情形吓住了。
那两个凶神恶煞之人如木雕泥塑般立着不动,“毒手娇娃吕娇娘”握刀的手还高悬在半空。掌柜刚才还得意扬扬的脸此时却是神情错愕,适才发生了什么事?刘伯温再看时发现了异样之处——两恶人的咽喉俱被利器刺穿,血已滴湿了衣衫,两人分明已气绝身亡,怎么尸体不倒呢?刘伯温刚想到这儿,“扑通”“扑通”二声,两具死尸向后栽倒,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传进耳中,笑声未绝,一团粉影只一闪,便站立在刘伯温的床前,手腕上还系着两条白练,调皮的笑挂在嘴角,目不转睛地望着刘伯温。
只能用又惊又喜来形容刘伯温此时此刻的心情了,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刘伯温朝思暮想牵肠挂肚难以忘怀的小师妹——朱珠。
“珠妹,你该不会是从天而降吧?”又见到亲人的刘伯温喜不自禁地问。“温哥,你一向可好啊?怎会落到这步田地?”
“你这死妮子!快与我解了绑绳,让手脚松快松快。”被人捆得如死狗般的刘伯温很不好受。
朱珠双手背抄,在屋内转圈踱步,改作慢条斯理状。
“为你松绑,这个容易,举手之劳,不过……”朱珠故意拖长声腔。“不过什么?有话快讲!”刘伯温恼不是不恼也不是。
“不过我有个条件!你答应了我,我便放了你,如若不然……”
“嘿嘿!你这小蹄子,竟敢威胁我,我就是不允,你又能把我怎样?”刘伯温有心不理会这小孩子的把戏。
“师哥,我的条件未曾说出,你便恼了,你这样太不好玩了嘛!”朱珠又是撒娇又是卖嗲。
“够了,够了,快讲你的条件吧!”刘伯温怕她再玩新花样。
“就是……就是允许我伴送你进京赶考。”
“是师父派你来的?”
“嗯……”朱珠“嗯呀”半天也未“嗯”出个所以然来。
“你肯定是背着师父,私自下山。”
这边仍旧支吾不语。
“师父觉察了有你好果子吃?怎么像个孩子似的,做什么全由着性子。”刘伯温板着脸孔语调言辞也激烈起来。
朱珠低头不语,双手不停地绞腕上的白练。她一边听着师哥的斥责,一边感到自己一片苦心如此地不值钱,眼泪便拼命地往下掉,哭得如“一枝梨花春带雨”,谁人看了不心碎!
刘伯温本还想再痛责几句,一见师妹伤心欲绝的样子,刚硬起的心肠也就软了。
“好了,莫要哭了,为兄答应便是了,不过男女相伴,一路多有不便,你须女扮男装才可,此外,凡事不可任意胡为,要听从我的安排。”
这女子的泪水来得快去得更快,脸上虽挂着最后一粒泪珠,却是欢天喜地过来替她的温哥解去绑绳,口里喋喋道:“呶,这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逼你。我答应按你的吩咐去做,你可不许赶我走!”
“你不知道那天你走后,人家心里多么牵挂你,我想你都快想疯了,那日师父外出访友,我一人孤孤单单地待在山上,后来,我心里就像腾起一团火一样,什么都不管了,下山来找你。其实,我跟在你后边已好几天了,想让你知道又怕你赶我走,所以一直悄悄地跟着,今天多险呐!幸亏我及时赶到……若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自己也活不下去!……”说着,一头扎进刘伯温怀中。
刘伯温心中纳闷儿,分开还没几天,这小女子竟变得如此婆婆妈妈,咳!女人真是难缠,不过,难得她的一片痴心与好意。
别后重逢,恋人的心中都升腾起火焰,虽然口中的话语远没心中的炽热,但彼此的心意无须点破便各自了然于胸。
刺鼻的血腥味很快让这对恋人从醉人的激情中清醒,尸陈于地、血流成河的场面确不是别后话情的场所。
“温哥,你看该怎样办?”
刘伯温稍加考虑,便有了主意,说道:“这‘福来老店’是个谋财害命的肮脏之所。现在,奸人已死,不如放把火,将这里化为灰烬,倒落个干净,珠妹,你看呢?”
“好,天快亮了,我俩早些动手,免得撞上官司,惹上麻烦。”
不久,熊熊的火光冲天而起,木头爆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火星四溅,用不了几个时辰,这个杀人魔窟就会变成除断壁残垣外便是灰烬。屈死的魂灵或许会在这烈火中得到超度,该死的恶徒大概也会在此中彻底丧失他们的肉身。
朱珠与刘伯温早已起程,火光中的“福来老店”已成为他们身后的一个亮点。
他俩一路急急地走,直至天大亮,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估计城邑就在前方不远处。走着走着,珠妹突然拉了拉刘伯温的衣袖,悄声问道:“温哥,为何旁人看咱俩的眼光怪怪的?”
刘伯温瞧瞧朱珠,再看看自己,心里便明了几分,对朱珠低声说:“人家以为咱俩是星夜私奔至此的野鸳鸯。”
朱珠让“私奔”二字臊得双颊飞红,脸上热辣辣的,嗔怒道:“休要胡言乱语,没遮掩。”
“此乃实情也。孤男寡女,尘霜满面,行色匆匆,携东带西,路人焉不会起这样的疑心。不若这样,你先换上一套我的衣服,扮作我的随从,衣服宽大不适也只好将就些,待进城中,再作打算。”
朱珠思量一番,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只得去路旁的避人之处乔装一下。
待她再回到大路上,娇小的身体裹藏在刘伯温宽大的衣装内,处处都富余得很,一顶布帽将秀发藏起来。刘伯温粗看,倒有几分男人相,再细细端瞧,那高耸的秀峰、粉嫩的脸又难脱女子的神韵。刘伯温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先对朱珠耳语一番,朱珠面上初露为难之色,后咬牙应下来。
刘伯温从行囊中找出墨块,又往掌心吐了口唾沫,将墨块蹭了几蹭,随即把满手乌黑都涂抹在那张粉嫩娇美的脸上。可怜,刚才还是位肤若雪花、貌如天仙的佳人,片刻之后便成了脸赛锅底、惨不忍睹的恶神。
不久,二人便置身于城中大道上南来北往的人流中。他俩在一家名为“悦来客栈”的门口站住脚步,刘伯温朝朱珠一使眼色,朱珠心领神会,用一手扶着额头,宽大的衣袖遮去大半张脸,刘伯温一旁搀扶着进了客栈,冲着伙计大声说:“找间上房,我这位同伴身子不适,需赶紧休养!”
店伙计见他呼喝甚急,慌忙不迭地将他俩引入一客房内。刘伯温吩咐道:“我的同伴需要静养,没有我的召唤,不要前来打扰。另外,城中离此最近的药店在何方?我好去寻几味药来煎与他吃,在我未回来之前,什么人也不许进这房间!”说罢,顺手扔给店伙计几两碎银子,小伙计一见银子,心中乐开了花,赶忙说:“听爷吩咐,一切按爷说的照办!您问最近的药店,出咱们客栈,向东拐,走不多远便可望见‘宝林堂’的招牌,爷可写下单子,小的替爷跑腿。”白花花的银子就是好使,小伙计一个劲儿地献殷勤。
“嗯,这个不必了,还是我亲自走一趟吧,你先出去吧!”
“嗯,好哩!有事您吩咐,有事您吩咐。”小伙计满脸堆笑,边说着边退出门外将门带上。
在一旁装模作样的朱珠见刘伯温如此煞有介事,一直强忍着笑,小伙计刚走,她便想痛快地笑出来,却被刘伯温的手势止住,只好紧咬双唇,将满腔笑意咽进肚中。刘伯温对她讲,他要出去片刻,让她先在床上休息。
朱珠躺在床上没多久,便酣然入梦了,连日来的奔波劳碌,特别是昨夜惊心动魄的遭遇及星夜兼程,身子确已乏透了,待她醒转过来,屋内已点起烛火来,刘伯温在灯下拥卷读得津津有味。望着肩宽腰圆的刘伯温全神贯注在书卷中,朱珠不禁意乱情迷起来,暗想要是能与这个人举案齐眉,做他夜读添香的红颜知己该有多好,可她实在不知那种日子何时才能盼到,自己有没有那个福分……
“唉!”她发出一声叹息。
这叹息声让刘伯温把目光从书卷上移开,关切地问:“珠妹,你什么时候醒的?看你睡得那样香甜,我一直没敢惊动你,肚子肯定饿了,你先躺着,我叫伙计将饭菜送到房间里。”
工夫不甚长,饭菜茶汤便摆了满满一桌,流香四溢,勾人馋涎。两人早已饥肠辘辘,谁也没客气,这一个狼吞虎咽自不必说,那一个比往日的细嚼慢咽要急了许多,投箸送筷如暴风骤雨,没多久,桌上的山山水水皆见了底。朱珠放下筷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另一个,另一个则专心致志摸索着最后的“残兵游勇”,许是一片青菜抑或一粒肉丁,找到后,向口中一抛,有滋有味地嚼了起来,完毕,目光仍盯在狼藉的杯盘上,口中却幽幽地说:“干什么眼睛老盯着我不放?”
自觉失态的朱珠脸飞彩云,嘴头上却不肯认输:“你未看人家,怎知人家在看你,真真的自作多情。”
刘伯温抬眼看了看她,嘿嘿一笑,说:“你那两道目光如火,都快把我烧焦了,我又怎么感觉不到?”
这话先是羞得朱珠脸上的两朵彩云顿成火烧云,将头深埋于胸,后又眼含笑意抬头看刘伯温,理直气壮地说:“就算看你又怎样?只不过你是这间屋里除了我以外第二个喘气的活物罢了。倘若这屋里有什么阿猫阿狗的,人家才不会稀罕你!”
“哈哈。”刘伯温不禁爽声大笑,心想这小女子真是刁钻得可以。
“我刘伯温看来真是不值钱,不过却有人不远千里赶来相救,唉,这口是心非并非我刘伯温一人专好。”
“好个狠心贼,薄幸郎!得了天大的便宜还在这里卖乖。只顾自己建功立业,却不管人家愁长思浓。你说,这段日子你想我没有?”
儿女总是情长,英雄难免气短,刘伯温与朱珠这一夜情话绵绵,直聊到三更时分,一个伏睡在桌上,另一个则在床上昏昏地睡去。
待他一夜醒转,外边已是天色大白。他挺直腰板,一床锦被从肩滑落,不知何时珠妹为自己披上的。抬眼向床上望去,却是空空如也,不见了珠妹的身影。
“吱呀”一声,门外进来一人,面如冠玉、神清骨秀,眉目间自有十分的风流倜傥,纵使潘安、卫介再世,也要自愧不如。好一个俊秀潇洒的书生!刘伯温不由得心生艳羡之情。那俏书生向他躬身施礼,念道:“兄台,现已日上三竿,愚弟以为该是你我上路之时了。”
刘伯温心中正纳闷儿:这书生一身上下的衣冠鞋帽与昨日为珠妹所买的竟是一丝不差,这一开口,却是极力效仿男子雄浑之声。此人不是珠妹又能是谁?
刘伯温不禁哑然失笑,又将珠妹上下前后打量一番,赞不绝口。
“看来,日后我要称你为‘珠弟’了。”
这一日,他俩直奔岳阳楼而去。
路途中,刘伯温有心考问师妹,问:“珠弟,你可知岳阳楼的由来?”
一听这话,朱珠便知师兄用意何在,不过是要摆摆其渊深的学识,故朝他翻了翻白眼,咬文嚼字地说:“小弟才疏学浅,胸无点墨,还望兄台不吝赐教一二!”
刘伯温清清嗓子,像开馆授艺似的讲了起来。
“这岳阳楼最早是三国东吴鲁子敬,就是鲁肃,他练兵于此所筑的阅兵台。后来,唐开元四……”
他这一“年”字尚未出口,却被朱珠打断。
“……中书令张说遭贬任岳州太守,沿原址构建了一座精美壮观的楼台南楼,后来改名为‘岳阳楼’。师兄,我说的对也不对?”朱珠讲这番话时,目光散射,似是漫不经意道出,但却麻利极了。说罢,朝刘伯温顽皮一笑。
死妮子,敢戏耍我,真是无法无天。刘伯温心中暗想。
“珠弟含才不露,愚兄眼拙了。杜工部、李太白、白乐天都有佳词绝句,不妨你我二人一道温习,我念上句,请贤弟接下句,可好?”
另一个笑而不语,点颔称允。
“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杜甫作于大历三年,题为《登岳阳楼》。”
“雁引愁心去。”
“山衔好月来。李太白题《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珠弟真是好记性!再听我出‘春岸绿时连梦泽’。”
“‘夕波红处近长安。’兄台,下边一联我只记住半边,望请兄台续全,‘猿攀树立啼何苦’。”朱珠飞快地反将一军。
“雁点湖飞渡亦难。”刘伯温毫不迟疑,将下句应声而出。
“兄台果然学识过人,折服了小弟。你看,前边莫不就是岳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