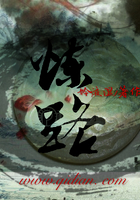雍亲王对这个女儿心中只有愧对,若不是因他这父亲,也不至于到今日此地步,明明风光锦绣前程,不想今日竟至此。
此乃皇命所致,他为臣子不可逆,自家女儿与母家命运本就牵连在一起。
雍亲王心中再是疼惜也无法。
他神情当中愧疚,王妃皆看在眼里,好言道:“王爷不必为女儿心有愧疚,既为暮家人,该与暮家共同分担才是。”
而后继续道:“西暇云暇皆已入宫了,入宫也有半月时候了吧,妾身听闻消息,咱家云暇已升为女官之位了。”
暮云暇从来做事勤谨,她是一出挑女子,雍亲王待她自然放心,听闻已晋封女官之位,心中欢喜,面上才露出些笑意,“云暇她这女子不会错,无论至何地何时,皆不必人担忧。”
自小暮云暇便是在父母夸赞之中长大,而她的确也是精明强干,王妃将带来披风披至他身上,“咱家的女儿,即便身处逆境,凭借自身也可改变。”
这二女儿,从来都是要雍亲王省心的那个,他所担心是暮西暇,跟着问道:“西暇如何?你可有她消息?”
王妃与暮西暇并无血缘亲情,在她在王府当中,也是将她视为眼中钉,此时她入宫为侍,王妃平日里担忧丈夫,与她那亲生女儿还不够,怎会顾及她呢。
“一切无碍,想她在宫中又会有何事。”王妃平声道。
她根本少有关注暮西暇动向,更是不知皇后已将暮西暇从尚寝局中分离开来。
“也罢,此时这两女皆在宫中,本王这做父亲的,也是护佑不得。”雍亲王哀哀叹了声。
他为先帝在时罪臣,虽此时因新帝登基而脱出牢狱,但还要再听圣上旨意,只怕他要闲在家中一段时日,待时机合适,新帝才会准他回朝处事。
而近段时日回到家中后,便要做一阵子富贵闲人。
马车轮子骨碌碌撵在石板路上,一路行向雍亲王府邸。
这一日唐宫之中皆是喜庆之声,皇后欢喜,这宫中奴婢欢喜,而唯独最不欢喜那人便是惠贵妃了。
此时宫中礼监正为她宣读圣旨。
她耳中听来,皇后已为太后,而她自身也已由贵妃为贵太妃,几字之差,在她心中想来,她与那太后之位,也仅仅相差一转瞬之运。
她卧于软塌之上,单手扶额,眼睫似睁非睁,叹了声道:“惠太妃……太妃。”
已是荣耀,先帝薨逝,那宫中根本毫不起眼,不为人所知妃嫔已随先帝葬入陵寝。
她得太妃之位,还有何不快。
“奴才差事已过,便先告退。”那内监伏地一拜,而后便起身离去了。
华清宫中冷寂非常,这青天白日里,礼炮礼乐之声不绝于耳,可在她听来却是心乱如麻。
一旁侍女与她好言道:“太妃从昨夜便未休息,过时躺下歇一歇吧。”
宁愿一觉长睡不醒,被那皇后压在头顶,她乃是先帝最为宠爱的妃子,怎可忍受。
“本宫心中憋闷,你替我寻御医来瞧瞧。”她一只细手抚在胸口,恹恹吐出口气说道。
“是。”那侍女听到吩咐欠身一拜,而后便出了殿中。
惠贵妃她身子疲软卧在榻上,哀哀呼吸,而后将身子慢慢躺平,望着眼前一点晃神。
这华清宫想来她也不可住上几时,想来还是早早离了这处,去投奔她那儿子去寻个心里清净。
眼不见心不烦,日子更要一天一天过下去,离了华清宫,还能要她少些想起从前与先帝之间恩爱。
他离了人世,惠贵妃仿若寄人篱下一般。
当真是她不通为人之道,处处与皇后犯难吗?而今日皇后已为太后,她的儿子已登基皇位,这唐宫天下便是他们的了。
惠太妃她心中忧思许多,千头万绪,更是理不清晰,她胸口憋闷一口浊气,平躺在这软塌之上,浑浑噩噩便就睡了过去。
宫中忙过一日。
苍寞寒自太极殿回来,此时已是夕阳西下,他忙过一日,忙过那登基大典,先是乘坐轿撵,前往未央宫向太后请安。
唐宫之中,那落日余晖遍布金碧辉煌高檐之上,处处皆笼罩在一派暖融祥和之中。
今日登基,于苍寞寒心中并无多想,只是即今日起,他自称便与旁人区别开来。
身边跟随,从前便在他左右侍候内监,郭公公,如今他因主成事,已是宫中内侍省首位,所属之下六局二十四司,虽在内殿省属下,而此时郭树人,郭公公已是总管大人。
“今日皇儿上登基,宫中大丧之后再添喜事,唐宫总是再繁闹起来。”郭公公跟随轿撵一侧,面带笑意道。
苍寞寒即便身在此位,心中却要时时记得,“父皇仙逝,朕承接大宝,更要秉承先帝之意,勤政爱民,并无繁华之想。”
听得他如此应话,郭公公只觉自己所言不妥,本是想来说些主子喜爱好话,却不想没成。
“是,是奴才妄猜圣意了。”郭公公垂首道。
那轿撵摇摇晃晃,苍寞寒那金色皇冠之上,挡在前额珠帘摇晃,不时便至未央宫之前。
郭公公高声道:“落。”
而后未央宫外,礼监层层传报声起,“陛下到……”
一层一层,至殿门外,一层一层传入未央宫当中。
此刻皇后正悠然得意,于窗前望景饮茶,终盼来这日,她总算可安然度日,再不必心中惶惶,怕失去何人宠爱,怕何人抢夺她宠爱。
想来此生,有苍寞寒这一位好儿子,便可要她高枕无忧。
这多年蛰伏忍受,终在那帝王离世,令她心愿成真。
此刻皇后面上,皆是那悠扬笑意,她卧在床畔,那雕花窗外是绿树红花,要人看来心旷神怡。
在今日后,自身便也可离去未央宫,享那晚年乐事。
熬过半生,她也劳累疲惫,想着该是歇歇了。
她嘴角扬起,虽是年岁大了,眼角细纹初现,而此时她面上笑意,也如那无忧少女一般。
听得传报声,是皇帝前来。
太后她慢慢转过头来,抬手令一旁侍女扶她起身,那侍女笑道:“陛下到底重视太后,登基大典才过,便前来看望太后。”
生养之恩,岂可抛在脑后,且多年对苍寞寒培养,几近耗尽太后心血,今日他终登上高位,受他回报,太后亦是理所应当。
侍女扶她起身,苍寞寒此时带郭公公走进殿中,至她面前一拜,“见过母后。”
“皇儿快些起来。”太后温温笑道,上前将他扶起,而后至床畔那软床入座。
苍寞寒与她同坐,见那小桌之上摆放一盏清茶,眼瞧着是百合花茶,说道:“母后也该多多滋养身子,这百合对女子来说最是滋补。”
他细致入微,太后听来面上便是温暖笑意,“得皇帝挂心,母后身子一向很好,倒是你。”
太后她看向苍寞寒,而这隐疾也是苍寞寒最不愿提起之事,而今有京燕为他调养,总归第一日受他针灸,身子倒是舒服不少,比起从前太医嘱咐所用药剂好上良多。
能暂且有缓就好,总好过一直看不到希望,最好此时还有个盼头。
苍寞寒笑道:“儿臣要母后挂心,这病也是急不来。”
他身上有着顽疾,却仍强迫自身与年昭媛行房,皇后想来是他当真喜爱那女子,当然也盼着年昭媛能生下一男半女,要她做上祖母,也是为皇家开枝散叶。
“你对那年昭训当真情深吗?”太后轻声问道。
自然,自然是情深,从见过她垂泪,见过她全心依附自身,她情深,苍寞寒便待她情深。
“儿臣是很喜欢她,年昭媛性情乖巧,而又实礼懂事。”苍寞寒温声应道,提起那小女子,他语调便十分暖人,可想见他二人平日如何缱绻动情。
这性情之好,算不得真情,倘若哪日年昭媛她性情不再这般讨巧,太后可想见,苍寞寒深情便也不再。
她为过来人,最是懂得男女之情,并无那百日好夫妻,若非一方执意,不然总会一拍两散。
什么深情,在这宫中最是少有深情。
年昭媛她若是想永保这宠爱,单凭她这讨喜性情,是远远不足,她既无那得天独厚美貌,若哪日君王身侧再添如花美颜,她自会被比得下风。
男子之爱,失之一瞬全无,而所剩,便只有旧情所带来敬重罢了,到那地步再想将宠爱重握手中,若是哭闹反遭厌弃,爱本就非那不可摧残之爱,君王怎会怜惜女子眼泪。
太后她此刻只在思虑,这唐宫之中,往后后宫妃嫔之间,定是再度重演,她从前所度过。
此乃后宫妃嫔皆会行过之路,太后她走过一遭,对爱情早已无念想,君王之爱,本就不可一生属于一人。
迟早也会移情别恋,想到此处,太后便再不会怜惜自身,因为她知,她与惠太妃并无不同,那君王在时,可将爱情从自己身上转到惠太妃身上,自然也可从惠太妃身上转至别处。
只是惠太妃她赶上好时机,在那君王已上了年纪时候痴恋上她,从此后无来者。
她是该得意,得此好运,她此生未尝得被冷落之痛,太后亦不会讥讽于她,而今日高枕无忧之人是自己,这独一无二的太后是自己。
此刻也该换得她受那冷落之感,那帝王之爱,至今日身为太后何必在意。
“宫中该再添新人了。”太后微微笑着,与苍寞寒好声道。
只年昭训一人,太后只怕她这儿子会寂寞,抛开他身子条件不提,哪位君王后宫之中没有三宫六院。
而此刻苍寞寒除非年馨儿之外,并不需要旁人,有这一小女子陪伴身边,这柔情已要他受用不尽。
“选秀之事,宫中大丧才过,父皇他才是入土为安,儿臣不想为人闲话,此事应当暂缓。”苍寞寒平声道。
他是不急,可太后却是很急,眼下宫中该热闹起来,至于她那丈夫,既是人已不在了,只要旁人待他敬意在就罢。
“你不必顾及这些,母后为你操办着,此事也要筹备一月之余,自然不是当下。”太后随着道。
听此言苍寞寒再未多话,“那也罢,那便要母后费心。”
他两人话过几句,苍寞寒便称有事先行离去。
自未央宫离开,便辗转前去大明宫。
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苍寞寒进入大明宫中,内监便将灯火燃起,他将皇冠取下,这才轻松一些。
这厚重皇冠,戴在人身十分沉重。
他至桌案之前坐下,翻过奏章,执起赤色红笔来,与一旁郭公公道了声,“今夜朕便在大明宫批阅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