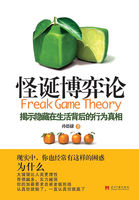世会福利院在城中一个安静的地方,一幢破旧的老房子旁种满了绿色的树木,远远看去,像一处城市中的幽静之地。
我喜欢那里,时常过去陪陪孩子们,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教他们画画,孩子们玩耍游戏的时候我都只是在一旁静静看着,那些需要强大的精力支撑的活动实在不适合我。
孩子们午憩过后,都奔跑到院子里嬉闹去了,我便坐到了大树底下的阴凉处看着他们。
今日天气晴朗,碧蓝色的天空漂浮着纱幔般轻盈的云朵,午后的淡金色阳光温柔地从树叶缝隙中穿过,洒在我的皮肤上,落下金色的光圈,微风徐徐,光圈在我的皮肤上左右舞动着,像欢乐的孩子们。
我喜欢此刻心里的平静,喜欢孩子们无忧无虑自由的微笑。
父亲的伤好得差不多了,重新回到了疗养院里,他的病房换到了走廊的第一间,能够让人清晰看到他的活动。
我总感觉父亲变得更加安静了,他很久都没有那般歇斯底里了,每天都只是坐在床上出神,对于我的到来都只是无动于衷。
他眼里是没有光的,像他的心没有了活力。
我看着阳光叹息,身后突然有个孩子走近,稚嫩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姐——”
落落坐到我身边来,阳光落在他的睫毛上,在脸上投映出一个小小的影子,他的目光静静地看着嬉闹的孩子们,眼里有着不属于这个年纪该有的成熟。
“你应该去和孩子们一起玩。”我说。
“他们太幼稚,我还是喜欢和你呆在一起。”
我无奈笑笑,“你才十一岁,这个年纪就该做点幼稚的事。”
“我不是孩子了!”他瞪大了眼,像只被惹恼的狮子。
明明就是个孩子……
落落大名叫苏落,上个月刚过完十一岁的生日。这个孩子在福利院里是比较特别的存在。
在福利院里长大的孩子几乎都是一出生就没有了父母或者是被父母遗弃在医院里身体有些残疾的,只有他,他曾经是有父亲的,只是没有母亲。
听院里的王姨说,落落来院里的那天,浑身上下都是伤痕,看人的时候眼里都带着深深的敌意。
他的父亲酗酒,他身上的伤都是他父亲留下的。
后来有一天,他父亲喝醉了,自己失足掉下河,溺死了。
那时落落才八岁。
我记得第一次见落落的时候,他就坐在院子里,孩子们都在成群结队地嬉闹,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眼里尽是落寞的神色。
我看得心疼,便走了过去。
我说:“你不去和孩子们一起玩吗?”
他似乎没有留意我的靠近,惊吓地看着我。
我微笑地看着他,只见他眼里微微闪着光,像极了那黑夜里的星辰。
半天,他扭过头,嘴上不屑一顾地说:“他们幼稚,我不想与他们呆一起。”
我一愣,顿觉好笑,但忽而看见他看着那群孩子时的神色,分明是羡慕的,我心下一沉,坐到了他身边。
他似乎对我的靠近很排斥,猛地站了起来瞪着我。
“你呆其他地方去!这是我的树!”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棵大树,“也没有刻你名字啊,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了?”
他怒气冲冲,但他根本无力反驳,只能将眼睛瞪得大大的,他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很强大,像只发怒的狮子。
“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你没来之前一直都是我的!”
他这般模样确实可爱,明明脆弱,却故作坚强,故作强大。
我轻轻拉住他的手顺势一拉,他一脸惊吓地坐到了我身边。
“你……干嘛……”
“看,那个孩子要赢了!”我指着孩子们。
他一愣,目光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
“一,二,三,木头人……”话音未落,那个孩子就碰到了他的肩,游戏结束。
那孩子发出一声欢呼,笑容比天上的太阳还要明亮。
他们生而不幸,却依旧为了生活点滴而笑。
“你几岁了?”
“九岁……”
他还沉浸在孩子的欢笑里,竟然乖乖地回答了。
“那以后你就叫我姐姐,知道吗?”
他猛地看向我,眼里的光变了又变,许久,只见他低头嘟囔了一句:“什么姐姐,脸长得和小孩一样。”
我拍拍他的脑袋,“我比你大三轮,叫姐姐。”
他抬头偷偷瞥了我一眼,又低头,扭扭捏捏半天,嘴巴张了张,发出蚊子般的声音。
“我听不到哦。”我故意逗他。
他猛地涨红了脸,脸上带着决然的表情,冲我大喊:“姐!”
我摸着他的头发,心满意足地笑了。
小狮子鼓着脸,炸毛的表情分外可爱,他的发丝软软的,摸起来手感特别好,直到现在我也习惯摸他的头发,然后看他一脸厌恶地瞪我。
他现在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自己不是个孩子,可在我眼里,他还是那个九岁的落落,敏感,孤傲,需要用尖刺来保护自己柔软的心的孩子。
“你为什么总来这里?你明明有家。”他突然说。
风吹得我指尖微微发凉,我靠在树上,从那叶子间仰望天空,阳光如海。
我说:“这里很安静,不是吗?”
“孩子们很吵。”
我一笑,摸摸他的头发,“你也是小孩子啊。”
他又生气了,鼓着脸,瞪着我,“我……”
“果子!”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我和落落一起回头看去,竟然是付书远!
“你怎么也在这里?”他高兴地坐到我身边来。
落落有些敌意地盯着他,似乎对他的到来很不高兴。
“我来做义工。”我答。
“是吗,真巧!”他的梨涡又荡漾开了。
“嘿!落落,你好啊!”他忽然对落落说。
落落猛地扭过头去,不理他。
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轻轻拉了拉落落的衣服,他硬是不肯回过头来。
“你认识落落啊?”我问。
“认识啊,这个让人头疼的孩子。”
落落听见“孩子”两个字,瞬间转过头来瞪着付书远,又变回那只炸毛小狮子了。
付书远一脸天真地冲他笑,甚是无辜。我一看这气氛有些不对啊,赶紧拦在他们中间,隔开了两人的视线。
“话说你怎么也在这啊?”我问。
付书远突然站起来,“走,带你去看点东西。”
我一头雾水地仰着头看他,他弯下腰一把拉住我。
“走啊,愣着干嘛?”
我站了起来,付书远从我跟前探出身子去看落落,笑盈盈地问:“你去不去?”
落落还生着气,拉不下面子,但好奇心对一个孩子来说是致命的,只见他扭头哼了一声,默不作声地站了起来,别过脸,默默地拉住我的手。
付书远满眼笑意,但也知道不要太打击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没有说什么,他拉着我,我拉着落落,三个人浩浩荡荡地一路走去。
“你究竟要带我看什么?”
“到了你就知道了。”他神神秘秘地卖起关子来。
我回头看了一眼落落,只见他眼里闪着兴奋的光,似乎很高兴又很紧张的样子。
我淡淡一笑,拉紧他的手,我们绕着老房子走,一直走到后院的一块空地上,那里堆满了废弃的床和柜子之类的杂物,平时很少有人来这里的。
“到了!”付书远停了下来。
我四周打量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
“来这里看什么?”
落落也有些茫然地看着四周。
“嘘!跟我来。”付书远放开手,轻手轻脚地走到前面去。
“过来,这里。”他朝我们招手。
我和落落跟着过去,他趴在一堆废旧桌子上,指了指里面,说:“看!”
我探头过去,顿时惊喜!
那旧桌子间的空隙里窝着一堆刚出生的小猫,毛茸茸的,软绵绵的,有白色的,灰色的,还有黄色的,它们紧紧地靠在一起,亲密无间。
“这里竟然生了一窝小猫!”我低声惊呼,生怕吓到这几个刚出生的猫咪。
落落也看见了,眼睛瞪得大大的,满眼惊喜。
“母猫应该出去找吃的了。”付书远说着要伸手过去。
“别摸它们!”我拉住他。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小猫摸多了会长不大的。”
付书远沉默半秒,缩回手来,“好吧,我们就静静看看它们。”
“落落,你喜欢猫不?”我问。
“还行。”他眼睛就没离开过那窝小猫。
我笑而不语,想了想,忽然说:“刚好三只小猫,我们给它们各自起个名字好不好?”
“行啊!嗯……我喜欢灰色的,就叫它……小灰!”付书远兴奋地说。
我瞥了他一眼,“好没新意的名字,那其它两个是不是就叫小白和小黄啊?!”
“果子!你好聪明!”他高声喊道。
“滚滚滚,一边去。”我送他一个白眼。
“落落呢?你喜欢那只?”我问。
落落皱着眉,很认真地思考起来,那苦恼的模样似乎在考虑一件天大的事情,我们都在聚精会神地等待他的选择。
半天,他幽幽地来了句:“你俩真幼稚。”
我和付书远默默对视一眼,进行眼神交流。
“我有点想揍他。”
“他还是个孩子。”
“可是我想揍他。”
“你怎么那么暴力?”
“他打击我的自尊心。”
“他还是个孩子,忍忍吧。”
“好,我忍。”
我俩目光顿时分开,我摸了摸落落的头发,说:“走吧,你也够时间上课了。”
落落瞅了一眼小猫,走回去了。
我和付书远相视一笑,都有些无奈。
从孤儿院出来后,我和付书远一起坐公车回去。
路上,我问:“你还没说你去那里干嘛呢?也是做义工?”
付书远正在看着窗外的景色,“没有啊,我回家啊。”
我猛地愣住了,他突然转过头,很自然地说:“我是孤儿啊,在世会长大的。”
他的眼里看不出半点情绪,依旧澄澈。
我却有些吞吞吐吐的说不出话来,我尽量想要装作若无其事,毫不惊讶,我害怕我任何的一个反应都会伤害到他,但是我的眼神还是出卖了我。
我感到诧异。
他那么若无其事地说着自己的孤儿身份,让我不知作何回应。
人啊,总在别人袒露伤痛时情不自禁地露出怜悯的表情。
我也是个俗人,避免不了。
他却忽而笑得开怀,让我一度以为他在开我玩笑,寻我开心。
“你这表情就像刚被总编训完。”他笑着说。
我本来还沉浸在悲伤里,被他这么一说,却怎么也怜悯不起来了。
“你就不能说点人话?”
“我说的是人话啊,大中国的母语!”他的两个小虎牙在我眼前晃着。
“滚滚滚,一边去。”
他更是笑得肆无忌惮,一如这八月的阳光,我透过车窗的倒影看见我微微仰起的嘴角。
这生活,若能一直如此平静该有多好!
杂志上市得很顺利,因贝岚的封面和Dior的采访,这期杂志销量大增,总编一高兴,请全体人员一起去吃饭唱k,大家都受宠若惊,尽管大家都觉得承了总编的情总是有些心慌的,但这有吃有玩的场合,不去白不去。
佩琪从得知消息那一刻开始就兴奋了一整天。
“果子,我今晚一定得大吃一顿,总编请客啊!这比火星撞地球还小的概率啊!我都要感动哭了!”
我正敲着键盘,眼都没抬,“你昨天不是说着要减肥来着?”
我刚说完明显感觉她身体僵了一下,我转头一看,她大梦初醒的样子。
我继续回头看我的电脑。
“果子,你好残忍。”
我淡淡说:“还好。”
“我恨你!”她幽怨地说。
“长痛不如短痛。”
“你不是人……”
“我是神。”
“……”
下午下班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是父亲打来的。
这是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我满是震惊,心微微颤动,惊喜得很。
他说:“夏果,你在哪呢?”
“我在公司呢。”
“还没有下班?”
“准备下班了。”
“吃饭呢?”
“嗯,公司有聚餐,呆会一起吃,爸,你呢?吃了没?”
“嗯。”
他应了一声,电话里沉默了许久,久到让我一度以为他挂了电话。
“爸……”
“这里不好……”他突然说话,我听不真切他说什么。
“爸,你说什么?”
“这里不好,她们困着我,都不让我出去,还拿针扎我,天天有人盯着我,夏果,你让我回家吧……”
他突然哀求起来,声音苍老。
我许久没有说话,感觉自己喉咙被塞了一块棉花,发不出声音。
父亲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来和我说话,我听出来了,他不是父亲,他分明是他体内的恶魔,他在想办法逃脱这个牢笼,所以他故作弱势,低声下气,只想我心软将他放出来,像当初一样。
那时父亲病情发作在打完我之后,他会跑过来用可怜的语气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你疼不疼?我给你找药。”
然后他一顿手忙脚乱地在一堆混乱中给我找来药,一边给我涂药一边说:“是我不对,你别哭,你原谅爸爸,以后我不会这样了,你原谅爸爸好吗?”
我在药物的清凉下慢慢止住了泪水,看着他苦苦哀求的模样,我刚狠下的心又心软了。
他说他不会这样了,他这样真诚,他应该不会骗我的,我再原谅他一次吧。
我又一次没有拨打医院的电话,我再次给了他机会,也再次给了那个恶魔成长的机会。
让他逃脱了束缚,也困住了我的父亲。
最后我还是不得不亲手将他送进那个牢笼,连带着我的父亲。
所以他恨我,情有可原。
他现在故计重施,我不可能再上当。
“爸,你得治疗。”
“这儿不好,这儿不好……”他反复在电话里说,如梦呓一般。
“爸,你听话,等你病好了才回家。”
“我没病!说了我没病!你们干嘛一直困着我!”他突然激动起来。
我一惊,害怕他又做出什么事来,赶紧安抚他说道:“爸,你听我说,我……”
“你是想我死呢!你还是我女儿吗?你个狠心冷血的人!”
他还记得我是他女儿呢……
他在电话那头激动大骂,我隔着电话听到那边忽然有人靠近,大声喊着:“快点,约束带!”
“安定针!”
“按住他!”
……
然后电话猛地被挂断了。
我愣愣地握着手机,许久也没有放下,等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满脸泪水。
“果子,干嘛呢?”身后突然冒出一个声音却戛然而止。
付书远看到我满脸泪水时瞬间呆滞了。
我转身抹了抹眼泪,低声说了一句:“我去一下洗手间。”
也不管他听没听到就冲进了洗手间。
我躲在洗手间里,拼命用冷水冲着脸,试图用那冰凉来压制我眼里的热度,我拼命告诉自己,不要哭,不能哭,可是越提醒那泪水往外涌得更凶,像决堤一般,摧毁了我所有的自控力。
我捂住嘴,尽力压低的哭声稀稀落落地从指尖溢出,我靠在洗手台上感觉自己的心像被人剜开了一样,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停止这种痛。
水声落在白瓷般的洗手台里,掩盖着我的脆弱,隐隐约约地我听见门外付书远与人说话的声音。
“书远,还不走?站在厕所门口干嘛呢?”
“你们先过去,我等等就去。”
“快点啊,迟到的话总编可不开心。”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先去吧。”
脚步声慢慢走远,门外又一片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