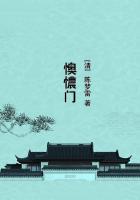晨风吻尽春花,似要将行人醉倒天街。
庆阳城主道,大齐士兵迎接南梁使团进城,百姓围了两旁街市,看着热闹。
花好从门帘一角看出去,大齐百姓个个容光焕发与有荣焉,对着南梁的队伍笑着指指点点,其中的深意只能让人无奈又心酸。
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身为南梁质子的秦又白又是如何想法。
使团队伍并不准备在庆阳城停留,直接通过街道往大齐都城瑞京而去,不过与之前相比,他们的队伍多了五百名大齐士兵,一时间整个使团的气氛有些微的紧张,连花好身旁的小翠儿都一改之前的活泼性子,安安分分的待在马车里不敢乱跑了。
南梁的每个人心里都似乎压了一块石头。
大概此时此刻唯一还能把日子过得跟以往一般滋润的,就只有身份不同的聂卿聂公子了。
当然这也只是某些人的自以为是罢了。
却不知,自打进入大齐国境后,聂卿行事愈发谨慎小心起来。
特别是当他发现那日在卞州刺史府里惊鸿一瞥的人居然还真混进了队伍里,心情就更加不美好了。
钟素素,你还真是死性不改!
聂卿凝眉望着不远处故意漏出破绽戏耍秦又白的钟素素,唇边不可遏制地露出一抹冷笑。
是夜,风凉如雪。
使团队夜宿一寻常山镇,人数太多,所以大部分士兵都只能搭营露宿,而秦又白等人则被安排在了不同的农居里。
花好领着小翠儿住进了一名寡妇家里,寡妇是新寡,一人独居,看着只有二十出头的年纪,一袭素衣麻布,头戴白花,羸羸弱弱,看着倒是让人颇为怜惜。
“县主大人,寒舍简陋,怠慢您了。”寡妇名唤玉娘,提起斑驳木桌上的茶壶给花好和小翠儿分别斟了一杯淡茶。
花好忙不迭接过,一口牛饮,“玉娘不必客气,叫我花好就行,我其实也是婢女出身,没那么多规矩。”
玉娘愣了愣,似乎没料到她会如此直白地说出自己的身世,很快那双盈盈水眸里又多了几分动容,“县主您脾气真好,将来必会是个有福气的。”
“哈哈哈,承玉娘吉言。”
双方进行了一番短暂的客套交谈之后,就很快歇下了。
夜晚风凉,花好睡下的房间里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黑暗中,一道人影动作缓慢的翻着花好的随身包袱。
“呵呵,花好这边总这么热闹,老鼠真多!”
聂卿的声音响起的同时,两道身影已经快如闪电地缠斗在了一起。
房间狭小,两人的动作也跟着受了限制,特别是聂卿惯用长鞭,这么一来便很是局限,只能用掌与那人对打,而对方出手如电,手中的短匕在黑暗中慑着冰冷的寒光。
“聂公子把花好当狗骨头一样看着,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
柔软缠绵的女声咬着牙恨恨地开口,这声音不是钟素素又能是谁?她千方百计混入使团不仅为了顺利进入大齐,也是为了接近花好拿到她手里的大印和令牌。
她原是打算继续好好忽悠这傻姑娘,让她主动把大印和令牌交给她,这样更方便她驱使沈河旧部,但计划败露,花好怕是对她有了防备,要想再说服她恐是难事,所以一计不成只得下手盗取。
但聂卿这人太过难缠,简直把花红盯得密不透风,她才刚有动作他就赶来阻扰了,实在神烦。
“至少花好现在只信任我,不是吗?”聂卿也不在意自己被比作了狗,黑暗中那双如星黑眸熠熠生辉,闪着冷凝的光。
两人的短兵相接并没有惊动花好和小翠儿,她俩之前喝的茶里被钟素素下了少量的迷药,怕被花好察觉异常,量下的并不大,但足以让她沉睡两三个时辰。
随着他们交锋的动作越来越激烈,屋内的桌椅板凳被撞碎了一地。
附近的守卫仿佛都成了死人,一点动静都没有。
凉薄的月光从破损的窗棂透过来,将屋内的情形拉成长长的影子,蜿蜒出妖异的舞。
“唔。”
花好的闷哼声在这样的情景下显得格外清晰。
聂卿和钟素素几乎同一时间动作一窒,双双把视线看向了原本在床上安睡的花好。
睡得迷迷糊糊的花好一睁眼就感觉周围的气氛有些不对劲,想到几天前发生过的事,头一偏,就见不远处两道人影正互踹了对方一脚,分别撞上了两边的墙壁。
“……谁?”花好猛一下坐起身,对着那两人大喊了一声。
混蛋,这一天天的是不是没完没了了,怎么这些刺客杀手黑衣人就专门喜欢跑她这里?!
聂卿还来不及出声安抚受惊的花好,钟素素已经身形一晃往花好的方向扑了过去,她手里的短匕像一头吃人的野兽,直噬花好的咽喉。
她这是要取花好的性命?!
聂卿甚至没时间多想,脚下一冲,整个人便朝着同一个方向飞了过去。
花好的夜视能力并不佳,哪怕有满室月光萦绕,也没能让她来得及去躲避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她感觉自己被一道人影抱住,鼻息间有熟悉的冷香。
是聂卿的味道。
还来不及多想,就听耳畔一道声响传来,几欲震碎她的心魂。
“噗!”
锋利的匕首刺入血肉之中,鲜血在莹白月光下如花一般绽放在一方暗室里。
“聂卿!”花好惊恐地尖叫,声音刺穿了冰冷的夜。
但聂卿此时却不能放松,钟素素一击得逞,如何能善罢甘休,不管自己伤重的身体,反身便朝身后的人影击出了一掌,掌风凌厉,势如破竹,蕴着他十成十的功力。
钟素素自然不敢硬接,身体连连后退,直接退到窗户旁,听外头已有士兵的动静声传来,神情复杂地看了一眼床上的花好和聂卿,恨恨唾了一声,暗叹一声功亏一篑,转身跳窗跑远了。
当秦又白带着人赶到时哪里还找得见钟素素的身影,以钟素素的本事她怕是早就藏得毫无破绽了。
他之前派景云去查队伍,但却一无所获,没想到今夜钟素素终究还是有了动作,居然还抢先一步到了他们今晚落脚的地方,扮作了寡妇玉娘。
花好的房间一团混乱,除了床之外,基本无处可以下脚。
聂卿背部被刺,伤势极重,花好不让人移动他,所以他就直接待在了花好原先的床上。
屋内已经重新收拾整齐,堵了漏风的窗,安置了新的桌椅,红炉火盆里烧着炭,一室温暖如春。
除了照顾的小翠儿之外,其他人都被花好赶了出去,包括秦又白。
聂卿上半身打着赤膊趴躺在床上,花好小心翼翼的处理着他背部的伤口,匕首很锋利,钟素素更是下了十成的力气,所以几乎整柄没入。
若非恰好避开了主要器官,聂卿这条小命怕也是岌岌可危。
小翠儿不断地端着被染红了的水盆往房门外倒,雪轻轻下在青石台阶上,裂纹里面冻了一层滑溜的冰,血水倒在冰上,汇成一条粉色的小溪。
“我拔匕首时会有点痛,你咬着这个。”花好递给他一块锦帕。
聂卿二话没说接了过来咬在嘴里。
花好深吸一口气,用干净的纱布包好伤口的边缘,以防拔出来时血液喷溅。
“我开始了啊,你忍忍。”花好出声提醒。
聂卿点点头,肌肉却忍不住开始紧张。
花好也紧张,但她身为医者绝对不能被情绪感染,咬咬牙,心一狠,手下用力,匕首已被她拔出。
“唔。”聂卿吃痛,一个闷哼,牙齿狠狠咬住了嘴里的那块锦帕。
裹在伤口上的纱布很快便被血染成了湿润的红布。
花好手下的动作飞快,在小翠儿帮忙下,拭血,上药,包扎,一气呵成。
等做完这一切,花好已经满头大汗。
“好了,休息十天半个月就会没事了,不过这段时间你不能下床,伤口也不能碰水,每日都得换药,吃得东西也得忌口,不能吃……”
花好开始滔滔不绝。
聂卿已经吐掉了嘴里的锦帕,此时正半偏过头看着她,面色虽苍白,但一双眼睛却格外明亮,唇边还漾着若有似无的笑。
“还笑?差一点你就一命呜呼了!”花好想起方才的凶险就忍不住心跳加速,只要偏了一寸,聂卿这条命就真的可能药石罔救了。
聂卿因为失血过多显得稍淡的唇微弯,一头青丝披在绣枕上,柔静的如同月下美人,挑着浅浅的弧度,有一种澄澈的风姿。
他的手指轻轻勾住花好放在床边的手,拨动着轻快的旋律,“英雄救美,死亦无憾。”
花好闻言脸颊微红,不由自主的低下头去,被他缠住的手却始终没有收回,柔美的红唇弱弱翕动:“就你会贫嘴。”
窗外雪意湛湛,屋内静谧融融。
花好想了想又抬头问:“你说方才来人是钟素素?”
聂卿点头:“是她。”
“她为何要杀我?我……”花好眸色微黯,“我可是阻了她的事?”
聂卿无奈叹气,握着她的手指紧了紧,黑眸幽冷如冰地望着床沿的火盆,说道:“她要的不是你的命,而是你手里的东西。”
花好一愣,“你是说……那枚令牌和大印?”
说着,心中微颤,不由得抓紧了自己的小包袱:“你见多识广,你告诉我,我这包袱里的东西,到底如何关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