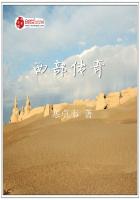一
我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
我的故乡在皖南的一座大山沟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穷得叮口当响的地方,土地不但少得可怜,而且非常贫贫瘠。半山坡上有座小学校,学校更穷,墙是泥巴的,桌子是泥巴的,板凳也是泥巴的。唯有班上十几个学生不是泥巴的。我就是那些不是泥巴的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我考取了城里的中学,又上了大学。大学一毕业,我就要求回家乡来,当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像我儿时的马老师一样,把一生献给山区的教育事业。
从我读小学一年级起,马老师一直是我的班主任。那时他还是个四十来岁的单身汉,教着教着,把我们教大了,而他却变老了。不知是岁月风尘的浸蚀,还是那纷纷扬扬的粉笔灰的漂染,他那一头黑发竟然变得雪白,远看活像一位白头老翁。
马老师有个特殊的爱好,就是收藏。论起收藏,马老师算得上中国最伟大的收藏家。他收藏的不是邮票、火柴盒,而是粉笔头。每写完一支粉笔,他不像其他人那样随手一扔,而是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带回宿舍,装进一只大纸盒,一年一盒。我在小学读了六年,他就收集了整整六盒。
有好几回,马老师正全神贯注地在黑板上写字,桌边的一颗粉笔头骨碌碌地滚到了地上。他的后脑上好像长了了眼睛,马上回过头,两眼朝地上直扫。坐在前排的我立刻从老师的眼里看出了他想找什么,忙弯下腰帮他捡起了那像花生米一般大小的粉笔头,递给他。他掏出手帕,小心翼翼地包好。早晨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落在马老师那微笑的脸上,像一片灿烂的朝霞。
我知道他心里高兴,因为他又多了一件珍藏品。
记得是一个暴风雨的夜晚,雨水顺着开裂的墙缝直往屋里灌,把几盒粉笔头打得精湿。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马老师把所有被淋湿的粉笔头摊到太阳下晒。他默默地守在一边,像看护着十世单传的婴儿。
但我实在不明白,收藏那玩意有什么用?我问他,他像孩子一样侧脸望着我:“说不定将来能派上用场哩!”再问,他只是笑。啊,明白了,他是想把这玩意送去回收?我特意到收购站打听过,他们说从不收购破粉笔头。
十多年过去了,马老师仍然孑然一身。除了教书,就是收藏了。不知他现在收集了多少粉笔头?那间小屋能放得下吗?
二
翻过钻入云霄的老人岭,眼前豁然开朗。到了,到了,就要看到曾养育过我的小摇篮了。令我兴奋的是,学校原先几间破旧的小平房变成了一栋大楼。几个工人师傅正在浑汗如雨地忙碌,他们把雪白的石灰往墙上抹,那石灰真白,太阳一照,白得烁眼,白得让人心醉。
上前细看,不像是石灰,像白水泥。用手摸摸,也不像。我问一位师傅,他说他也没见过,这里的老百姓都把这叫做“白泥”。是今年春天才发现的。
“在哪发现的?”我问。
师傅说在松树坡的水沟边,是挖排水沟时无意中发现的。顶多挖上一米深,白泥就像面粉一样源源不断地往外淌。听他说得神乎其神,我不大相信,跟着他跑到坡下,伸头朝沟里一看,沟壁上果真现出一个圆溜溜的小洞。师傅把堵在洞口的石头一搬,一股白花花的东西就直朝外涌,稍微用水和和,就能往墙上抹。
他们就是用这种白泥把整个教学大楼打扮得漂漂亮亮。
我的心怦然一动,这不是再好不过的生财之道吗?有了这个聚宝盆,还愁穷山沟富不起来!别急,待我静下心来研究研究再说。我用手撮了一点用纸包好,准备带回城里化验化验,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成分。
三
我从学校门前的草地上走过,迎面走来几个放学的孩子,他们用惊异的眼光打量着我。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用试探的口气问:“叔叔,你是新来的老师?”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我忙弯下腰,笑眯眯地把头点点。
孩子们一听说我是老师,忽拉一下围了上来,问这问那。其中有个孩子突然问:“你认识我们的马老师吗?”
“是不是那个收藏家?”
“是的是的。”
“我也是他的学生呢!”
“可他——”
羊角辫垂下眼睑,轻声对我说,马老师已在去年春天离开了他们。她指指松树坡上的一座土丘,说那就是老师长眠的地方。
我站在那里半天没动,泪水在眼眶里聚集。孩子们看我情绪不对,摇着我的胳膊,叫我别难过。
我们手拉手地向墓地走去。路上,我说起了马老师收藏粉笔头的故事。他们没笑,个个脸上洋溢着神圣的表情。羊角辫说,马老师直到临终时还在收集,已经装了满满几十盒子了。
马老师是在课堂上猝然倒下的。
他患的是鼻咽癌,开头还不觉得,等到了城里医院一查,才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回到学校他没告诉任何人,揣着粉笔又上了讲台,看不出一点悲伤,看不出一丝绝望,仍然像往日一样讲着笑着,很有表情地朗读着课文。杜鹃花在他的笑声中开得热腾火旺,百灵鸟在他的笑声中亮开了歌喉,小溪在他的笑声里弹起了琴弦……是孩子们那一张张微笑的脸使他忘记了一切,是那一篇篇精彩的课文使他的生命得到了延伸。
那天,他正在讲述一篇关于春天的文章,刚开了个头,就像一根被融化的蜡烛,软软地倒下了,倒在一个清亮亮的早晨,倒在静静的讲台上。他的手心里还攥着一截粉笔头。他那微微上挑的嘴角依然挂着微笑,好像在说:“孩子们,别管我,继续念。”
他是带着对孩子们的深深眷恋而离去的。
教室里响起了不可遏制的哭声。
羊角辫扳开老师的手,取出那个粉笔头,用小手帕包好,带回老师的宿舍,轻轻地放在最后一只盒子里。
孩子们最能理解老师。在掩埋老师的时候,几十个孩子不约而同地抱起这些盒子,把成千上万只粉笔头慢慢地倒进深深的墓道。这些星星点点的粉笔头,掩盖着老师的身体,像雪花伏盖着田野,像梨花铺满了大地……一位白胡子老爷爷流着泪说:“有了这些粉笔头,马老师就好像看到孩子们天天守在身边,他也就放心了。”
一位进山体验生活的诗人仰天长叹:“这哪是粉笔头,分明是孩子们的眼泪,是眼泪凝成的珍珠。”
一位回乡探亲的科学家一字一顿地说:“有了这些粉笔头,老师的身体就不会受到细菌的侵蚀……”
诗人和科学家都曾经是马老师的得意门生。
四
墓地静悄悄的,青草支支直立,几株龙柏松挺立在马老师的墓边。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洒下斑斑点点的光亮,偶然一声清脆的鸟鸣打破这山里的寂静。
几十个春夏秋冬,寒暑凉热过去了,马老师教过多少学生,他记不得;吃了多少粉笔灰,他说不清;唯有那些粉笔头,是最好的见证。它们默默无声地记录了每一节课是怎样的生动传神。
“说不定将来能派上用场哩!”老师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悠地,一个奇特的念头像闪电一样在我脑海中划过,还来不及抓住它,思索它,只是问自己,那抹在墙上的白泥莫不和那些粉笔头有什么内在联系?一种强烈的潜意识推动着我飞快地跑到离墓地二十米左右的水沟边,蹲下身子细细观察那出白泥的洞口。白泥已停止了涌动,洞口像一只幽深的眼睛盯着我。
我朝墓地望去,墓道直通洞口。我百思而不解,难道冥冥之中真有……我不敢把这种想法告诉任何人,我怕有人说我在胡思乱想,说我头脑出了故障。
我很快回到城里,把白泥交给化验所化验,化验来化验去,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什么。一位老化验师一口咬定说这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后的物质。里面到底是什么成分,一时难下结论。他劝我去查查县志,看看历史上可记载过这种宝贝。
翻遍了资料馆的每一本志书,也没有一点蛛丝马迹。我准备进山作一番调查,真希望能找出白泥和粉笔头之间有什么联系。
就在我再次翻过老人岭的时候,一位进城读书的中学生在山道上迎上了我。他对我说,那流淌白泥的洞口昨晚被人掘开了,一直挖掘到马老师的墓地前,白泥全部消失。
这消息像擂鼓一样震得我耳朵嗡嗡响。我一把抓住那个学生,问是谁干的,他说可能是村里的三拐子,他是个恨不得一锄头掘出来个金娃娃的黑心汉子。
三拐子原先也是马老师的学生,只念了两年就不念了。他到过上海,去过深圳,做过几笔赔本的生意就又转了回来。没想到在白泥身上打起了主意。我问:“他人呢?”
“被派出所拘留了!”
我不顾一切地向墓地里飞跑,在那片绿茵茵的草地上果然见到被掘开的一条长长的泥沟,龙柏倒在沟边,枝叶在微风中颤抖;鸟儿在空中盘旋,发出揪心的鸣叫;沟底流淌着一股浊黄的水,那莫不是老师的眼泪?
因为三拐子是夜晚干的,白泥被抛洒得满地都是。
青草支支直立,仿佛在争先恐后向我诉述昨晚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我慢慢地蹲在老师的墓碑前,心底掀起了拍天的狂涛。
四周静悄悄的,听得见小虫在草丛里吟唱,像老师在絮语。
远处,一群孩子捧着一大束鲜花向墓地走来。
五
更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暴风雨后的早晨,当我再次来到墓地前时,一个奇特的景象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只见碧绿的草地上缀满了一朵朵雪白的小花,远远望去,真像一个个粉笔头撒了一地。
马老师,是不是和上回一样,粉笔头被暴雨淋湿了,得晾到太阳下好好晒一晒?……恍惚间,我又回到十多年前那个清亮亮的早晨,我低下头帮马老师捡起滚落到桌下的小不点。当我直起腰时,看见马老师那微笑的脸上洋溢一片,真像灿烂的阳光。现在,我弯下腰,看到的却是一朵朵白色的小花,散发出浓郁的清香,弥漫在这生我养我的大山沟里。
很快有人发现,这种白花有一种奇特的功能,哪家孩子头痛脑热,不能上学,只要采几棵放在锅里一煮,把汤喝下去,病立刻就好,就会背起书包像小鹿一样朝学校飞跑。
不知谁把这小花取名叫“马林瓜”,和电视上的“玛琳瓜”药片读音一样,不知道那玛琳瓜和我们山里的马林瓜可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的马老师就叫“马林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