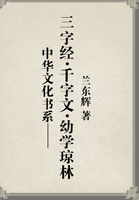韩少功
我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异响,跑到院子里探头一看,见竹林里枝叶摇动,还有个隐隐约约的黑影,似乎正在藏匿。是谁呢?我随手抄起一杆铁锹大叫一声,那里便有一刻的静止,然后冒出一个顶着蛛网和草须的脑袋。
“我来砍点茅竹。”他露出两颗黄牙。
“你是谁?怎么砍到我院子里来了?”
“这些茅竹没有用的。”
“你说没用,我有用呵!”
我大为生气,觉得这人真是无礼,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擅闯私宅,冲着我的园林狠下毒手,是不是过两天还要来拆墙和揭瓦?还要来这里改天换地?可怜我精心保留下来的一片绿色,院子内必不可少的第二道或第三道绿色帷帘,已经被他撕开了缺口。围墙红砖裸露出来,砸得我眼前金星四冒。
他嘴唇肥厚得有些迟重,又披挂着嘴上又粗又密的胡桩,搬运起来不方便,吐什么字都是一锅稀粥。他说了他的名字又似乎没说,说了他家在何处又似乎没说,还说茅竹不是楠竹,只能砍下来卖给毛笔厂做笔杆云云,但我都没怎么听清。我喝令他立即住手,立即离开这里。他怔了一下,迟疑地点头。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当时回答得并不清楚更不肯定,或者干脆就不曾回答。
“这些茅竹只能藏蛇,留着做什么呢?没有用的,没有用的。”
他还在嘟哝,把已经砍倒的竹竿收拢成捆,扛上肩,总算出了门。
不久后的一天,我从外面回家,一进院门,发现这里已经有了主人——又是那一嘴胡桩,像一个刷子没剩几根毛;还有两大块嘴唇,冲着我一番哆嗦和拥挤,总算挤出几星唾沫,是高高兴兴的唾沫:“回来了呵?”在他的身后,两头牛也有主人的悠闲自在,一边喳喳喳啃着草,一边甩着尾巴,拉下了热气腾腾的牛粪,惊动了上下翻飞的牛蝇。我恍惚了一下,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但定睛一看,这刚刚用石板铺成的路,刚刚开垦出来的菜地,刚刚搭就的葡萄架子,明明还有我的手温。这围墙外的一棵大树和远远的两层山脊线,明明是我熟悉的视野,怎么眼下反倒让我有一种反身为客的紧张?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没好气地问。
他兴冲冲地指着一块菜土:“这里的地湿,你不能种番茄,只能种芋头和姜。你得听我的。”
他又指着樟树那边说:“那下面有两株好药,五月阳,你不要锄掉了,等我秋天再来挖。”
我完全不懂什么五月阳,也不在乎两株草药由谁挖走以及什么时候挖走,但我无法容忍他这种兴冲冲的劲头,这种无视法律和搅乱社会的口气。“你到底是谁?我同你说,这是我的院子,我买下来的院子,我办了土地证的院子。这个意思你不会不懂吧?你要挖草药,要放牛,要砍茅竹,可以到外边去。你如果要进这个院子,就得经过我的同意。你懂不懂?你要不要我拿土地证给你看看?”
他怔住了,似乎再一次难以理解这么深奥和复杂的道理,“你是说,你是说……”
“我是说,你以后不要到这里来放牛。”
“这里不能放牛么?”
“你觉得这院子可以让你放牛?”
“牛最喜欢吃这些茅草,你留着反正也是没有用……”
“留不留是我的事,对吧?”
“你要留呵?你要留,就早说呵。我不知道你要留。我不知道。
你要是早说一句,我也就不会来了。”
他没有追究我不宣而禁不教而诛的责任,吆喝一声,赶着两头牛出了院门,一大捆牛草在他肩后晃荡,叶尖沙沙地刮扫着路面。他当然没有带走他的牛粪和牛蝇。
我给院门加了一把锁。
我加了锁以后才知道他的来历。他叫李得孝,外号孝佬,是附近的一个农民。只因为我买下的这块地,原是分配在他名下的责任地,二十多年来,已经被他跑熟了,甚至被他家的牛跑熟了,一放绳,根本不用驱赶,牛就乖乖地直奔这里而来。眼下,他不是不知道事情已经有了变化,不是不知道这块地经乡政府征用,最终卖给了我这个外来人。但他砍茅竹或者割牛草的时候,还是情不自禁地往这块地上窜。想想吧,他熟悉这里的茅竹,熟悉这里的茅草,熟悉这里某个角落的五月阳,憋一泡屎尿甚至也曾经习惯性地往这里狂奔,一心要来增肥沃土。他一时半刻哪能割舍得下?他远远就能嗅到这里的气味,远远就能听到这里发芽或落籽时吱吱嘎嘎的声响,连睡梦中一迷糊,也能感触到这里在雨后初晴或者乍暖还寒时的一丝抽搐或跃动。对于他来说,这些当然比一张土地证更重要。有人告诉我,自从我不久前两次把他逐出门外,他还是有点半醒不醒,好几次还扛着锄头来到我家院门前,见门上一把铁锁,才怏怏地蹲下或者徘徊,最后掉头而去,嘴里嘟嘟哝哝地不知说些什么。
他没有大喊大叫地打门,就算是够清醒够冷静的了。我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还会在一把铁锁面前恍惚,就像把一个儿子过继给了人家,但很难把这个儿子视为人家的骨肉,一不小心就还会叫出什么乳名。
我的目光越过院墙,看到了墙外起伏的青山,看到了雨后的流雾在山间悄悄爬升。我这才发现自己对这里所知甚少。
说起来,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了三个月,也许往后再住上三个月,再住上三年,我也无法得知这里的全部故事。就拿对面山上那个无人的峡谷吧,我只知道它在地图上叫“珠波坳”,或者是农民平常说的“猪婆坳”,一个诗意的名字不时散发出猪屎味。到底是“珠波”还是“猪婆”?在一个旅游者眼里,那条峡谷也许只是一片风光,只是春天的映山红和秋天的落叶红。但在一个勘探者眼里,那里可能不过是丰富的酸性红壤和页状层积岩?是勘测记录里来自侏罗纪时代的云母矿和含硫铁矿?同样是那条峡谷,对于一个耕作者来说,也许更意味着竹木的价格、油茶的产量、蜜蜂花源的多或少,水源利用的难或易,还有某一年山林复垦时刺骨的寒冷和腿上流血的伤口?我在这里还认识了一位喜欢谈风水的船老板。我知道他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猪婆坳在他眼里既不是风光,也不是资源或者物产,只是一些青龙、白虎、神龟、玉兔以及来意不明的其他巨禽大兽,是这些神物的伪装和凝固,还有它们对山民们命运的规定。于是,船老板总是在山水中看到了遥远的祸福,有时会被一棵老树的倒下吓得浑身冒汗,或者对某一个建房工地心急如焚长吁短叹。
船老板近来忧愤交加,因为风水正在遭到漠视和破坏。外来人越来越多了,大多不理睬他的那个罗盘。除了我这样的城市生活逃避者,还有商家要在这里征地,建制药厂和矿泉水厂,还有政府机构要在这里征地建培训中心,还有一家港资公司打算在这里圈地上万亩,建设宾馆、猎场、马场以及生态公园——测量人员已经来了好几趟,陌生的身影和口音让山民们颇为好奇,未来的一切也就变得闪烁不定零零落落。乡政府干部大为生气,说有些农民一听说外人要来征地,就到处制造假坟,骗取迁坟费。乡长在广播喇叭里曾经大声怒吼:有些家伙,平时一没看见他们上供,二没看见他们挂香,到这时候了,就这也是祖宗那也是祖宗,你们哪来那么多祖宗?孝子贤孙想当就当么?随便挖个洞,丢几根猪骨头牛骨头在里面。想诈骗谁呢?以为我瞎了眼吗?以为人民政府的钱出门就可以捡吗?
农民对此不服气,在路口上三五成群交头接耳,说人骨头就是人骨头,乡长如何扯上猪和牛,讲出这种浊气的话来?他自己的祖宗未必就特殊些?有本事他也挖给我们看看!再说,那公司老板的先人姓曹,以前就是这里的大地主,只是革命那年吓得白了头发,瞎了双眼,最后一绳子上了吊。但现在曹家香火旺盛,人脉发达,在台湾出了博士,在香港又出了董事长,财大气粗的又要把土地统统往回收。让他家多出几个迁坟的钱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是做了几个真真假假的坟,不也是让他多掏一顿饭钱么?哪里扯得上什么破坏改革开放?
说起来,命就是命呵。他们还常常感叹,十几年前修公路时,移过曹家的祖坟。人们发现坟破之际,坟内的热气直往外冒,潮乎乎的鲜味扑鼻,像包子铺里一个揭了盖的蒸笼。你想想,时隔几十年还能有这样的蒸笼,曹家不兴旺发达也是不可能的。这话的言下之意,是他曹家多出几个钱也在情在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见到过曹家的后人。乡长带着一行客人来到我家,照例是无可款待的时候,把我这个院子权当乡间景点之一。客人中领头的一位满头银发,但穿着旅游鞋,背着双肩包,揣着照相机到处照相,照我家的树,照我家的草,照我家的鸡埘和锄头,最后照到我的脸上,似有一种对案发现场的认真仔细,让我有一刻的毛骨悚然。他身后的所谓秘书也是个银发老头,也穿着旅游鞋,但一进门就倒在椅子上呼呼大睡,大概是太累了。如果不是他们身后还有年轻的一男一女,在折腾着便携式电脑,我觉得这两个老顽童疯疯癫癫,投资开发一类纯属儿戏。
他们操着台湾式国语,倒是很和善,见人就递名片,见人就彬彬有礼地鞠躬问好,连一个个抹鼻涕的娃崽也被他们笑脸相向,毫无一点寻仇报冤的迹象。
他们把我家院落前前后后细看了,临走时,照相的老头低声说:“你在入秋的晚上是否听到过什么声音?”
我摇摇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他笑了笑,吁了一口气:“你这里是个好地方,最好的地方,千金难买。我告诉你,只是有一条,你千万不要冲着西北角那个方向撒尿。”
我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看了看我家后门,看了看后门外碧绿的水面,很有把握地点了点头,“你听我一句:这个门的朝向要改一下。实在不能改的话,至少要在门外做两个石头狮子。实在不愿做石头狮子的话,门上至少也要挂一面镜子。”
“为什么?”
“你不知道么?你这张门,正对着猪婆坳。民国十六年,那里一夜之间杀了七个人。血光之灾,必留恶煞之气,还是避一避的好。你明白了吧?你要是下水游泳,也千万不要游到那里去。那里不干净的。你明白了吧?”
我明白什么?民国十六年,也就是七十多年前,也就是比我出生还早三十多年,那里为什么杀人?杀的是什么人?被杀的人与这张后门又有什么关系?
老头言之不详,告辞走了。我事后向乡亲们打听,他们也含含糊糊,没人能说得清楚。孝佬来挖五月阳,顺带找我讨几片瓦,对杀人事更是一无所知,连连摇头,只是说那山峒里原来有一户人家,听风水先生说他家要出三顶轿子,心里十分高兴。没料到一辈子过下来,还是穷得差点卖裤子。主人最后倒也没有找风水先生的麻烦,只是叹了一口气说:三顶轿子倒是没有说错呵,我婆娘结扎是抬出去的,我婆娘遭病也是抬出去的,最后死了也是抬出去的,不就是三顶轿子么?
我一听孝佬说起这事,知道他已经糊里糊涂,不是说猪婆坳,是说到附近的雁泊坡去了。他的耳朵似乎有点背。
我跟着制药厂几个人去寻找水源,去过一次猪婆坳。我们弃船登岸,劈草开路,沿着一条小溪走进了比人还高的茅草丛,走进了一时明又一时暗的杂树林。我不怕蛇,甚至没工夫想蛇,满脑子是前不久曹家老头那很有把握地点头,于是对峡谷里的一沙一石既好奇又提心吊胆。大概就是这里了吧,也许不是。也许事情还发生在前面,在歪脖子松树那里。我不知道溪边那片石滩上是否横过尸体,不知道前面那棵老枫树上是否挂过血淋淋的肠子或者眼球,不知道更前面那一丛火焰般的美人蕉,之所以开放得如此癫狂,是否扎根于一个蚁群曾经密密噬咬过的骷髅。我正在走过一个现场,以至我在一个石头上喘气的时候,觉得这块巨石太凉,凉得很有些来历,让我有点不敢触摸。最后的情节很可能就出现在这里。就是说,那个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从坡上的草丛里爬过来,把扎进肚子的杀猪刀拔出(这样也许可以爬得快一些),把身上那些鼓着气泡的血水送进嘴里(也许可以解渴和增加体力),眼睛就盯着这块石头,一寸又一寸,半寸又半寸,希望能在天黑下来以前抵达,好让他或者她看到山下的屋顶(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个水库,也不会有水库边的小船和草棚子)。但那个人可能就在触到巨石之前,伸出的手痉挛了,僵硬了,最后垂落下来,并且慢慢地冷却,然后有蚂蚁、蚊子、蜈蚣、山蚂蟥的聚集……他或者她的衣袋里,可能滚落出一个银镯子,或者是一片人耳——以后查找仇人的证据就此失落。
一声尖厉的惨叫拔地而起,吓得我全身有抽空之感。仔细一听,才知不是什么惨叫,不是有人丧命,是林子里鸟的喧哗。
我可以确定,我完全应该确定,我们在这里什么人迹也没看到。除了树上有一张蚊帐般的大蛛网让我心惊,除了一种草叶毒得我两腿奇痒,这里只有各种野花争相开放,足以让你想象自己落入了一个万花筒天旋地转。在一种有草腥气息的晕眩里,你还可以看到一大群蝴蝶扇动着阳光的碎片,遮天蔽日地从天而降,感觉到全身被无数个光点一瞬间击穿。
坐在这块石头上,同行人谈着引水工程以及将来的大规模开发。我没有什么好说,回望水那边,恰好可以看到村子里的几户人家,包括看到孝佬的那两间瓦房,看见他的屋顶上照例没有炊烟。我知道,他很久没有来我家了。我知道,像其他有些农民一样,失去土地以后,他就去城里打工了。他算是运气不太好,打完第一年工,老板跑了,让他一个工钱没有拿到。第二年算是拿到了工钱,但老婆跟上一个照相的浙江佬,要跟他离婚,还要带走儿子。儿子想了想,对母亲说:“爸爸一辈子抓泥捧土,好辛苦,我不会离开他的。”母亲说:“妈妈再给你找个好爸爸。”儿子说:“我不要新爸爸。你一定要离婚的话,我就穿一身白衣到汽车站去送你,给你叩三个头,但从此以后你不要回来,我也不会去找你。”这话是孝佬说给我听的。
还是从孝佬的嘴里,我听说他婆娘听完儿子的话,跑到山上大哭了一场,但还是走了。儿子果然穿着一身白衣去送她,果然是在汽车站撅起瘦小的屁股,冲着她的背影跪叩三番,直到夜色降临还跪在路口,直到泪水流干还面朝着公共汽车远去的方向。是一个陌生的老头最终扶起了他。
从那以后,母亲再没有回家,再没有寄钱回家。为了独力负担儿子的学费,孝佬在工地上不再吃早餐和晚餐——因为老板只管一顿免费的中饭。这样,他每次看见同伴去吃饭,就假装上厕所或者逛街,一直熬到中午,一直熬到可以白吃的时刻,再狠狠吃他个两眼翻白,又是嗝又是屁地动静很大。他后来一失足摔下脚手架,摔断了腰骨,大概就是胀昏了头或者饿昏了头的缘故。
他一度回到了村里养伤。我有时看见他一手扶着腰,在山里挖药,或者给邻居阉鸡,还给学校里这个或那个老师挖地,种点菜秧,好像他吃着百家饭管着百家事,或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魂。后来我才知道,他欠了很多人的钱,一时没有办法还清,就用气力来还一点人情账。
有时他也一手扶着腰,拿着十几根多余的菜秧来找我,问我要不要赶着季节栽下。这时候,他蹲在地头,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根烟,嗖嗖地吸出声音,总是嘟哝到他的儿子。儿子在县城里读高中,本来成绩好好的,去年竟然考了个门门不及格,退学了,去了广东的工厂。其实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们都知道,他是故意考砸的,是想考出个退学的正当理由,早点去打工赚钱替父亲还债。
“孽障啊,你看看,真是个不忠不孝的孽障呵!这个该吃枪毙的,英语只考了个八分,传到外面去,把我祖宗的脸面都糟践成屁股皮了。”
他一说起这事,就抽自己一大耳光:“我就是腰不好。要不是这腰,我早就跑到广东去了。我要找到他,打断他的腿!”
“你不要怪他。年轻人也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
“不读书怎么办?不读书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到时候不就像我?一辈子就土虫子一条?”
我连忙岔开话题,问他为什么不另外找一个老婆。女人的话题也许能使这个单身汉开心一点。
“我有儿子了呵!”他瞪大眼睛。
“我不是说儿子,是问你为什么不再找个女人。”
“我有儿子了呵,已经有了呵。我对得起祖宗了,还结婚做什么?还养个婆娘来吃饭?来费衣?来摆看?”
这回轮到我有点费解了,"你毕竟……才四十出头,就不要个做饭的?"
“做饭最容易了。我煮一锅,吃得了两天。”
"就不要个伴,好说说话什么的?"
“我不喜欢说话。”
他已经栽完了菜秧子,又摘了些大树叶来给菜秧子遮阳,防止它们遭到暴晒。看他对菜秧子兴冲冲的劲头,我怀疑他根本没听懂我刚才的话。他平时随便找个碗,往地上一砸,取块瓷片就可以帮邻居阉鸡或者阉猪,甚至给自己剜疮或者割疣,他莫不是又砸了一个碗?取一块瓷片把自己给阉了?这是另一种可能。不然的话他为何对再婚毫无兴致?
春天又来了,我家的芥菜果然长得很猛,每一棵就胀得地皮开裂,能让你挖出碗大的菜头,可见孝佬确实熟悉这里的泥性。春天里的茅竹齐刷刷抽笋,很快就绿成了密不透风的一片,有几只鸟在那里面扑腾或者啼叫,总是引起来客们的注意。我不得不去间伐掉一些茅竹的时候,就想到了孝佬。我早就取下了铁锁,敞开了院门,希望他什么时候提着柴刀前来,但他的脚步声倒是不再出现了。我家的五月阳已经繁殖出一大片,开出的花朵像满地金币,却没有人再来挖采。
我路过他家门,发现门上挂着锁。他是去寻找他的儿子,还是去哪里给人家帮工还人情,抑或是去城里找他的一位兄弟,不得而知。
他的邻居也不知他去了哪里。更准确地说,他其实已经没有多少邻居。村子里有点空空荡荡,我的脚步声足以引起巨大的回响,我的说话声也足以让自己惊吓。一张大门锁着。另一张大门锁着。另一张大门还是锁着,就像一场瘟疫留下了突然的空阔。声音在这里出现了奇异的放大,一片树叶的轻落,一只蝴蝶的飞掠,一缕微风的穿过,几乎都是这里震耳的惊雷,震出天地间滚滚的声浪。还算好,我找到了一间有人的房子。但留在这里的老人和小孩似乎已经习惯了寂寞,不大说话,只是倚着门,直愣愣地看着我。你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眼光里有欢迎但没有惊奇,看我离去时有欢送却没有惜别。也许他们已经生疏了人间交往,常见的世界只是泥土和泥土和泥土和泥土和泥土,常见的活物也只是野兔、野麂以及飞鸟。那么我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只人形的鸟,即算挂着古怪的墨镜和照相机,也还是一只鸟,一只稍微有些特别的鸟,不过是来此落脚,吃点谷米,撒点粪粒,然后又飞上前面的山冈,离开他们的视野。
我问他们:打工的人会回来吗?比方说,过春节的时候会不会回来?
他们说: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
我问:他们总会要回来的吧?
他们说:当然,总要回来的。
我看见了好些空屋都充当着库房,堆放着一些杂物,有烧剩的干柴,有破摇篮或者旧水缸,当然更多的还是一些农具,比方木头大禾桶,是以前给稻子脱粒时要用的;比方说木头大风车,是以前给谷粒去壳时要用的;还比如木制的龙骨水车,复杂和精巧得像巨大的骨雕项链,是以前抗旱引水时要用的。眼下,它们用不上了,或者说是被更先进的金属机器替代,只能在这里蒙上尘垢,冷落在某个阁楼上或者墙角里。奇怪的是,主人把这些东西都保留着,没有把它们烧掉,好像它们还会有用上的一天。
在这些人家的屋檐下,在横梁上或者走道里,一定还停放着一具或者数具棺木,不可一世地占据着很大的位置,翘起的棺头更有点趾高气扬,只差没有喷出呼噜噜的鼾声,或者高声大气的一个哈欠。
我知道这些棺木是主人们的宝贝:一户人家如果有这样的棺木,足以证明这一家略有积蓄,还有对未来的及早准备,常常引起他人的羡慕和称道。生活从此就可以过得踏踏实实。
我还突然想起了前不久院子里的一只鸟。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这只鸟在林子里呱呱呱地大叫,搅得我根本无法入睡。我只得摸黑去寻找和驱赶,用木棒敲击了好些树干,用石块射击好些树杈,但最终不知它藏在哪一片墨色的树影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鸟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而且发现这只鸟就死在石阶上。它身上没有任何伤痕血迹,只是瘦成一包壳,掂在手里轻飘飘的,像一片影子。它有蓝色的翎毛,有橘红色的眉圈,有眉心间的一点纯白,其实美艳惊人。
它为什么死在这里?它是不是带来了远方什么不祥的消息?抑或远方什么喜庆的消息?曹家老头曾经低声说过,要我注意初秋夜晚里的动静。我这才发现,那老头看似疯疯癫癫的,其实是个知情人,对我早有暗示。在这一刻,我甚至相信七十年前七百年前七千年前七万年前所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是知情人,对今天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他们大概早就知道,早就在口口相传,有一只无名的鸟今天将回在这里,死在露水和晨光之下。
我把它埋葬在竹林边,踩紧了一堆新土。
(选自《文学界》2005年5月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