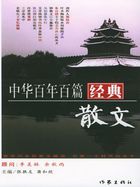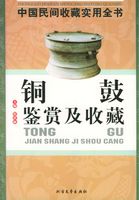一、威瑟拉德堡
一串晶莹透明的竖琴声,牵引出一个皇朝古堡的兴衰。威瑟拉德堡悬崖上,屹立着一只目光锐利的历史之鹰。在游吟诗人的浅唱低回中,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复活与重现了。诗人和诗——荒漠中的一串驼铃与足印,大地上的一群神秘精魂,创造者与收割者,灵魂与精神的黄金,像传说一样写在开头。一个时代与它的诗人和诗歌同步。在时间的那一端,对人们如此叙说的,不仅仅是时光——辉煌与衰落。血脉像河流一样奔涌不息的精神。能见度极好的阳光穿过纯粹而含氧量极高的中古清洁空气,照射在古老的威瑟拉德堡一片耀眼的金碧辉煌之上。布拉格的鹰在飞翔。时光深处的隐隐约约,历史一路走来,粘着远古的泥土和斜阳气息,一路风尘仆仆。转眼之间,它已卓立于眼前,像一位带有玫瑰香气的森林少女或英武的古堡少年。古城堡依旧令人热血澎湃。古老的威瑟拉德堡外曾一度风光旖旎,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原野和森林。那条著名的河流环绕而过,像一道美丽的金边,为城堡留下永远美好的记忆(人们曾以为这是时光永恒的面容)。然后,它离乡逶迤远行,决绝而勇敢……夕阳。古堡躲到一片金色后的黄昏里去了,像慢慢西下的太阳,结束了使命的它永久地歇息于黑暗之中,像静物。但历史并不因此终结,或许它才稍稍开了个头——一个王朝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吗——时光自有其脉搏和年轮。城堡廊下的石柱和峭立的悬崖默默,伏尔塔瓦河悄悄绕崖而去……一个灵魂在徘徊。它有着一双留住历史的时光和空气之手。斯美塔那失聪而痛苦的耳朵里传来的歌声,如河里的波浪日夜磨炼着他脆弱而顽强的神经。威瑟拉德堡的鲜花绽放出的时空灿烂,和最后一声温暖的叹息令人荡气回肠和灵魂慰藉,像思乡的一剂良药。
二、伏尔塔瓦河
伏尔塔瓦河,由一冷一热两条溪流交汇而组成的河,晶莹剔透,仿佛永不枯竭,由历史的诸多元素组成。像两只上下翻飞的蝴蝶,在历史的山坡上飘飞,像时光深处的一个传说,交汇成一条精神之河——令任何走过它身旁的人都无法不为之心动的灵魂之河。除了大地,还有永恒的波希米亚精神,血液和骨髓的流淌成为每一个波希米亚人的生命因子和遗传基因。喝伏尔塔瓦的精神之水成长起来的人们,每当提起它便不禁像河里的波浪一样心潮澎湃,它纠缠每一个游子的梦。伏尔塔瓦。波希米亚。伏尔塔瓦+波希米亚=永远的精神抗争=流动的纪念碑。凭它一个民族足以无敌和不朽。这就是伏尔塔瓦。这就是波希米亚。这就是布拉格。斯美塔那、德沃夏克、库克利贝、雅纳切克、马蒂农、哈维尔、米兰·昆德拉……塔波尔战士和胡斯党人——这一长串名单就是历史,就是一切?如历史与河流一般绵长的,并不仅于此,还有波希米亚精神的大地和奔流不息的一切的孕育。诸如历史、花朵和暗夜里的光……像尼加拉瓜瀑布一样的背景。
美丽的、令人荡气回肠的、日夜难眠的伏尔塔瓦河从历史深处流出,波光粼粼——于森林中聆听过原始狩猎、溪流的平缓节奏、乡村之舞、月光仙女的身姿、飞泻的瀑布。既像朴素的村姑,又像华丽高贵的少女,熠熠生辉,款款而行——波希米亚独具的魅力和财富……鸟语花香的草地、雄伟的森林和原野的诗意和情感,从山林的那边来,到海的那边去,要流过曾经宏伟的威瑟拉德堡和如今同样宏伟的布拉格。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古老的神秘时光,一直到大海——宽阔无边的精神之源——只是为了呈现一个奔流不息的意象?
温暖和慰藉着波希米亚大地上所有曾经与依然寒冷和饥饿的灵魂,让人永远不能平静的灵魂之河,斯美塔那有力的双手抓住了它,像力挽狂澜的舵手。
这样的双手蕴含着的力量,或许就在河畔最初的篝火、舞蹈和泛滥和灾难中,深情的弦乐群、激情的铜管和高亢的锣鼓……这样的双手一再让一大堆木头、铜铁、管弦、锣鼓一唱三叹、如醉如痴、忘乎所以,像同样奔腾着的伏尔塔瓦,至今如此,且永不休止——有雷鸣般疯狂的掌声、喝彩为证,它们似乎于历史的梦中惊醒。
三、萨尔卡
值得记住的不应只是那个男权时代——捷克娘子军的传说曾在波希米亚大地广为流传,她们用耻辱、痛苦、热血和生命送葬了一个时代。萨尔卡——被迫、勇敢、智慧、美丽而致力于战斗的波希米亚妇女。一段历史的终结者与改写者之一、女性领袖。姐妹因她而悲伤与狂欢。
萨尔卡美丽的眼睛在哪里呢?在罪恶男权时代的每一个女性的悲泣、哀号与期盼里。伏尔塔瓦——波希米亚的精神之河,填满她们仇恨与爱的精神之河——河水无论如何都无法洗清她们的肉体和灵魂之耻,只能用沾满血的锐利尖刀来解决了。深夜的篝火、狂欢的酒舞和黎明前黑暗里的灯光,狂欢后的士兵们已经疲累了,他们丝毫感觉不到梦中的冰冷利刃,嘴角尚余一丝私欲满足的微笑。深情的她们只能对他们举起仇恨的尖刀,她们一定想起了那些母亲们的眼睛,但她们依然要把利刃插进他们的胸膛。历史的罪恶者总是让它的儿子用性命来抵债。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没有记忆的历史,这就是循环着的人类史。这是否是波希米亚妇女——萨尔卡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历史的应答?夜又一次暗下来,黎明就要来临了。唯有手握尖刀的颤抖的手和心?……上帝流着泪,背过脸去。
这是那个民族血流得最多、最重的一页,像最暗的黎明前的黑暗?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斯美塔那如是说,是为了告诫自己的民族时刻警醒历史曾有过最为可怕的一页,抑或是精神的战栗和痛心疾首?他的双手神经质般地颤抖着,记忆又一次漫过这位灵魂孤独者的锥心之痛。
四、波希米亚原野和森林
迷乱、开阔无边的波希米亚原野和森林,从四面八方涌来。“四面八方”——一个致命而沉重的词语,像核与原子武器打击到人们情感最脆弱的部分。谁能经得住如此经久而狂风一般的打击?这原野和森林中,还躺着死去的朋友和亲人的灵魂。它们日夜于坟墓和河畔歌唱、张望。波希米亚枝繁叶茂的森林里,同样藏满日夜歌唱的鸟儿——倏然的歌唱或许更能惊起似乎已经麻木的心灵,像夜晚惊梦之后无法入睡的双眼。往昔的欢乐、沉思、恋爱、深情曾怎样萌生于人类精神的开阔与繁茂地带?如今它们是否已长成参天大树和情感的密林?还是夭亡一般绝望地逃走,成为一个虚无的历史传说?阳光照耀得令人屏息的熠熠闪烁、树叶沙沙、鸟儿的歌唱仿佛永不停息、蛙鸣中的铜铃、瀑布悬置天边的风景,那浩浩荡荡、由远及近、渐渐清晰的原野与森林。已经来到、将要来到的、永无止息的,河畔、原野和森林里的歌唱,击打出生命最强烈的歌唱和最无可名状的节奏和情感。
原野和森林里走出的迷人村姑,明眸皓齿,带着田野的花香摇曳而行,像星星一般行走在波希米亚梦一般的大地上,如田园诗一般坚定地款款前行。这时才让人明白,美是如此难以抵挡。由黎明的长笛奏响和引领,诗一般的田园,家一般的温暖,什么能够阻挡铜管发疯一般的前进?让人知道的还有,原来如此纤细之美是如何演变为一场进行曲一般的憧憬和期望的——热烈的、不可扼制的,绵长的、遽然起伏猝不及防的——原野、森林,森林、原野一般的美丽。
像一个狂奔于原野的青春少年手执一把鲜花,激动得呼吸明显节奏失调,累了就去岸边繁花的梦里去重温。斯美塔那一不小心将自己变成一个轻佻的采花少年——老夫聊发少年狂!老夫子已率先将自己激动得一塌糊涂了。多少个失眠之夜,耳中鸣响的噪声比贝多芬还痛苦的绝望里,他还要求什么!没有忘记吟唱的美丽。
让他在这样的土地上彻底放松、甚至放纵一次吧!应该肆意放纵的还有那些铜管和打击的锣鼓们,或许它们已经很久未亲近到情感云团如此密集的波希米亚原野与森林的天空了。
五、塔波尔城和布拉尼克山
塔波尔城和布拉尼克山同样是一种精神象征。战士,一个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素质取决于其战士的真假和优秀程度。战士,这一纯洁标志的词语,更多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标志,与野蛮的武力几乎没有关系,真正的战士总是避免使用武力。让斯美塔那感到自豪的是这个概念在自己的民族并不是一个被占用和污染的象征,而是真正属于自己和自己的保护者——上帝。
战士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之魂,其本身固有的灵魂,让真正拥有自己战士的土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也许是波希米亚——捷克民族历经磨难、屈辱,在一次次灭顶之灾里巨人一般重新站起的力量之源。这个让人敬畏的民族,支撑它的是什么?背后的一切——几乎无法想象的坚实和丰富的一切,无论如何想象也不过分。波希米亚不朽于伏尔塔瓦河于此泛起的人类精神最纯粹、激越而有力的波浪。塔波尔城和布拉尼克山制造波希米亚精神穹顶的同时,也为连绵不断的人类精神的峰峦起伏制造了又一惊心动魄的一幕。隐约响起的威瑟拉德堡的歌声?不,是塔波尔战士的故事和传说,用它们支撑和结束一首交响诗。用音乐把故事和传说雕塑成纪念碑的力量,这分明是与人类精神重合的那一部分——内化为人类的本质成分,这是斯美塔那不朽之所在。
……斯美塔那、德沃夏克、库克利贝、雅纳切克、马蒂农、哈维尔、米兰·昆德拉……请允许我再抚摸一遍这一长串名字——波希米亚大地最黑暗的暗夜之下,是他们在纷纷涌动。塔波尔城保卫者的灵魂和布拉尼克山一般的身影,以及他们背后的默默无语者,同样如布拉尼克精神之山一样雄伟高耸。他们和英勇的保卫者们再次重合——胡斯党人、波希米亚的卫士们。
上帝的战士。真正的战士属于上帝。《上帝的战士》——斯美塔那为英雄选取一段古老的圣咏,恰切描述这些为保卫和拯救大地和历史而牺牲的勇士们——不止这些,人们一直固执地认为,那些为国战死的勇士们并没有死,他们走进了布拉尼克山和传说——人们总能为殉难者找到一个适合灵魂永远安息的地方。于是,故事开始在波希米亚四处流传:英勇的胡斯党人的精魂在那场血战之后并没有死亡,而是趁暗夜悄悄潜入了每一块石头都十分英勇的布拉尼克山。每当波希米亚大地危难之时,精魂们便会鱼贯而出,遍布山林和原野,神出鬼没,处处都闪耀他们的身影,这样的大地还有什么危险可言呢?他们活在人们的记忆和憧憬里——人们让他们在故事与传说里不朽。一首世界上最长的交响诗于此圆满了。失聪的斯美塔那选择最为简洁有力的一搏!之后他知道自己依然要去忍受比贝多芬还要痛苦的失聪的日夜耳鸣,直到写出最后的歌(带有自传性质的弦乐四重奏《我的一生》和后期的几部歌剧都于此坚忍创作)。
六、波希米亚河
难怪流亡他乡42年的库贝利克,在1990年“布拉格音乐节”上,一再压抑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过于激烈。曲终,忍不住当场老泪纵横。面前坐着的同样激动得无法克制、曾为捷克的民主自由历经囹圄之苦的总统——哈维尔及其夫人。此时,两个精神和肉体双重流亡者的心中(精神重逢?)又是怎样难解而融洽的滋味——能够有资格在“我的祖国”亲自演奏和聆听《我的祖国》。在这两个流亡者心里泛起怎样同质而不同色彩却同样猛烈异常的波浪——像伏尔塔瓦河那一冷一热源流涌起的最终波浪?难怪波希米亚的音乐家们说自己轻易不敢演奏这首曲子:“说实话……移民后,我一直避免演奏《我的祖国》,因为我怕自己会太情绪化,我想我一定无法控制面对观众时的情绪,所以我一直拒绝演奏它。”(世界著名捷克指挥家佩塞克);难怪它会成为捷克爱乐乐团百演不厌的经典保留曲目,每一次演奏都同样如醉如痴、忘乎所以。有时会响起30多分钟之久、似乎能够再现和见证整个民族苦难和屈辱的掌声,《我的祖国》——威瑟拉德古堡、伏尔塔瓦、妇女萨尔卡、无边的波希米亚原野和森林、塔波尔城和布拉尼克山,一次次定格在世界各地的无数个黑夜、白昼和心灵里。
“上帝的战士”和威瑟拉德堡主题最后的交相辉映,像力量的河流汇聚成汪洋大海。历史和现实交织重叠,江河一样汹涌澎湃、彼此呼应,构成了人们对波希米亚大地的记忆。以一个民族的历史,创造了一个交响诗世界的神话——斯美塔那不可避免地成为捷克音乐史上的丰碑和神话。波希米亚旋律唱响在另一种历史里,伏尔塔瓦河流淌在另一种时间里,这就是音乐世界的持久魄力?伏尔塔瓦河在音乐里流成了波希米亚大地的精神之河。
伏尔塔瓦河,这条从首都布拉格穿城而过、孕育一长串耀眼名字的河流,为每个捷克人提供不可缺少的精神元素和母语感,像孩子只有母亲陪伴时才能安稳入睡一样,人们在它身旁才能感到灵魂安慰。这条几乎流进每个捷克人骨髓、蕴含着波希米亚民族精神的河流,同样预示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它有着一种内在的节奏,像宇宙的规律一样准确,像一首歌在人们心中唱响,这首交响诗已将神秘的历史内化为一种内在节奏——历史和民族精神竟在斯美塔那无声的世界里复活了。其实,斯美塔那已经把自己内化为波希米亚民族的一部分,把交响诗当成一种民族精神的隐喻和象征——他让自己完全消失在音乐里。
但就是这个被誉为“捷克民族音乐奠基人”、“新捷克音乐之父”、“捷克的格林卡”的波希米亚人,第一位以波希米亚民歌和历史写作的精神信徒,在忍受失聪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时人侮辱性的评判:“不能再对他有所期待,因为他甚至为了博取大众的同情而装聋。”后来知道,类似的评价和攻讦竟是不朽者的标志之一。
波希米亚河因此而不朽。
2004年7月20日冰雪里的燃烧
俄罗斯大地的凛冽暴风雪中,一颗炽烈的心在跳动。与寒冷异质却同样猛烈的心跳席卷、温暖着冰雪覆盖的俄罗斯。它的炽热足以融化整个大地的冰冷,这一切出自这个除音乐之外几乎不为世上的一切所动的灵魂。音乐的灵魂和思想在这个尖锐冲突的矛盾体身上,音乐张力使音乐的每一个元素都暴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近乎风暴中心的音乐真空状态赋于音乐一种魔力,使人一靠近它便感到眩晕。而貌似相同的音乐元素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如同岩石熔化为其他物质一样,音符具有了双重性或多重性,相同的只有形式。拉赫玛尼诺夫,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的确是一种误读或不可名状下想象力失却的匆忙呓语——其音乐之复杂远非浪漫主义一词所能涵盖。只是在他这里,形式显得如此无足轻重,一些拘泥形式的人认为他的音乐形式显得过于苍白而乏有新意,而这种无视灵魂内在的浅薄曾不止一次让这个对人类充满善意的人陷入绝望。
冷峻、阴郁,“六英尺半的愁容”的冰冷外表下,内心却像燃烧的石头一样,时刻迸溅着情感和思想的雷电,像一个浑身通电或着火的人,在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之间频繁转换着角色,在大地上挥洒着生命激情。像一个急于赶路的人或饥不择食者一样,拉赫玛尼诺夫顾不上在形式这种问题上耗费时间,在现成而简单质朴的浪漫主义形式上“省力”地行走,形式对他来说并不是问题——他竟然忽视了形式。拉赫玛尼诺夫是一位直接用灵魂和思想来演奏和作曲的音乐家。
如此,人生终点、半生流亡的拉氏才得以写下了一首即使以现代主义著称的作曲家也难以超越的人生绝唱——《交响舞曲》,从内容到形式都超越了浪漫主义概念范畴。音乐元素和组合手法之多元复杂令人应接不暇。组成这部交响曲的三首曲子与舞曲形式根本无关,只是借喻猛烈的生命之舞。他用极其现代的意识为乐曲的三个乐章分别命名:清晨、中午、黄昏——用三个截然不同而顺序更替的阶段表现复杂的人生,其手法简略和概括力可见一斑。致命的是拉氏以此总结一生,作为自己人生的终结曲。
人生的清晨却涌动着阴郁低沉的块状云层,阳光镶上闪亮而阴暗的金边。儿时充裕生活的美好回忆因短暂和匆忙而让具有天才灵魂的他痛心疾首,一场人生的激烈抗争仿佛来不及准备便开始了;中年的主旋律——匆忙而节奏杂乱,仿佛一个为生存和音乐而四处奔忙的灵魂,不和谐音像幽灵一样追寻着他,双簧管制造着危机四伏的氛围,令他无法喘息。流浪者处在物质和精神的异乡,“故乡”的期盼成为他表达的动力和音乐本身,不和谐音和音符之间的张力让他的灵魂无法宁静却藏有不可思议的能量——这便是他给予中年——中午的定义(精神的眩目期)。钟声响起,人生黄昏的冥想如此悠长——漫长,令人惊慌、心悸而压抑。像一场虚脱的梦,大汗淋漓,无力感,疲惫感,绝望,黑暗无可避免。一切抗争都显得如此徒然无力,夕阳坠落的速度并不因任何力量而有丝毫减缓。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整部交响曲激情四射,一气呵成,迅猛富有张力——在生命行将终结时仍蕴含着如此丰富的生命能量。像冲进大气层的陨石,迅疾地燃烧着划过和照亮广寒的茫茫太空。然而,他“六英尺半的愁容”却并未因内在的燃烧稍有改变,仍然冷静得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将情感和思想熔聚为生命合金然后急遽燃烧熔化,这种双向的生命演进过程(积累和消耗)在同一生命矛盾体的同一时刻完成而不动声色,拉赫玛尼诺夫音乐的最奥秘和精髓之处。
浪漫主义这条破旧的漏船,已无力承载拉氏化腐朽为神奇的激情、不可估量的生命能量和丰富清新的音乐元素了。因此,与其称他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倒不如称之为浪漫主义终结者更恰切一些——他一挥手便终结了整整一个浪漫主义音乐时代。木质的钟情与赞美除了鸟儿美妙的喉咙,木头发出的声音无与伦比。温暖、宽厚、亲切、柔软、朴素、自然……可以用一切美好的词语来形容。能够发出美妙声音的乐器大都与木头有关,教堂、音乐厅等一些靠近声音本质的场所,木头是其主要构成部分。除非必要的响亮和抒情,人类是忌用铜及钢铁乐器的。或许人性和神性不允许这样,还是木头更接近灵魂与自然?或许木头作为最靠近人性和神性的发声物质,通常更能表达人类对上帝的赞美和钟情。
莱比锡托马斯教堂、米兰大教堂、青岛圣艾弥尔大教堂、乐托·达姆修道院,静穆得没有任何声音,座无虚席。人们因敬畏和崇拜主而灵魂寂静。只有木质的声音,与之合奏的是教堂木质结构的深阔空间——它们成了一种乐器或听众,铜管们仿佛只是某种黄金般的点缀——这些声音们因而具有更为明亮而温暖的色彩,像女人们佩戴的项链或十字架。哥特式的雄伟廊柱和尖顶直逼天空,十字架像人性的避雷针保护着这个群体,以免人类不幸触电;又像是靠近上帝的敏感信号线,人类借此接收来自天堂的消息。
声音却是如此平和与宁静——难道因为是木头们发出的吗?与木头最为契合的人声:“天主慈悲我!”唱诗班的吟唱仿佛从天堂雪一般倾泻而下,变得同木头一样,木头也具有了某种温度。肉质的、带着温暖呼吸和热血奔涌的吟唱,如同大地或平原一样起承转合,与天上的星辰和空气相接。因与木头和上帝接近,赞美和钟情也就具有木头质地,世界顿时被木头的温暖怀抱着,这样的声音是可信的,让人感到如此平常,上帝仿佛触手可及,如同大地上籽实饱满、头颅低垂的庄稼们一样——上帝蕴含在万物之中,也存在于谦卑与苦难之中。因为拯救了人类的罪而使人类充满灵魂的慰藉和得救。也只有用生命和血救人于水火而对人类的爱不变的灵魂才可以被称作上帝,上帝的救赎超越人类的想象力。
此时,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痛苦呻吟对人类来说却是如此温暖而没有伤痕,以一己的伤痛和生命拯救人类所有的伤和罪。人类只有感恩和喜乐。对于这样一个灵魂,人类也只有用喜悦和赞美来报答,任何的痛苦和伤痛则是渎神——从宗教原理上说,耶稣之后大地上不应该再有痛苦——而宗教裁判所或奥斯维辛之后不应该有诗,则是人类没有看到自身的罪恶——面对苦难喜乐,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因此,人类一次又一次在对上帝的赞美里洗净自己,木头做的十字架一次次将我们托起。木质的赞美和钟情或许更靠近心灵,大地上木头离人类最近,木头更能使人类感恩而又不至离上帝太远,可触可感,一如上帝冬夜之火炉。
巴赫,这位全心侍奉上帝、几乎一生都在为上帝写歌的乐师,在9岁、10岁相继失去父母后,最深切地体会到了上帝之爱。这个一生赞美上帝的人,为什么在49岁上写出如此平易具有木头质感的《B小调弥撒》?面对知“天命”的年纪,或许此时上帝对他来说已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他要做的只是把心中对上帝的感恩写下来。平易、纯粹,不亵渎上帝之爱,所以他选择了木质的声音靠近上帝温暖而寒冷的心。他知道,这种声音是这个世界和上帝最需要的,像棉花一样温暖和柔软。不似他的其他一些宏伟音乐似乎没有全身心地接触上帝。“每一件艺术作品,无论是一首诗作还是一座教堂的圆顶,都显然是其作者的自画像……”(布罗茨基)巴赫藉此靠近上帝。
离上帝最近,也许是他献给上帝音乐的标准之一,所以,这一首,他让自己的声音具有木质的属性,显然,木头具有铜管无法比拟的优势,仿佛人类接近天堂的天梯,人们可以借此无限地接近上帝。人类饱含上帝所有的荣耀。愿上帝与你同在。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