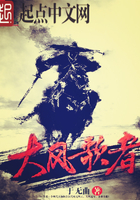我还是决定要写书。无论如何,二万六千三百四十六元还是钱,是老兵的全部遗产;无论如何,老兵把我当成了能为他(他们)写书、以让他(他们)灵魂安息的作家。我们往往对死人的尊重大于活人,如果是活人,有当面反悔的机会,对死人就没有了。写到这里,读者可能认为我写书是出于无奈,其实不是,当我真正拿起笔写的时候,那笔横财已经找到了好去处——老兵基金会。
写,一张纸,一支笔,要像模像样的话,再加一杯苦咖啡。我是有点文采的,上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基本上都上墙报,工作后写过豆腐块,也上了报缝。这次要实现一个跨越——写一本书!我有些激动,我喜欢干有跨越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写成了豆腐块,我写老兵,老兵翻来覆去就那么点经历,长官说冲就冲,说开枪就开枪,然后,死了一片又一片人,让我一点想象力都没有。我求助于苏黎,让他给我提供几个抗战老兵,供点素材。苏黎说,“你还真写啊?我就那么一说,是哄老兵高兴的。姐,要我说你就写几篇文章,纪念纪念,你不要为那两万多块钱心里不安,那钱权当是稿费和我们请你帮忙的工钱。”我说,“我现在的想法升华到什么程度你是理解不了的,我是要为这个民族写历史,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一次卫国战争写篇章。我们非常需要一部悲壮恢宏的、需要我们全民族铭记的英雄史诗。”我本来是想调侃,但话说出来成了那么义正词严,把自己感动得都热泪盈眶了。
苏黎像吓着了一样沉默了半天,说,“姐,我支持你,咱区里没有国民党老兵了,我给你到区外找,市里、省里只要有,我挖地三尺也要给你找出来。如果你不满意,咱可以到外省,到可以找到老兵的一切地方去找,我在这方面有人脉。姐,我也突然感觉到真应该写这么一本书了。”苏黎说得很真诚,这份真诚无疑给我的锅底又加了一把柴。
苏黎说到做到,当天晚上就给我送过来一张单子,上面列了十七八个老兵的信息。第二天我就按图索骥一口气跑了三个县,见到两个老兵,我风尘仆仆、焦急万分,我不是把写书当成了一件迫在眉睫、只争朝夕的事情,而是跟死神赛跑——这些老兵已是风中的蜡烛、没油的灯,没准我晚了哪位一步,就给写书造成了很大遗憾。在我眼里,这是最后一群濒临灭绝的、珍贵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活载体。结果怎么样呢?跟第一次的情形一样,我听的时候深受震撼,写出来的仍然是干巴巴的豆腐块,而且是大同小异的豆腐块。制造了几个豆腐块后,我苦恼了。苏黎说,“姐,这结果一点都不出意外,能活到现在的,当年都是些傻乎乎的兵娃子,能有什么呀?我们找错挖掘素材的对象了,我们应该找个当官的,有经历才有东西写啊!可是,我到哪儿给你找呢?”
我热热闹闹搞了这么一大圈子,没有一个老兵不知道我是要为他们写书的,没有一个不泪水涟涟,对我感恩戴德的。有一个我们泾阳的老兵,住在北边的嵯峨山上,孤苦伶仃一个人,住着一孔几辈子前的破窑洞。这个老兵有文化,在参军之前是位教师,因为年轻,热血激荡时带着一群学生一起参加国民党军奔赴中条山抗日前线了。听我要写如此一本书,嵯峨老兵从将近窑洞顶的窑窝里掏出一个铁盒送给我,说是他父亲传给他的,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这东西是有灵气的,不要随便打开放了气,等写不下去的时候,打开煮一点喝,就能写下去了。看着嵯峨老兵老得不能再老的脸上笼罩的神秘气息,我小心翼翼地接了过来,其实我并不想要,这些老兵们的东西都有一种腐朽气息,但经验告诉我,如果我不要,他们立即会像小孩子一样跟你翻脸,那样你就要花不少时间说好话抚慰了。这铁盒里面是神丹妙药?出于好奇,闲暇下来,我把铁盒打开了。几层麻纸,一动就碎,确实年代久了;扒开麻纸是油纸,油纸较结实,剥开,是一块用红色丝绸包裹的东西;再打开丝绸,一个做工极其精致的红木盒出现了,盒盖上雕刻着“泾阳裕兴重茯砖茶”字样。我惊呆了!这是一块民国时期的老砖,泾阳县新建起的茯茶博物馆收购这样的老砖,起价就一百五十万。但这块砖茶代表的不是巨额钱财,而是一个耄耋老人对我殷殷的期望,我怎么能忍心放下笔让他空欢喜呢?可我又写不出来!老砖再有灵气我也不能喝,我是喝泾阳水吃泾阳粮长大的,我希望泾阳的茯茶产业发展壮大,我想动员嵯峨老兵将老砖捐给泾阳这块土地。我写不出来,我苦闷极了。苦闷就回家,把苦闷讲给母亲听,这是我们家所有人的习惯,包括我父亲。母亲总是能把我们从苦闷的羁绊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