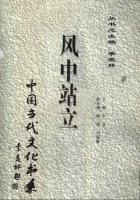麻柳沟尾有座背篼山,背篼山顶有个背篼寨。当地盛传:高不高,拉湾寨,矮不矮,水田寨,半天云头背篼寨。
背篼山孤峰独立,高耸入云,远远望去,状如背篼,因形取名,相沿至今。背篼寨又矗立于背篼山之巅,像巨人顶戴的冠饰,悬巍巍,颤巍巍,其险其峻,不言而喻。
夜来读书,阅到《理番厅志》记述的许多名胜古迹,诸如:熊耳秋风、牛心古灯、箭山晚照……却无背篼寨的只言片语的记载。我为此感到奇异和遗憾,找到附近许多老民村学,方知其一鳞半爪——
据传早在元代,岷江上游一度诸侯割据,不归大统,土官与土官、土官与朝廷之间在这里征战杀伐数十年。在厮杀中,部落头领争先抢占有利地形。而当时争夺最烈的要数这背篼寨。最终有个实力最强的达纳部落争得此地,从此,占山为王,世代生生不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因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得罪清廷,乾隆皇帝前后用兵十余年。为了扫清途中障碍和占据有利地形,清兵便急于攻下背篼寨。哪知这山寨易守难攻,除了上山进寨的一条独路以外,四周均是悬崖绝壁,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再加上山民骁勇无比,临危不惧,清兵攻打数年,除了丢下成片的尸体外,毫无尺寸进展。直至金川之役凯旋,背篼寨仍然固守在达纳部落的手中。四川总督不服,奏请皇上再度用兵攻打这弹丸中的弹丸之地。聪明的乾隆皇帝因有金川之役之得失,遂御批:无功则留。意为攻打没有成功,就让它保留下去吧。于是,多少年来官方将背篼寨又叫则留寨。而老百姓仍然老叫不改,直呼:背篼寨。
乾隆何许人也?他的“无功则留”的御批,是“十全武功”“千古一帝”绝无仅有的遗憾,是一头雄狮面对身上虱蚤的无奈!
不可小看,这万山丛中,云端高地,生息着一支强大部落的后裔。他们是山民中的山民,是劫后之余生,是血与火中的魂灵!
慕名引起关注,关注就想实地一见。利用假日,笔者呼朋唤友直奔背篼寨。
这是一个仲春时节,一个虫虫蚂蚁都晓得躁动的时节,我们驱车行进在麻柳沟蜿蜒曲折的机耕道上。麻柳沟不见一树麻柳,是天绝还是人灭所致不得而知,不然缘何取名麻柳沟呢?映入眼帘的是怪怪的岩石、蓬乱的雷蒿和张牙舞爪的狗牙刺,行进中它们像银幕中的景,“呼—呼—呼—”地由远而近直扑过来,抵拢眼前一晃,“刷—刷—刷—”地又由近到远离我而去,周而复始,杳无一迹一痕可留。山弯连着山弯,坡道接着坡道,人在车中,如砂锅煮豌豆,跳得翻。好不容易挨到沟尾尽头,我们赶快下车,心里想:谢天谢地,这般路况,有,不如无。还是用自己的“11号车”行走稳当。
上山的路又细又长,好像一根若隐若现的蜘蛛之丝飘曳于悬崖峭壁上。过了一个斜坡,上了一道偏桥,登上一个山冈,来到一个路边的岩洞,洞内有三个石头,等腰三角形地立着,里面堆满了燃尽的余灰,岩壁上全是漆黑漆黑的烟油,呛鼻的烟尘和霉味告诉我这是遮风避雨、过夜留住的途中居所。
前面是一道高高的山梁,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登上了这道山梁,目的地就不会多远了。高度在上升,力气在减弱,但我们毕竟在前进。鹞鹰在空中盘旋,呼啸,白云在脚下翻滚,幻化。风过云去,格外朗然。向下一看,山上山下万丈深渊,两腿有些筛摇起来。朋友告诫:小心攀缘,万一不慎,掉下去做烟包皮都使不得。谁都想象得到“烟包皮都使不得”是啥惨状。我们干脆找了一处稍微平坦的路边歇下来。我靠在一块“椅子形”的岩石上,伸着软脚,望着蓝天,喘着粗气……清风送爽,揩着倦人的汗,抚摸着爱山爱水的人。这时,山下不远处传来阵阵清脆的铜铃之声,不一会儿铃声靠近了我们身旁,眼前蓦然站着一头灰黑灰黑的毛驴和一个虎生生的小伙子。毛驴驮着两袋沉沉的货物,它在路边伏下头,咧嘴闻着干驴粪,吹了几下响鼻,突然仰天吼了起来,其声之大,仿佛大山都快抖垮下来了。驴声刚落,小伙子吆喝一声又开始赶路起来。我问寨子还有多远,小伙子说不远了,过了大树子就到了。说完“噔—噔—噔—”轻捷地登高而去,淹没在疏疏的山林之处,只听到铜铃之声渐弱渐小,大山渐渐恢复着寂静。我想起不知是谁写的一句诗:那人,那山,那水。不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水、人应该是协调、通融的。人,毕竟要生存。
好不容易爬上山顶,来到一棵大柏树下。这是一棵造化千古的神树,树身约有五丁合抱,枝丫坚挺,叶碎小,却茂密长青,岁寒而不凋。虬曲的根像龙爪一样死死抓住岩石的骨架,背依古寨,侧临危峰,确为山中一景。站在树下可以仰观背篼寨全景:这是一个平坦开阔的山寨,足有上百户人家。春播已过,平旷的土地已经铺满银白的地膜。土地的边缘是萧苏的荒林,不时传来野雉“啾嘟”之声。寨中高碉林立,云烟袅袅,墙连着墙,房挨着房。只要走上一家房顶,就可平履全寨人户。这里一户是百户,百户也是一户。这是典型的“东方古堡”,它的建筑,真可谓:相互依存,生死与共。
走到寨口,几只小狗跑出来狂吠不停,不一会儿围了七八个赤着脚、裸着肚的娃儿。他们衣着驳杂,未成体统,有的斜戴着“公安帽”,有的持着木枪、木棍,怯生生地瞪着黝黑的葡萄小眼。我们问村长在家么,他们说“不晓得”,嘻嘻哈哈,做了鬼脸,溜了。
寨子的巷子很狭窄,很阴,又很长,像一根神秘而深不可测的暗河。人走在巷中,软软的,像海绵一样。原来,这里垫了草,沤了粪,人畜共通一途。每天早晨,成群的山羊像雪浪一样从圈里涌出来,约定在巷里下粪蛋。这粪蛋通过人畜共踏,不经意捣磨成了细粉,像烟丝面面,绵软酥和,人过巷中不亏脚,不怕跌,不失为国内巷中之一绝也!不过这粪便积多了易生虫虫,每到秋夏,蚊蝇四起,臭气熏天。人过巷中不敢出大气,免得吸进几只飞物,屈遭一场“铁扇公主”的际遇。再加上狗在墙角尿,猪在四处拱,天长地久,地久天长,这滋味怎生了得!有人对这般沤粪提出异议,老民却坚定地说:“人吃油盐,田吃粪草的嘛。”
走到村长家,村长姓陈名保,但都唤他长命保。村长家在当地是排得上号的家庭,他有五男二女,二女均不到二八之龄就远嫁坝区,剩下清一色五个“公牛儿”。山上人爱儿又怕养儿。有儿有劳力,但山寨自古阴阳失衡,“公鸡”多了,哪个下蛋呢?眼下,长命保家境尚佳,但若拖上几年,几个“好劳力”配偶无着,他们只得在外乡打工、上门。这个火红的家庭可能要锁门。
步入堂屋,火塘上,梁椽上,仓房上全都挂满了猪膘、野味,完全可以称得上“肉林”之家。而龙门垣墙堆满了柴捆子、柴花子,柴码的头面收拾得整齐如切,米脂般的油松送来幽幽的芳香。自古以来“柴、米、油、盐”中,柴是居家的第一要务。山寨的显强竞富,并不是钱,也不是粮,而是堆积如山的柴码子。
村长将我们带到杨狗狗家。敲了半天门,屋里才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门一开,几只“午睡”的鸡从脚下四处飞蹿起来,有的上了灶头,有的往灶坑里钻,有的还飞到了床铺上……灰尘满屋,鸡鸣狗吠。女人怀有身孕,已是大腹便便,羞怯地招呼我们“坐坐坐”。她拿了几只满是茶垢的瓷盅,撩起自己的围腰帕擦拭着,盛上茶水笑着喊:“喝、喝、喝。”攀谈中我们得知杨狗狗到鸡公寨提亲去了,提亲之事也很新鲜、奇怪:不为别的,只为腹中之子订下儿女亲家。真是未雨绸缪,深谋远虑矣。
回到山下,回望背篼山,我独自怅然叹息,噫,这背篼寨实在险、险、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