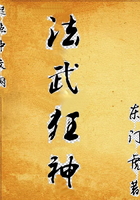冯白口中的升降梯顶盖有个真空层,如同一个气闭的活塞装置。
它现在停了,这意味着我们被卡在了井道的某个部位。
而同样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冯白的举动。
她抱住了我。
动作更是叫我吃惊,冯白开始解开我上衣的扣子,一会儿之后,我就感觉到身上似乎是被冯白的大褂围裹住,然后胸口竟然还贴上了冯白前胸。
我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把自己白大褂内的毛衣给脱掉的,甚至连女性私有的Bra也给扔掉,这会相当于光着上身与我来了亲密接触。
客观地说,从外表来看她已经不年轻,但如果之前没见过她的模样,仅仅是从皮肤的触觉来估计,我怎么也不会把她想象成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光滑紧致的身体倒像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
我的脸开始有些发烫,不过还在可以控制的程度。
只是考虑到我和冯白的年龄差距,尤其我想到贴着我的家伙热衷搞科研,心气立刻凉了一大半。
我不知道她想搞什么鬼,握着拳头的同时身体一直僵直着,我不会揍她,只是准备着随时推开冯白。
“冯医生……你在做什么?”我其实一开始想问的是升降梯为什么停了。
“上升停止了,来不及解释,快!抱紧我,”冯白这么要求道,“把我的外套也裹紧了!”
其实她也不用解释,在我疑惑着照做的时候,我能瞬间感觉到升降梯仿佛变成了一个冰窟窿一般。
身上没有被冯白的大褂覆盖到的部位,从双脚后跟一直延续到后背的颈脖,现在仿佛是被按在极寒的冰块上。
冷!两个字“很冷”!N个字“贼TM冷”!
除了没有被白大褂覆盖的身体部位之外,白大褂内我身体的其它地方竟还有些温温的感觉,尤其是胸口的位置,上半身和冯白紧密完全接触的这一面,温度最高,而且我现在知道了冯白的毛线衣被她裹在了自己的双脚上。
我大概能理解冯白之前这样的举动,她是想取暖,现在也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说得过去。
虽然感受着冰火两重天,不过这样的冷,我在适应了一阵子之后,就不再觉得难以忍受。
比起和蛇昙沟遭遇过的寒流,它还远比不上。
我忽然想起来寒流中,纳兰在当时的举动也是解开衣服贴在我身上,她们取暖的方式起码有些接近。
这让我在一刹那间又恍惚了一次,但冯白就是冯白,她不是任何人。
“果然如此……”冯白的双手摸了摸我的后背,大概是感觉出来我的后背也开始散发体热,这时她再度出声,“抱紧些,我现在需要你的热量,不要管那么多了。”
我听从冯白的要求,将她紧紧抱住。
总感觉我是在做无比羞羞的事情。一种道德上的廉耻感油然而生,我开始在心里默念色即是空,脑袋出神地去想与现在毫不相关的事。
是的,我需要走神!完全抛离远离现在的情况!
想点什么吧……罗丹?罗丹这家伙跑去哪了?罗丹……我很想思考下罗丹的去向,无奈此时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却是罗丹更为火辣的身段,我甚至冲动地想起来罗丹上下身什么也不穿的模样……可能是对象选得糟糕!
那想想陆仪吧……陆仪出现在我脑海中,的确没有像罗丹一样,出现什么不合时宜的模样来,不过形象却很模糊,模糊到我连陆仪的脸都不是很确定,她的模样似乎是来回在半岛时候和金发的娃娃脸之间变幻着。
情况似乎变得更糟,没想到陆仪和冯白的身份关系,反而成了煽风点火的恶鬼。
我可千万不能有任何想法啊……这TM可真是陆仪他妈啊……我觉得自己不能对不起陆仪,做任何违背良心道德的无耻之事。
于是再换了个臆想的对象,他必须是个男的,而且是个只要一想到就能让我变得对女人毫无感触甚至超凡入圣的存在。
古修之并不符合,可以匹配这个条件的人是奥斯西时。
仔细想想,在那条河边是玛琳第一次找到奥斯西时,同时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那张令我厌恶的酒鬼醉态脸。
我讨厌奥斯西时,即便后来这个酒鬼会为了一个女人甘愿做一个普通的猎人,隐居在小镇外的山林里。
也许是因为我看到的片段场景不多,直到后来那个女人死去,她和奥斯西时之间似乎也没给我带来多少感动。
我现在甚至连那个女人的名字也没记住,只记得她称呼那时的纳兰亭为玛琳小姐,而且认识得很早。
能让我记忆一直深刻的人是奥斯西时,他是个很谨慎的酒鬼,但酒鬼只是他众多伪装手段中最低级的那一个。
我现在已经知道,他对包括纳兰亭在内的所有人伪装,差点也把临时出现在纳兰亭身体里的我给骗了。
尝试臆想奥斯西时的结果似乎还不足够,我仍在不断努力让自己的思维离开冯白与我的身体接触。
反应到行动上,我只能让自己的双手离开冯白的后背,用五指撑起冯白的白大褂,以此来避免更多的肢体接触。
“千万别乱想,我只是在借用你身体的热量,”冯白的任何开口都伴随着说话时的口腔热气,这让我感觉更难受,又听她继续说道,“要记住我们是人,有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知道是什么么?”
“……”我没回答,但我知道她的意思。
“是理智,那是把我们从动物界中提炼出来的前提,现在忘掉你身体的原始反应吧,”冯白接着这么说道,“想点别的事,转一下你现在的注意力,否则你将与禽兽无异。”
我觉得冯白大概是感觉到我身体部位的变化,所以才这么提醒我,这就更叫我尴尬了。
她说得对,人只有理智才能叫人,而且我的确需要转移注意力。
随后,我再次在脑海中搜罗有关奥斯西时的记忆。
渐渐在脑海中,清晰地回忆起了第二次回到纳兰亭记忆里的遭遇。
百多年前奥斯西时和纳兰亭待过的那个地下据点,我记得大概是在De国,只是具体位置不明。
而当时的奥斯西时在那个阶段已经在靠针剂来续命,也许是因为纳兰亭对他的身体做过什么,我当时就是这么猜测过,要不然以奥斯西时之前的身体状况他应该活不到我见到他的那个时候。
时间延续到蛇昙沟的现在。
如果说之前见到的奥斯西时才刚刚发生了叛变,那么我在蛇昙沟见过的则是叛变过后的奥斯西时,这其中近百年漫长岁月的过程中,奥斯西时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
他曾经叫骂过纳兰亭是个从上帝那里作弊的怪物,但如今他也已经成了像是怪物一样的存在。
并且在这个古怪驱壳里的奥斯西时,借用他自己的研究来说,他的灵魂颜色一定早已和之前的自己判若两人。
想到这点之后,我忽然意识到也许冯白所说的“恶化”,正是出自奥斯西时的研究理论。
毕竟冯白这么推崇奥斯西时,所谓的“恶化”或许正是灵魂颜色发生了改变。
仔细想想他带来纳兰亭地下实验室捣乱的那些家伙,京剧脸也好,伪装纳兰偷袭纳兰亭的小女孩西格也好,似乎个个都像是打了鸡血一般,极具攻击性。
冯白的研究看起来就像是低配极简版本的奥斯西时的研究,越是那么想,我就越觉得之前自己对这里和纳兰亭的猜测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说纳兰亭是个地下工作者的话,奥斯西时一定是个与其呈现反面的存在,他一定与很多人有联系。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名为“关怀院”充斥着西格玛射线的小牛山,真正关联着的或许是奥斯西时。
我现在有足够多的证据能证明奥斯西时和这里的关系。
比如我从后背的伤痕得到了西格玛射线与分子装的某种可能的关联;又从冯白那里听到了大量关于奥斯西时的理论;还有如同是送“快递”一样把“分子装”“送”给我的京剧脸曾经给过我一个不算显眼的提示。
京剧脸认得我这个身体,也说出了质疑我这样的下等“雇佣兵”能够融合“分子装”这种话。
这说明奥斯西时和雇佣兵的势力即使相互之间没有合作,最不济的关系也是相互知道。
转移注意力的做法很奏效,可能还不如冯白那么冷静,但我基本上已经不躁动。
并且这时的注意力完完全全转移到了奥斯西时上面。
这个过程中,我一直都是睁着眼睛,当眼睛习惯了黑暗的升降梯内部之后,周围的黑暗仿佛是一块幕布,能将那个影子印在我的视野中。
没想过,在我脑海中的奥斯西时竟会变得无比立体。
随之而来的,就是奥斯西时那张令我厌恶的酒鬼脸,它在我的脑海中愈发得清晰起来。
但这很奇怪,他比玄石和朴永慧似乎还能引起我的愤怒来,我努力去想自己的这股愤怒具体是源自哪里,仅仅是奥斯西时那张脸的原因么?这样的说服力很弱。
客观地说奥斯西时并没有对我造成多么致命的伤害,我和这个科学疯子的正面交锋更是几乎没有。
我意识到我对奥斯西时的愤怒源自纳兰亭,而且忽然记起来纳兰亭说过的一句话。
现在的我和她一样可以读取记忆,似乎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可能经历一段纳兰亭的记忆。
可那是怎么做到的呢?我难以理解这样的事,纳兰亭根本没有跟我明确过要怎样才可以做到如此。
条件是什么?
我在努力还原着当时面对纳兰亭的情况,想象着种种导致这种可能的条件。
然后我还发现了更奇怪的事情。
原本让我感受不到光线的升降梯内部,竟会让我感觉四周有微微的红光出现。
很弱的红色微光就在我的周围,可无论我怎么去转动眼球,努力想找到红微光的来源,它总是与我保持着固定的距离——就在视野边缘,但我无法靠近它。
就像是眼角余光,我一直能瞥见有红微光,但无论怎么转,都找不到光源在哪。
正当我没法解释这个现象,想要询问冯白的时候。
红微光像一块“幕布”一样,突然将我整个视野覆盖住。
“空气……”冯白突然出声。
而我像是突然从睡梦中被叫醒一样,浑身一个激灵。
刚刚突然出现在我视野中的红,在这一个瞬间就闪过消失。
我眨眨眼,发现我的四周依旧是一片黑暗,安静得只剩下我和冯白的呼吸声。
可能是出现了幻觉,我这么猜想着。
但是冯白的话并不是幻觉,又听到她继续说道,“越来越少了……”
“什么?”我没怎么听清她的意思。
“我们被拉高了,电梯里的空气变少了,没感觉到么?”
我这才意识到冯白说话时竟会有些喘气。
但我没有感受到空气变少这种变化。
“电梯并不是依靠电力上去,它也许更像是个针筒,我们所在的升降梯是针筒里的活塞,它在外力作用下缓缓上升,这会逐渐把下部的空气抽空,”冯白解释给我听,“除了顶盖,电梯里并不是密闭的,所以空气会越来越少。”
“不需要电力?那我们怎么还停在这里?应该早就上去了吧?”我觉得这挺奇怪。
“电力是用来维持压力系统,我们是靠压力系统上升下降。”冯白回答我。
“干嘛这么费劲?直接把我们拉上去不可以么?”我不解这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办法。
“我说过了,这里面到处都是西格玛射线。”
“这么说,只有这样才不会影响到西格玛射线拟构出来的场景?”我想到这个解释。
“是,不过依然会影响,只是这样的方式能把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冯白接着回答我。
这里的东西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太常规的存在,虽然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我仍然要在心里吐槽一句这特么是个什么鬼地方。
“我们可能到顶了,只不过没人从外部打开的话,还是出不去。”
虽然冯白这句话的后半部依旧宣告了我们暂时出不去,不过前半部倒是能让人振奋。
这算是个好消息。
“那……这里的空气能支撑多久?噢!我们如果不说话,会不会支撑地时间更长些?”我想到眼下的难题不仅仅是温度被降低。
“不,还是说说吧,说话能转移注意力,让我保持清醒,而且你好像又不规矩了,”冯白这么说道。
这话听着叫人尴尬,而且有些强人所难,我并不能完全控制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非常时期这不怪你,我只是开玩笑,”冯白再次开口,用这个对我来说不算是玩笑的玩笑暖场,她问我道,“你觉得人会有灵魂么?”
“会,但它是怎么来的呢?”我回应了冯白,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奥斯西时的观点也认为‘灵魂’是存在的,但它在最开始并不是指‘我们’,‘我们’这些意识,是‘灵魂’由后来的经历记忆所构筑出来的独立意识,所以我们每个人会因此表现出来不同的学识、认知、情绪等等,”冯白又搬出了奥斯西时的理论,这点让我无可奈何,我觉得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去找找奥斯西时的所有著作。
又继续听冯白说道,“他说所有的表象都不一样,区分我们彼此的不是外貌体形的构造,而是内在,这点我很同意他的说法,至于‘灵魂’是从哪里来的,连奥斯西时都没有给出什么答案来,我的猜想也就完全不值得一提。”
“不一定,干嘛他没说,你就觉得自己的不行?”我不太认同冯白仿佛是有些丧气的说法。
奥斯西时在遇上纳兰亭之前,也就是个不得志的老头罢了,那时可能半只脚都已经踏进棺材。
我觉得冯白没必要这么捧高奥斯西时,虽然那个酒鬼老头现在的确不一般,但人与人最大区别不就是内在的想法么?在我看来一切不经过大脑计算考量而对任何一个事物表现出来的遵从都是不明智的。
如果冯白因为奥斯西时没有提到过,就放弃思考的能力,而对权威奥斯西时表现得畏首畏尾的话,她也就显得太过守旧。
对冯白来说,这样的结果只会是让她的研究停滞不前,让她停留在奥斯西时留下的理论框架里。
正如同我臆想过那些“恶化”的病人,可能会是我未来的模样。
那些在冯白到来之前就已经是“常驻”在此地的人,会不会就是冯白未来的结果?
也许那些“常驻”人以前就是像冯白这样的人,然后,他们失忆了。
成为一种只记得本能反应的存在,就像拳击手的职业本能就是挥拳头,程序员的专精就是写代码,而这些白大褂们所擅长的,就是用这里的器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们之前做过的实验。
他们会不知疲倦,因为“灵魂”又或者“意识”已经被替代。
如果有那么一天,那这身体和机器零件的区别还有多少呢?
我忽然就有了这么一种不着边际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