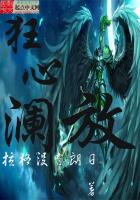救援船最后靠在一起,前后排列开始离开这条水上路线。
一直到找到我为止,几条船救到的人和物资数量都还不少,虽然不是我的功劳,好歹也算是跟我挂钩。
这让我觉得自己总算是起到了一点点正面作用。
由于没有码头,所以不能靠岸,船是去了最近的临靠点。
江风带起的波浪愈演愈烈,我们破浪前行,不过仍旧要在水上待上好一会。
时间会在晚上的七点半左右到达。
而且我们没法再回去蛇昙沟那边的江水段,负责路线的船长告诉我们,从蛇昙沟那段一直延续到上游的坍塌的大坝位置,水陆都不适合过去。
传闻说是有人违规操作,喝醉酒之后进入了控制室。
但现在一切都只是传闻。
喝醉酒?还不如瞎说个借口就说是吃条江里的鱼,然后拉肚子忘了关闸门呢……我从船长的房间出来的时候,船长自己都笑了,他说那个说法太扯了,又是不知道谁在推责任。
我很认同船长的观点。
不过我有另外的想法,我和船长他们了解体验到的情况很不一样。
当然,我说的是纳兰亭所控制的地下实验室。现在由于回不去,对现在位置不明的我也不知道在洪水之后,地下实验室会怎么样了。
那里还在么?我不清不楚地离开了那里,而且在离开的时候还记得纳兰亭说过,那里的自保措施已经启动,奥斯西时包括她自己在内,都会被困在里面。
如果还在的话,只要返回去原先差不多的位置,就能再进去的吧?我心里这么想着,有了想要重回那里的打算。
但目前还没法实施,船长已经告诉过我,现在救援已经收尾,那边不给民船再去,已经成立了专门的队伍去封锁的区域调查坍塌的原因。
大坝坍塌的原因当然不可能是传闻的那样是因为一个醉汉,那只是个胡扯一般的谣言。
但要说这个大坝的坍塌和地下实验室没有一点关系,我宁愿相信那个谣言,然后随便听信一场阴谋论。
至于阴谋谁与谁,我不知道,船上的其他人更不知道。
那个喝醉酒的人也许是个临时工呢?也许是奥斯西时他们的手下呢?仅仅我知道的还有四个势力在维持着地下实验室的运转,所有混进去的人和没有进去却想要对付纳兰亭的人一定不在少数,我这么猜测着。
这都是因为地下室里的东西值得所有人去争夺。
我没法定义它是什么,它又包含了什么,除了纳兰亭,我们所有人都不清楚它的来历。
如同一千个人去看《哈姆雷特》就会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
它会表现出来肮脏不堪、也会有神奇斐然;它如果被正确运用,就能帮助许多人,而被错误引导之后,也会毁灭一切觊觎它的存在。这是我对“它”的理解。
这样一个不明来历的天外来物,最可能的就是被当做一个UFO收藏在最机密的地方,我不明白当初它是怎么被安排在蛇昙沟下面的,一直以来它又是如何在这个并不发达的地方运转着的。
听上去不可思议的同时,还会让人觉得隐隐恐惧,因为感觉安全平静的地方,却是个充满着汹涌澎湃之地。
劫后余生的感觉说来轻松,但是真正体会过的人,很难用语言来明述这其中所获得的东西。
别人我没法去了解知道,但是同样是作为幸存者的我,现在看待问题的角度什么的都已经变得和以前不一样。
我忽然意识到这其中表现得最汹涌澎湃的是人心,来自那个名为奥斯西时的人。
在纳兰亭的那趟记忆之旅中,我还没有看到最后,对他们之间最后反目的结果并不清楚。
但那个对纳兰亭敬畏的奥斯西时已经被自己的私欲染黑,他看起来只想要独自霸占秘密。
他也许早就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想要把它公诸于世,让所有人都知道纳兰亭的秘密,那种打算百分百已经忘在了九霄云外。
雨已经停下,天色不明不暗,距离到达还有两个小时,或许会更短。
有船员给了我一瓶啤酒,他们和被救上来的那些人,停留在甲板上。
甲板上的大家能从洪水中获救,都是心存感激,仿佛人生都被刷新了一般。
平时不喝酒的开始喝酒,平时不抽烟的人也在问船员要烟来抽。
后来大家基本上也没什么事,有的人就帮着船员去分发食物,最后结束之后,船员和我们这些被救援上来的人一起坐到一起吹牛。
包括船长在内的所有船员,也包括所有被救上来的人在内,他们特别感谢了罗丹自己掏钱救人的举动。
所以这一路上,整条船的人都在拿罗丹当天使一样,罗丹在收获了满满的夸赞之后,心理早已经飘到天上。
船员和一些被救上来的男人开始起哄,他们都是以为罗丹这么费劲雇佣船只来找到我,我们的关系一定到了那种地步。
有个船员说劫后余生回来,对爱人一定要亲上一口。
所以他们要让我去亲一口罗丹,对这个说法我当然不信。
立刻就说明了我们是普通朋友。事实正是如此,如果不是“古修之”的缘故,我们不会一起来蛇昙沟。
起哄声中,罗丹立刻退出了我们的吹牛聊天中,似乎是躲回去房间,我没有兴趣去过问。
有人说罗丹是害羞,有人说她是生气,要让我追上去,我摇摇头拒绝了,再一次重申我和罗丹的关系,依旧没人相信。
不过这个时候,对我来说,罗丹并不重要。
我所在意的是在罗丹离开前听到的传闻,或者说故事。
出自一个船员。
从那个船员的口中得知,我们将要去的那是个古老的码头,也许在明清之前就开始存在了,年代说上去可能都有几百年。
据说还有许多诡异的传闻,听上去像是民间流传的鬼怪故事一样。
不过在大家靠在一起,聚成一团的时候。
鬼故事也能当成津津有味的趣闻来听,也没人会去较真船员话里的各种。
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会这么较真。
我并不是先被鬼故事吸引,而是先听到那个码头的所在地之后,才开始关注他的故事。
那个码头在阳顶山。
我对这个地名很有印象,当船员提到这个地名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些片段画面。
我意识到这个名字引发了我的记忆连锁。
那些,都是我之前的记忆。
尽管现在已经模糊,但是仍旧能分辨出来,和这个地名相关的记忆是关于“古修之”的。
我想起来他有个妹妹,名字叫古小柔。
而他们出生在阳顶山,我意识到我马上要去的地方,是古修之的故乡。
船员的故事,不考虑我刚刚想到的因素,那就是个鬼故事。
我把内容归纳了一下,基本上如此:
阳顶山有座山峰,很漂亮,原来是附近几个景区当中知名度最高大的地方。
但是经常有人会在那座山峰失踪,并不只是游客,就连本地的许多人也会在那一片迷路,出不来的人也大有人在。
一开始,失踪人数不多的时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上山的人总会面临各种风险。
而且报导出来的人都是在独自的小团体里,人数多在四五人,也有十几人的大团体,这些团体的共同特征就是走的都不是开发好的步道,他们都以自游探险为目的,在山里自由活动。
可后来就传出来有人在山里失踪的消息,搜救队伍半个多月都没有找到,而且并没有家属之类的人来景区附近滋事哭闹,所以大家都以为那只是谣言,或者是竞争对手的抹黑,又或者里面有什么秘密之类的,最后反而以谣言为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者”。
但在那之后,失踪的人数就成跳跃式上升,最多的一次,失踪了二十几个。
那次的队伍带足了设备,做好了一切与外界联络消息的准备。
他们的探险开始很顺利,只遇上了一些山险,后来有了一些意外的发现。
从他们传出来的影像画面来看,他们遇到的是一堆被绑在枯木上的尸体,尸体已经腐烂成为骨头,但是脑袋还保持着完好的模样。
像是用人的尸体做成的“稻草人”一般的存在,只不过画面传播得并不广,也没人提醒他们,那其实是种警告。
带着娱乐精神的队伍,有小部分人在那个时候选择了退出,那段人头稻草人的影像画面也是那几个人带出来的。
但大部分人仍然选择了前进,他们后来的遭遇没人再知道。
只是后来官方派出了更多专门的搜救队伍,但只在在山里的小溪里发现了那群人被砸烂的设备,那里连尸体也没有留下。
而后来大家再去看那几个人带出来的画面,并没有发现画面中他们描述到的人头稻草人,不仅如此警方还发现了那几个人藏着一部分带血的衣物,所以他们被当成嫌疑犯被逮捕,尽管他们声称看到了人头稻草人,但是没人相信他们。
再后来,他们死在了监狱里,时间距离他们入狱仅仅一个月都不到。
船员说到这里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还以为这是一个蓄谋杀人而被侦破的刑事案件。
不过船员接下来的话,就刷新了我们刚刚对此的观点。
死在监狱中的那几个人,只剩下脑袋还在,模样和他们自己描述的人头稻草人类似。
在死的前一天毫无征兆,但是在当晚大喊大叫,像是疯了一样。
叫声持续了半分钟左右,被大家发现的时候,就成了那副模样,正常来说一个人如果自杀,是不可能做到如此的地步。
唯有他杀才有可能出现肢解那样的情况,而匪夷所思的是,关在同一个监狱房间内的其他人都说没有目睹到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监控能调用,成为了一个谜团。
这是从监狱中传出来的传闻。
与此同时,继续前往那里面的人,开始有人声称真的从出事的溪水附近见到了那几个人描述过的人头稻草人,不过么有证据,那样说的人在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大病了一场。
至此之后,只要进入那片区域的人,出来之后都会染上一种怪病,送去医院也医治不了。
但是神奇的是有人找过神婆之后,反而能治好那种病,不过也有人找过之后,并没有被治好。
这并不靠谱。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传闻失踪在里面的人,在一个雨天全部出现在当地附近的村子,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像是一大群恶鬼一样,就站在村里,到处都是。
弄得那附近的村子的人几乎都疯了,没疯的被迫逃离自己的村子,直到现在,附近的几个村子还是一片荒野。
没人愿意过去与那些恶鬼为伍作伴,住在比那几个附近村子稍微远些的人,也开始搬家离开。
逐渐,在那片区域附近没有一个人再愿意去居住,那里成为了彻底的无人地。
现在阳顶山的旅游业几乎被废止,就因为那个区域的存在。
虽然在附近竖立了牌子,声称只要不靠近那里,就不会有事发生,但已经没多少人愿意再来这里。
现今,所有人已经快把阳顶山遗忘,而为了淡化这个诡异的恐慌,它是唯一一个从景区地图上被抹去的景点。
人们只知道阳顶山总是在失踪人,但却已经没人知道那座山才是阳顶山。
未知并不一定能换来好奇心,恐惧是与此相伴的。
而惊悚的故事,就是需要荒诞,越是匪夷所思就越能让听的人感到害怕。
那个船员的话,说到这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有丝丝的不寒而栗。
不过我很好奇,他是怎么知道的,还能这么清楚。
如果不是从哪里的记录看来的,那就只能说他很会讲惊悚故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从哪看来的,不是说那里已经没人了么?”我问他。
“嗨!传闻呗!”“谁在意这个,就是!”“这种鬼故事,我也听过,来!来!我来讲一个!”
人群中有几个人相互这么说着,他们对船员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我总觉得怪怪的,也是在这个时候,我重新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个船员的眉目。
他脱下了船员帽,整理了下头发之后,又擦了擦脸上的灰。
我觉得他有些眼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