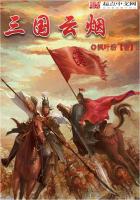面对陈杉的义愤填膺,方译桓表现得出奇平静,似乎根本就没在听她讲话,也无意争执。直到看见他在就诊人那一栏填上自己的名字,陈杉的惊讶溢于言表。
他预交了需要的所有材料和费用,又逼着自己去做了各项检查,符合条件,签下了协议,得知脑定向手术将在半年后进行,他就回了国。
国内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的,都是国际黑势力实际掌权人在英国被击毙的消息。曾在中英两国之间流窜,省公安厅历时两年半也未能全部剿灭的特大犯罪集团,终以方良时的死亡而戳上了结案的章子。
自然有杂志为了销量,刀口舔血,查到了方良时和方译桓的胞弟关系。一石激起千层浪,记者们闻风而动,纷纷预约围堵致电。秘书何子格不堪其烦,请示老总之后,一纸文件签下去,市价百万的出版集团以三分之二的价格被收购,旗下三大热销杂志停刊封印。
有人说,这才是方译桓的真正手腕。
一个横跨中英两国,固定资产以百亿计的集团,若真如纸牌屋般风吹就倒,又何以在电商界称霸七年?
而那个掌舵人,又怎可真为软柿子,任人拿捏?
桓宇国际才没有传言那么容易倒,方译桓也没有传言那样软弱。
荒原野狼披上羊皮,改变自己,只因爱上了天敌。但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狼就是狼,披着羊皮的狼,依然是狼。
桓宇国际又恢复了往日的兴盛,方译桓又重新登上财富榜单。一切宛如从前,好如那些过往从未发生过。
不同的是,他不再用任何美女做幌子,不再夜夜笙歌,不再频繁出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名流会所。除了这半年,每晚重复的梦境,一个红衣女子站在玻璃门前,礼貌浅笑:“方总您好,又见面了。”
那一声方总您好,循环往复,来来回回,像旧时候的留声机,带着时光的印记,嘈杂着、旋转着。
多少次的午夜惊醒,身边空无一人,只有桌上的始终嘀嗒嘀嗒。
最初对手术那强硬的抗拒,已被这排山倒海的思念压得一丝不剩。这么多年来,从未真正被什么战胜过,任何时候都是他所向披靡,凯旋而归,何曾有过服输时候。这一次,他是真的投降了。
起身去喝水,意识朦胧间打碎了桌上的情侣杯。她的所有东西都在,他没有收,也不敢收,好像只要她的气息和陈设在,她就在似的。其实比谁都清楚,这是蕉鹿自欺,可那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没有这残存的希望,他的生活又有什么劲头?
去厨房拿扫帚,打算将这满地的玻璃碴扫掉。却在冰箱上,看见了自己曾给她写得便条:好好吃饭。
睹物思人,愈发难过。
伸手,将那张纸揭了下来,打算扔进垃圾桶。却突然想起了什么来。
沈向晚的死……一切都像是有所准备。
她是胸腔中弹身亡,心脏不可能没有受到一点的创伤。可那心脏,不但完整完好,还能在离体长达七小时依然健康活跃,这不太合理。况且沈向晚是东方人中少见的熊猫血,而他是普通的A型血。她的心脏与他并没有配型,就能这样匹配,连排异反应都没有。
她将身后事料理得仅仅有条,甚至把研究所的地址和电话都誊写下来给他,那誊写的字迹,整洁有力,没有一丝颤抖。说明她早有准备,是料到了自己早晚会死。
律师表达了歉疚,说明是在冬冬去世之后。而冬冬去世到她的去世,仅仅隔了半个月的时间。
她在给裴佩的信中说,曾以为自己会死,最终并没有死。她说,不到最后,永远不要放弃。
不到最后,永远不要放弃。
他握着那张便条,手在抖,整个人都僵硬了。那是在荆棘中赤脚狂奔太久的人,为鲜血淋漓的双脚穿上了梦寐以求的鞋子,即使荆棘林永无尽头,他也能一步一步走出去。好像找不到家的孩子,刺骨夜风中谁为之点起了一盏灯。
空旷而寒冷的胸腔仿佛一团火在熊熊燃烧,灼热而明亮,将那些淤积的黑暗和痛苦都驱散。他忘记了时间,站在冰箱前,像一个傻子。窗外的天际不知何时起了鱼肚白,星辰一颗一颗熄灭了光,雾气缓缓蒸腾,只剩下了朝日和晨曦。
站太久,呼吸有些不畅。揉了揉肩颈,喝了口水,不及洗脸刷牙,立刻给律师打去了电话。
“按照当事人的意愿,我已尽到了我的职责。对于你的问题,鉴于保密协议,我无法回答你。方总,真是抱歉。希望你理解。”
律师没有否认。
但将沈向晚称为当事人,而不是逝者。用词婉转,却意思到位。
他再次飞往伦敦,以亲属的身份要求调阅方良时的档案,遭到了伦敦有关部门的拒绝,理由是涉及国家机密。几番艰难求证,找了所有能找的人,终于寻到了苏格兰场处理那起案件相关人员的法医。是位三十岁出头的白人女性,带着他在黢黑的地下室里穿行,两边成排生了锈的铁柜,挂锁的门上张贴着嫌疑人的基本信息。
在尽头的柜前,她停住了脚步,告诉他,这就是他要找的骨灰和档案了。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锈迹斑驳的柜子,里面是一片黑暗。
手机的背灯照进去,是绿色的铁板,上面空空如也。
没有骨灰盒,也没有任何档案。
法医也愣了,转身去打电话,核实之后告诉他,已经被内政部调走,看不了了。他不死心,再次询问当天的情况。大概是案件影响太巨大,法医还记得一些,却十分确定地告诉他,死了,都死了,罪犯和人质都死了。
他那本已燃起的零星希望,顷刻消散。
晚上还有欧洲区总经理组的局,在场的都是当地的政商要员,不能不去。何况这位美丽的梁经理已约了多次,他已拒绝多次,这次不能再拒绝。酒是好酒,菜亦可口,旁边的梁经理也是细心妥帖。酒过三巡,他终于问起消失档案有可能的去向,与商业无关,与当晚的主题无关。
但他不能放弃一点可能。
好在那位老公职于苏格兰场的财务部秘书答应会帮忙询问,虽然结果不可知,但已经让他感激涕零。为这一句不算承诺的承诺,他已经喝了三杯西拉子。
其实他不能喝酒的,但心酸上溢,他根本顾不得。梁经理看出了他脸色不对,找了个借口就要送他。他不是不明白梁莹的心意,当年她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表露,他这才以高升为由将其调往欧洲区。
车内并不凉快,酒精的作用也让他有些烦闷,手倚在车窗上吹风,听到旁边的她声音温柔:“身边这么多优秀女性,就没一个入眼的么?两年了,你怎么还单身呢?”
他脸泛红晕,笑了笑:“你不也是?”
“那刚好。你要不嫌弃我的话,咱俩试试?”
她笑得醉意朦胧,心里却清醒得很,还不就是借酒装疯。即使被拒绝也不觉得难堪。
他瞧了梁莹一眼,笑意更深,“不试了。可不能把鲜花糟蹋了。”
“我知道了,你就是看不上我。”梁莹一脸幽怨,如娇似嗔,半真半假,“你倒是说说,我哪里不好了?”
他歪头想了想,“挺好的。”
“敷衍。”
他是个喜怒不轻易形于色的人,但今天不太一样,梁莹都看出了他的心不在焉,简直一语中的,“难道流言是真的?你和那个去世的离婚律师确实不一般?你问的档案的事情,和她有关对不对?”
他一脸好笑地瞧着梁莹,“梁经理,我可是你顶头上司。再八卦,以后让你天天穿小鞋。”
“反正我在欧洲,山高皇帝远,你管的着么。”她终于不再嬉笑,“你与其在伦敦警察厅上下文章,倒不如直接去找遗嘱见证律师。但别抱太大希望,毕竟已经宣告死亡了,不太存在活着的可能性了。”
他面上微笑浅浅,没有答话。
一下车,他却立刻换了脸色。
一直拼命压下的愤懑和失望,瞬间涌上头顶,他连夜驱车前往了曼彻斯特。三个小时的车程,他开的飞快,不出两个小时就已到达。他像土匪一般,用力敲着门,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突兀,左邻右舍都探出了头,那表情像看一个疯子。
好半天律师才开了门,穿着睡袍,头发还滴着水,看见他,面上惊讶一闪而过,正要说什么,却被方译桓一把攥住了睡袍的领子。他本就比那律师高一个头,身形也比律师魁梧一些,这样用力,仿佛一把就能将律师拎起来,额上青筋暴起,“告诉我,她到底在哪里?”
律师自然知道他所说的那个她是谁,却只能装傻,“谁?”
“谁?你知道她还活着的!”他语无伦次,不想再听律师打得马虎眼,眼眶鲜红,神色凶恶而可怕,“怎样才能告诉我?要钱?要多少钱?还是要什么?!”
律师被他逼得连连后退,却仍旧嘴硬:“我已经告诉你了,沈小姐已经不在了。所有的遗物已经照其生前意愿分配了,你再逼我没有用!”
这不是他想要的消息!所有的心酸绝望都涌了上来,带着粉碎一切的怒意,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张律师,别忘了你的女儿还在国内!晋城明治双语国际小学是么?今年要升初中了是么?你是希望她平安顺利地毕业呢,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