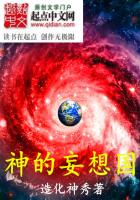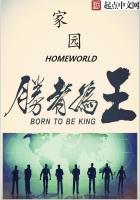……
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当年恬静没死,他们不能在一起。现在恬静死了,他们依然不能在一起。这一辈子,天上地下,他们都没办法团圆,都没办法相聚,都没办法像普通的情侣那样,平平静静地说话打闹,结婚过日子,从孩子的上学,到步履蹒跚回忆往昔时光。
可老天又是那么的公平,在他最绝望的时候,给了他一颗心。
即使,他多么想要她能活下来。如果非要在彼此的生命里二选一,他多么想她留下。
……
思绪回转是个缓慢的过程,他摩挲着笔记本封面的真皮,终于抬起头来,气声浓重:“她是在哪里发现这个本子的?只有这个本子吗?”
“你若不问,这个本不打算给你的。”律师转身,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透明的文件袋,放在桌上。
方译桓打开白色的卡扣,将里面的材料,一张一张拿出来看。
这文件袋里放着的,是沈向晚在他的保险箱里发现的那些材料。
江映荷的护照。
江莲青的整容手术方案手册。
他和江映荷的结婚证。却猜的一点没错。
也终于能明白,沈向晚不顾一
还有佑峰国际的资产评估书。
望着手里编造得几乎是天衣无缝的“证据”,他闭上了眼睛。
那些离间的东西,他没见过,切要置他于死地的原因了。
从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方良时不知不觉闯进了他家,在保险柜里放下这些东西,就是要让她误会,就是要他万劫不复。
他做到了。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恐怕冬冬不会死,恐怕沈向晚也不会死。
但最坏的可能已经发生,再无法挽回。
那笔记本中,还夹了几张纸。
是保罗丁伯根研究所已经研发成熟的脑立体定向手术与药物结合的接触精神依赖治疗的介绍,第一页上,是沈向晚亲手誊抄的地址和电话。
这是她希望的吗?
将一切都忘了?
裴佩夫妇不知何时离开的,空旷的病房里只有两个人对坐着。他怔忪间,律师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有些模糊,他费劲了才听明白:“这是沈小姐的意思。感情毕竟不能说放就放,如果太痛苦,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她也希望你忘掉他,重新开始。”
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雨。西风周年吹着,北大西洋暖流作用下的大不列颠群岛,气候总是湿润,春天的阴雨更是不曾停歇。
“手术的风险很高,在院死亡率为10%左右。除排异反应外,术后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并发症。即使动了手术,也不一定能保证永久,平均生存期只有十年。”李翔宇将全英文的文书递给他,“这是手术知情同意书,确认无误签字后,立刻进行手术。”
他将签好的同意书递上去,“我有心理准备。”
能活下去就好。沈向晚也是希望他活下去的。
他被推进手术室,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旁边放着的电话机般大小的无菌腔室,里面一颗鲜红的器官有规律地跳动着,那是从捐献者体内摘除的心脏。为了减少缺血而引发的变质,这枚心脏已经使用常温氧合血灌注保存了七个小时,电子屏上的各项指标显示着一切正常。
此时,距离沈向晚的宣告死亡也已经过去了七个小时。
两台无影灯照下来,将他所有的清醒都阻绝在了复合麻醉之下,气管插管连接着他的鼻腔,除此之外,身上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管子连接着不同的仪器,人工心肺机的透明痒合室内,鲜红的血液缓慢地流动着。
5位医生来来去去,护士不住地给主刀大夫擦汗。
漫长的14个小时之后,手术室外的红灯终于熄灭,他被推出手术室。
在外等着的四个人听见声响,立刻站了起来:“怎么样?”
李翔宇顿了顿。这一顿却让本就胆小的尹谨媛瞪大了眼睛,她紧紧捏着苏浚的手,生怕医生说出什么不利的消息来。而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苏浚也是紧张得满手汗,却不肯再问。
“手术过程很顺利,但心脏跳动的节奏并不平稳,随时都有二次危险。所以会继续观察,这段时间依然要依靠人工心肺机来维持呼吸。”
裴佩问:“这段时间,是指多久?”
“不好说。短则十几个小时,长的话,有可能是一两个月,也有可能是一两年。许多并发症都发生在术后早期,主要有供心衰竭、大出血、感染和排异反应等。但也不用太担心,译桓的情况相对良好。”
麻醉剂在第二天的凌晨失去了作用,疼痛开始翻江倒海,他盯着天花板,却一声不吭。
护士瞧着他满额头的汗:“方先生,给您来一支安定。睡过去就好了。”
他说:“让我清醒一下。”
极端的痛楚是极端的折磨,在这如上刑一般的感官刺激下,他的大脑竟然还能冷静而正常的运转。
沈向晚把心脏给了他,他不能轻生,不能怨恨,不能一蹶不振。
他只能好好活着。
为了她,好好地活着。
三周后,在苏浚的陪同下,出了院。
沈向晚的坟前已长了新草。昨日的大雨让公墓的路并不好走,柏油硬化了的小径上满是冲刷而起的泥,一层一层,有些斑驳。绿叶刷刷响,倒让他的脚步声不那么孤单。他帮她除了草,在那冰凉的石阶上坐了一会儿。山风带着水汽,湿润润地吹在脸上,让脸颊也有些湿润。
照片栩栩如生,他看着那清晰如昨的笑容,跟她说着话。
他说,以前总责怪你不懂爱,怪你将用最恶毒的心意揣测我,怪你弄丢了冬冬,但现在,想责怪你,你都不给我机会。
他说,冬冬的死,我知道你也很内疚,你也很难过,但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么惨烈的方式来道歉?我不想接受,我只要你活着……
他说,你的人已经不在我身边了,可不可以让记忆陪着我?我真的不想忘记你。总有老了病了死了的那天,那时候再忘记你好不好?关于你的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不想连那一点点残存的记忆都被剥去……
没有人会回答他,只有零星的雨滴,一点一点,宛如梦境。
他说,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会尽力。
保罗丁伯根研究所历经搬迁,沈向晚留下的电话和地址都不正确。联系了陈杉,才找到了地方。陈杉站在街角,一眼就认出了他,以为他是来调查沈向晚的过往的,甚至想好了该用怎样的文法才能让他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