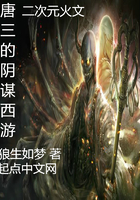“沈夕歌!你怎么这么傻?你不许闭上眼睛,你睁开,看着我!”他颤抖着双手捧起她的脸,“不能睡,沈夕歌你坚持住,不许睡!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沈夕歌只觉得意识飘忽,身体上的疼痛她似已感觉不到,只觉得累极,生命似乎在随着潺潺的血在一点一点流失。
“你看着我,沈夕歌。你坚持住,我一定会带你回去,你知道吗!”舒奕寒心疼得说着。
沈夕歌缓缓的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张了张口,发现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得扬起嘴角,露出一抹近乎于解脱的笑意,然后世界一片眩晕,她缓缓的依在他的肩头,眼里的世界一点点沉入黑暗,最后归于死寂。
也许,就此结束一切,也好。
你爱我也好,我恨你也罢,所有爱恨都勿需言说,只这一瞬间便能证明一切。
狂风呼啸,暴雨猛烈,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太过渺小脆弱,而舒奕寒死死的用身体为她遮出一寸安全之地。
干净明亮的病房里,脸色苍白的沈夕歌躺在病床上,眉头紧紧皱着。
“冷……冷……”她的声音虚弱无力,瘦弱的身子瑟缩着,旁边有机器不断的滴哒着。
身旁围了一圈穿隔离衣的医生和护士,正在进行紧张有序的手术。
而隔壁的病房,舒奕寒同样苍白着脸躺着,人事不醒。
转眼已是八月半,南方的秋虽然总是来得很晚,但已不似盛暑时的酷热了,大地渐有萧疏之意。
沈夕歌坐在轮椅上,眯着眼看着窗外一片落叶随风打着卷儿落下来,禁不住拢了拢身上的线衫,周身一片寒意。
虽然已是一个月后,但她似乎还没有走出那个可怕的阴影,天稍一冷就发抖,天一黑就做噩梦,尤其害怕下雨天,仿佛永远也无法从那个恐怖的梦里走出来。
出事当天,纪博发现联系不上舒奕寒时,当即便报了警,搜救的船只很快发现了沉没的游艇,当即知道他们遇了难,纪博动用EX的特殊关系利用最短的时间找到了那个荒岛,并在那晚的暴风雨结束前找到了舒奕寒他们。
经诊断,沈夕歌两根肋骨断裂,其中一根还插进了肺里,若是再往里深一厘米,也许她就不能活着离开那个岛了。
直到现在,沈夕歌都不知道自己当时哪里来那么大的勇气,用自己的身子替她挡住了那根树干,那瞬间崩发出来的能量,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
她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没有阻止舒奕寒上那条游艇已经令她心生悔意,也许只是不想让自己再后悔吧。
是的,后悔,她最怕的事情就是后悔,而现在却悔不当初,就在半个小时前,纪博来找了她,跟她说了一些事情的真相。
“太太,有件事情我必须向您报告一下,您父亲死前看到的那封信不是老板寄给他的。出事的当天晚上,老板便让我着手调查这件事情,可是事情刚刚有些眉目,老板和你便出事了,一直拖到现在……”
一瞬间,沈夕歌的血液仿佛凝固,身体猛的一颤,如置身于冰窑一般,背上的伤也隐隐作痛。”
不是他?自己认定的事实被突然推翻,这怎么可能。
“那寄信的人是谁?”
“寄信的人是陆少杰,他企图利用您父亲破坏你和老板的关系……”
陆少杰……
好一个陆少杰……
一边诱导利用自己去陷害舒奕寒,一边又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心口上仿佛有一把刀子正钝钝的凌迟着她,虽然心痛,她却感觉轻松,那条束缚在她心上的线没有了,曾几何时,这条线无时不刻不在折磨着她,一点点勒紧,入肉三分。
而现在,她终于可以不顾一切的去后悔自己曾对舒奕寒做过的事,终于可以敞开心扉去触碰那颗滚烫的心,终于可以勇敢的去接受那份超越了生死的爱。
肩上蓦地一片温热,沈夕歌回头,是方语泽。
“天冷了,多穿些衣服。”方语泽为她披上了一件外套,声音都温柔如旧,只是成熟了许多,不再是那个眼睛里时刻闪烁着光芒的年轻少年了,他也学会了敛锋藏锐。
“嗯。”沈夕歌轻轻点了点头。
“我推你出去晒晒太阳?”午后的太阳看起来很温暖的样子。
“好。”沈夕歌扬了扬嘴角,一只手习惯性的覆上了小腹,那里有一个小生命正在孕育着,一天一天的成长着。
死亡,带给人类的是绝望,而新生,所带来的就是希望。这希望如种子一般,种在人心里。
沈夕歌醒来后医生告诉她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她已经有一个月零五天的身孕,当时,她便喜极而泣。
幸好,这个小生命坚强的扛过了那场暴风雨,这算暴风雨后的彩虹吗?
阳光下,沈夕歌靠在轮椅上,金色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感觉,令她贪恋。
“转眼要秋天了。”看着旁边几棵开得正盛的桂花树,微扬着下巴,嗅着空气中淡淡的桂花香。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方语泽将她推到桂花树下,自己坐在了树下的长椅上。
“不快,我觉得像是经历了一个轮回。”暴风雨总是能让人成长,脱胎换骨似的成长。
“傻丫头,怎么还是这么傻。”方语泽禁不住抚了抚她柔顺的长发。
沈夕歌看着他傻傻的笑。
“语泽,你还爱我吗?”她突然仰着脸问他。
“爱。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语泽的眼睛温柔如月光一般,“可是爱也可以分很多种,每个人都自己爱人的方式,也许我的爱是伟大的吧,只要你能幸福,让我放弃一切都可以,哪怕是放弃你。”
沈夕歌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眼睛里闪烁着比阳光还灿烂的东西:“我想,我知道什么叫爱了。”
特护病房里,舒奕寒躺在病床上,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白。
坐在病床前,沈夕歌看着这个病床上躺着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