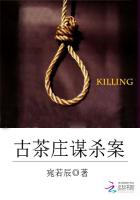锁儿爷的鬼故事,之八、白老太太
引子
光绪二十六年发大水的事儿,咱们在老庚的故事《笤帚疙瘩是千年精灵,借助法力二婶劝女鬼》的章节中说过,那场大水过后温疫流行,有的村庄十室九空,尸横遍野,人们没有粮食吃,怎么办?便从大水过后的淤泥里挖掘已腐烂变质的死猪、死羊、死狗充饥,温疫像风一样的传播开来。
人们浮肿无力、腹涨赤目、鼻涕过河,腹泄如水,谁来解救灾民?靠官府吗?皇上拨的那点赈灾款还不够官僚们层层盘剥,到了百姓手里还不够一碗清可鉴人的浠粥,何况,慈喜太后正忙着全力对付义和团,哪儿有精力管百姓的死活,这时镇上却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新鲜事儿。
第1节、避洪水迁居高阜,救灾民赈粥舍药
提起高阜镇的白家,周围数十里的百姓都知道,可又都不知道,有人说:“锁儿爷您这说法不是自相矛盾么?什么叫都知道,又都不知道哇”?锁儿爷笑咪咪的抽了一口烟,摆出一副说书人的样子,不紧不慢的说:“莫急,听我慢慢道来”,说罢将那铜烟袋锅往桌角一磕,“啪“的一响。
话说,高阜镇十字街儿,把角儿的第一家儿,虽不说是高楼大厦,却也是一水的青砖瓦房,让明眼人一看,就知是个大户人家儿,若大的四合院有数十间房的家业,原来却只有一个老苍头和一个小伙计在此居住,临街五间大瓦房,除一间是院落的出入门户,其余四间便是高阜镇唯一的一家儿药铺“续命堂”,有人说,这药铺字号太大,太狂,可着天下找,还没有哪一家儿药铺敢如此称呼。
东家便是白老太太,堂号之大,必有非凡的能耐,也确实如此,当年,曲阳汉白玉采石场,一个小伙儿不慎将腰椎砸碎了两节儿,看了多少正骨名医,走了多少名城、大川,都无人能治,眼看这人就废了,后来有人说高阜镇有个续命堂你不防去试试,死马儿权当活马儿医吧,家人赶着大车便将小伙儿拉来。
白老太太没让他下车,在车上就为他拿捏了一番,然后给开了三付药,安顿他们住下,三付药吃完,白老太太用手一拉那小伙儿,小伙儿“哎哟”了一声,竟坐了起来,并下地走了两趟,还真是好了,续命堂的字号还真不是瞎吹的。
白老太太在这儿有药铺,有宅子,但从不在此留宿,每天来去有辆轿车接送,但白老太太住哪儿?没人说的清,农历七月十三,天阴的水盆似的,老苍头与小伙计匆匆将药铺下了板,说是得赶快归置一下房间、院子,东家要搬过来住。
申时左右,白老太太搬家的大车到了,“喝哦,有十三辆大车之多,可细看,只有一辆大车上装的是应用物件、细软之类,其余十二辆大车装的都是金黄色的秸秆,看热闹的街坊邻居都觉得奇怪,搬家要这么多秸秆干什么”?但谁也不好多问。
当天夜里,白家整整折腾了一个通宵,到第二天清晨,白家的房舍焕然一新,原来的青砖瓦房不见了,影入人们眼帘是比那青砖瓦房还高上二尺的秸秆房,连续命堂都是金黄色的秸秆房,门窗是秸秆的,地面是秸秆的,墙壁是秸秆的,房顶是秸秆的,就连药铺的药阁子都是秸秆的,街坊邻居无不咋舌:“难怪拉了十二车秸秆”,可就是没人想,一所宅院,这么大工程,一晚上连拆带建怎么能够完的了工?这事怪吧?
还有更怪的呐,七月十五开始下雨,雨是越下越大,如瓢泼,如银河倒泄,街上的水有二尺多深,家家儿屋里、院里都进了水,白家却安然无恙,怎么回事儿呢?听说过水涨船高么?,人家的宅院像船一样,随着水浮了起来,看过白蛇传吧,就像那法海寺,水涨庙长,白家的秸秆房就是下再大的雨也没事儿。
刚才说的这些邪惑事儿,大家或多或少的都听说过,那不知道的是什么呢?锁儿爷问,你们谁能知道白家从哪儿搬来的?谁能知道白家的身世背景?谁能知道白家以前是从事的什么行档?就连白家的家小人口都没人说的清,所以说,大家又都知道,又都不知道。
大雨一下就是二十多天,西大洋终于崩了堤坝,排山倒海的洪浪滚滚而下,冲垮了千百村庄、万亩良田,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高阜镇地势虽然较高,也有不少民房被冲毁,按说白家的秸秆房能随水漂浮,应被洪水冲走,可偏偏人家的房子像生了根一样,连晃动都不晃动。
过去有句老话儿说,饱暖生闲事,饥寒起盗心,这大灾之年,正是庚子年,人心不稳,北方旱的旱,涝的涝,人们流离失所,这一年终于暴发了义和拳运动,拳坛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北方各省都动荡不宁,急的慈喜老佛爷四处调兵遣将,力图剿灭“拳匪”,没想到,“拳匪”是越剿越多,你看大清朝整个儿都乱了套了吧?但咱们家乡这一片还算稳定,为什么?一是京畿要冲,二是大水过后,高阜镇白家在镇上十字街口设置了粥棚、义诊,十字街儿四条路口的把角儿,各支起五口赈粥大锅,难民们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可以随来随吃,药铺前,又一张八仙桌,白老太太便在此坐堂义诊、舍药,方圆数十里的难民都拥向了高阜镇。
一个多月的舍粥、义诊,就是家财万贯,家有金山银山,也得有用尽之日啊,邻居几家帮工的人都觉得奇怪,“白家院舍再大,也存不下这许多粮食、草药啊”,免不了有人偷看白家的行经,清晨只见白老太太端着半盆米,往二十口大锅里各舀了一小勺米便算完事儿,那帮工心想,“那么大的锅放一小勺米,就算熬米汤也不行啊”,没想到赈粥时,掀开锅盖儿一看,却是满满的二十大锅稠粥哇,“怪了,这白老太太真是有点邪门儿”。
那药阁子的抽屉也是,白老太太在前边号脉,开方儿,老苍头和伙计在后边给抓药,只见往外抓药,就没见有人往药阁子里续过药,老抓老有,你说邪门儿不邪门儿,白老太太一天至少也看二百几十号人呐,那药抽屉的药怎能老有啊。
有人说了,来看病的不可能都是一种病啊,怎会老从几个抽屉里抓药?锁儿爷说,这你就说错了,大水过后温疫的传播,大体上就是那几种症状,浮肿无力,腹涨赤目,腹泄不止,鼻子风发等,所用之药无非就是提神利水,消炎止痛,把干止泄,健脾生津之类的药物,像什么甘草,麦冬,胖大海,杜仲,桔梗,山渣干等,当然还用了什么药只有白老太太自己知道,反正病人吃了她的药,逐渐就好了。
有人问:“什么叫鼻子风发?这是什么病啊”?锁儿爷哈哈一笑,“这是咱们当地的方言,就是感冒流鼻涕,用现在的话儿说,就是病毒性感冒,农村老人们还是这么说”,说着锁儿爷便学上了农村的土话:“你咋啊咧?鼻子风发咧,吃药哩呗?吃咧,哪一下揍好喽昂”,锁儿爷学的是男女对话,那是唯妙唯肖,逗的大家哈哈一乐。
闲话少说,我们还是接着说白老太太赈粥、舍药的事儿吧,一天粥棚来了四个外乡人,这四个外乡人长的很是特别,有人问,怎么特别法儿?首先是看不出这四人的年龄,说他们像四五十岁?像,说有六七十岁也可以,总之说不准他们的实际年龄段,再就长相怪异,三个尖嘴猴儿腮,一个倒三角儿脸,三个瘦高条儿,一个矮胖子,他们排队在粥棚喝完粥,又到白老太太的义诊摊来看病。
白老太太一上午,手就没实过闲儿,挨着号儿叫,逐个儿号脉、开药,这个病人刚离开,便喊下一个,这时白老太太刚喊:“下一个”,这四人就一块儿上来了,白老太太台头一看,立即一绷脸儿:“你们四个老不死的来捣什么乱,没看我这儿正忙着了吗”?“老姐姐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在这儿一人儿吃独食儿,让我们在一边干看着啊,行善事儿也得叫着我们啊”。
有人问,这四人是谁啊?大概有的人已猜着了,来的这四人正是胡大爷,黄二爷,柳三先生和灰四爷,白老太太揶揄的说:“你们四个老不死的想跟我一快儿赈灾?不怕耽误你们的修行啊”?胡大爷说:“行这等大善之事能顶十年修行啊,我们能落这个空儿吗”。
“那好,我就不客气,给你们派差事啦”,“小弟们全听大姐吩咐”,“得,胡老大你就在这儿给我盯着粥棚放粥,黄老二,柳老三,灰老四你们敢紧给我往这儿捣腾粮食和药材,我这儿可是快接不上顿儿了啊”,“好啊,我负责放粥没问题,老二和老三有的是药材,老四的粮食更是没问题,就这么着,你们仨赶紧着吧,别让大姐着急了”,胡老大对那哥仨下了逐客令。
白老太太的右邻街坊周兆林,也是行善之人,但家里不裕,因而自愿到白家帮工,每天早起为那二十口赈粥大锅挑水,这天可能是起早了,正要挑着水桶出门,忽听街上“唰、唰”的有人走路,听着还不止一人,像是有很多人,“难道又来了新的难民?不对啊,怎没有噪杂的说话声儿”?于是扒着门缝向外观看,这一看,吓得他目瞪口呆,差点儿没坐在地上。
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儿?锁儿爷说,满街桶子都是耗子,黄鼠狼和长虫,那耗子个大呀,说着用手一比划,“有这么大个儿,二栓子,比你们家的猫还大,那黄鼠狼多的数不过来,那长虫都一讨(绦)多长啊,(农村说的一绦是五尺),三路纵队,正往白家送粮食和药材呐”,那帮工心里说,“难怪白家的粮食,药材总是用不完呐,这白老太太会法术,能拘五大仙呀”。
本章完,请看下章: 五仙赈灾招祸灾,衙内乱轮三姨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