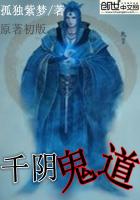左宗棠瞥了天门一眼,冷不丁说道:“官无官智,民无民德,圣贤之礼俱失,岂不失地陷城!”
众人面面相觑,骆秉章的脸色极为难看,曾国藩看着郭嵩涛,心里说,这是什么人,怎么如此乖张。
天门知道这些士林清流向来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并不愿与之有任何交集,想着将这场饭局应付过去,各自东西,从此路人。因此虽听左宗棠话里有话,有意挑衅,却毫无反击之心。
郭嵩涛正要打岔,左宗棠接着说:“依左某之见,叛军只所以能成今日之势,究其根源,全因旗人视天下为私产,未能真正做到‘满汉一家’之故。旗人有家主之实权,无治家之实力,汉官有治家之心力,却因担着家奴名分,不肯相残于兄弟……”
郭嵩涛拿眼瞪他,“季高,季高,扯远了!”
左宗棠心里说,你既拉我来混脸熟,不叫曾国藩领略我的见识,岂不白落个攀权附贵的恶名。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左宗棠无功名在身,有何可顾虑的,他正是要将心声说给这两位朝官知道。
他便依然我行我素,“太平军算什么军?乌合之众都算不上,一帮子贩夫走卒,流氓地痞而已,牛刀杀鸡,竟被鸡蹬翻了桌案,岂不令天下人耻笑。”
这屋子里,既有刚刚离任的一省巡抚,又有当朝四部侍郎,左宗棠仅是“搜遗”举子,竟大言不惭妄议国事,简直太狂悖无礼了。
骆秉章忍无可忍,但毕竟老道,不纠缠左宗棠的理论,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问道:“这位仁兄,骆某请教,圣贤之礼如何讲?”
哪知这是左宗棠设的陷阱,他含笑道:“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骆大人以为在下尚礼而无礼,孰不知在下正是谨遵圣人的教诲,‘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在下的话虽未必中听,却是心不藏奸,舍己为人呀!”
骆秉章被噎得哑口无言,想了半天,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驳斥他。
左宗棠在湘乡素有辩名,鲜有对手,骆秉章是官场中人,循规蹈矩,迂腐日久,怎能应对得了他的“胡搅蛮缠”。
郭嵩涛忙给骆秉章递台阶,“骆大人,季高向来没有章法,不必理会他。我讲一则季高的趣闻吧,道光十八年,他赴京会试,恩科诗题是‘师直为壮,得平字。’,你道季高作了一首什么诗?”
曾国藩一怔,他便是道光十八年的进士,那一年的诗题是“天心水雨”,道光二十一年诗题才是“师直为壮”。
曾国藩见左宗棠并不纠正,便要听郭嵩涛要编出什么故事来,因而也不点破。
骆秉章知道“师直为壮”语出《左传》“师直为壮,曲为老。”这一年朝廷命林则徐赴广东禁烟,道光钦定试题,有为自己鼓气之意,不知左宗棠这个狂人如何作答。
郭嵩涛清清嗓音,诵道:
“司马忧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
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
龙户舟横宵步水,虎关潮落晓归营。
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
骆秉章听罢大为吃惊,心说这个狂人的确狂得有道理,凭这首诗应该可以取第的,因何名落孙山呢?
郭嵩涛问:“骆大人以为这首诗如何?”
“将林大人比作岭南长城,甚是贴切,若末朕能点出‘天子之威,慑服四方’则更合题旨。”骆秉章不由对左宗棠产生了好感。
“骆大人一针见血,此诗前面诸联都妙,坏就坏在末句上。季高报国之心太操切了,以林大人衬托自己,借诗言志,表明心迹,反而弄巧成拙。”
郭嵩涛瞧了曾国藩一眼道:“据说皇上阅卷后,只轻轻吐出四个字‘真书生也!’,便把季高刷下去了。”
曾国藩等人不由轻笑,左宗棠红了脸道:“道听途说而已。”
天门忍不住调侃说:“恐怕不是因为那四个字,而因为最后三个字吧。”
“你是说‘佐太平’吗?那时尚无太平军一说,怎会因言废事?”郭嵩涛道。
“邵公子说笑罢了。”曾国藩说。
左宗棠却当了真,冷笑道:“照邵公子的说法,左某若是今年以此诗应试,岂非要引来杀身之祸?”
天门语出惊人:“左先生幸亏未及第,若早些年入仕,或真有灭顶之灾也未可知。”
郭嵩涛心说,好嘛,我好容易按下一个狂人,又冒出一个狂人,左季高岂是省油的灯,两人又免不了一番唇枪舌战。
“哦,邵公子何出此言?左某倒要请教一二。”
左宗棠懂阴阳术数,研究过自己的八字,知道自己命里有凶星当值,对天门的话有些认同,只是不知他是信口胡说还是精于此道。
天门笑笑说:“你自知命数,何需问我。”
“邵公子既然有意卖弄子平术,何故吞吞吐吐,莫非仅是一知半解,故弄玄虚吧?”左宗棠反唇相讥道。
“断你的命数,一知半解足够。”
天门的孤傲比之左宗棠有过之无不及,令骆秉章等人为之侧目,连曾国荃也听不下去了,道:“听邵公子的口气,似有太公垂钓时的自负……”
曾国藩暗中扯了下九弟的衣襟,说:“天门,季高也精通阴阳学法,你们何不切磋一番。”
左宗棠已经被激怒了,道:“既然棋逢对手,岂能错过。今日虽当曾老夫人大事,左某也要先和曾大人告个罪,便失礼一回,向邵公子讨教一番。”
“大家同为士林中人,坐而论道,何罪之有。”曾国藩说。
“我非举子进士,算不得士林,刚才一时失言,多有冒犯,请左先生不必计较。”天门说:“骆大人还要赶路……”
左宗棠以为天门在讥讽他的出身,恼道:“请问邵公子是何出身?”
“不曾参加过任何考试。”
“哦,那便是不屑于圣贤文章,瞧不上在座士林的学问啦?”
“并非不屑,而是不适于入仕。”
“哦,左某明白啦,邵公子自认是当今的卧龙,不世的高人吗?”
天门已后悔刚才的多言,有意和解,但面对左宗棠的咄咄逼人,他终于按捺不住性子,道:“龙潜于水仍是龙,鱼跃龙门仍是鱼。”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左宗棠是“搜遗”补录的举人,“鱼跃龙门仍是鱼”,似是在暗讽左宗棠鱼目混珠。
“哼,邵公子难道不知鱼跃龙门,过而成龙吗?”左宗棠道:“请你这位‘潜龙’用‘半解’学问断一断我的命数,叫左某长长见识吧。”
“不用费那么多周折,左先生的凶年已过,好事将近,眼前便有贵人……今日之后,你便一路通达,未来封侯拜相全无阻碍。”
什么?封侯拜相?众人全都愣了,众人之愣,因不了解天门,以为他是说气话。曾国藩却是认真的,左宗棠并非科甲出身,怎么可能封侯拜相呢!
“你在取笑左某吗?”左宗棠怒道。
天门笑了,“你要天门为你看命数前程,直言相告却又说我取笑你,真是岂有此理。”
“‘书生岂有封侯想’,左某有自知之明,不会有非分之想,你何出此言?”
“信不信由你,六十年后见分晓。”
“二十年后?哈哈哈……”左宗棠放声大笑,笑了一半,发觉不合时宜,忙瞧了曾氏弟兄一眼,收住笑声,道:“还说不是取笑,这种乱世,左某岂敢奢望再活二十年。”
郭嵩涛不悦道:“邵公子果然谙熟江湖之道,惯于见风使舵,所言皆四平八稳,无可佐证,不用问,你说季高眼前的贵人,定是曾大人喽!”
天门看也不看他,说:“曾大人当然会成为左先生的贵人,不过眼前却不是他。”
“是谁?难不成是邵公子?”
“骆大人。”
“骆大人?他已解职回京,怎么会成为左某的贵人?”左宗棠疑道。
“世事难料……”天门话刚出口,拇指上的扳指忽然滑落下去,险些掉到桌下。天门手疾眼快,伸手接住,心念一动,道:“骆大人恐怕回不去啦!”
众人都觉好笑,认为天门已经人慌失智,开始胡言乱语了。左宗棠此时要卖弄他的相术,仔细端详着天门的相貌,说:“左某也给你相一面如何?”
“请便。”
“你面如软玉,鼻似如意,眉走太阳,耳廓半掩……不对啊,你自称不热衷仕途,却正逢宝盖两口中,你在官哪!你莫不是……宫里人?”
曾国藩听出左宗棠在骂天门是太监呢!这不仅是侮辱天门,也是打他的脸。想他在朝为官,十数年不回家,回家葬母,却带宦官回乡,岂不可耻。
“左宗棠,你这是何意?”曾国藩怒道。
郭嵩涛也知这玩笑开得太过分,道:“季高,你多大的岁数啦,还这样混不吝!”
“我看‘麻衣神相’里有这种面相,要错也是古人错了!”左宗棠辩解道。
天门说:“左先生说对了一半,天门的确险些做了太监,曾大人不记得那一年闹得满城风雨吗?”
“是有这么一回事,不过……那次误会竟也能入相吗?”
天门笑笑,心里说,给左宗棠一个台阶下吧,免得大家尴尬。
这时,曾家仆人进来传话,称湖南巡抚派差官求见骆大人。
原来骆秉章绕道湘乡之事,是和新任巡抚张亮基知会过的,张亮基也有一份祭礼让他捎给曾国藩。
张亮基接了上谕,要骆秉章不必回京,仍留在长沙城协助御敌。
差官通报完上谕的大致意思,除了曾国藩之外,众人全都傻了,一齐看向天门,全都感到不可思议,再无人敢怀疑他的“龙潜于水仍是龙”之说。
左宗棠知道这绝不是巧合,而是真遇到了“神人”,他瞧了瞧骆秉章,再看一眼曾国藩,然后目光停留在天门脸上。这一刻起,一改玩世不恭的态度,变得无比庄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