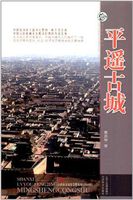惠亲王虽不如穆彰阿有城府,却也非省油的灯,他瞧出幕后主使是穆彰阿,便擒贼先擒王,欲拿话唬住他,只要他示弱,那些穆党中人没了靠山,便容易对付。
穆彰阿皮笑肉不笑地回道:“既然王爷说不是隐秘,请把实情讲出来,让大家都明白明白。”
惠亲王没想到穆彰阿并不买他的账,当即一怔,不禁有些慌乱。
穆彰阿为何不惧惠亲王的要挟?只因惠亲王这次犯的错太大,无论怎样解释,都躲不过律令宗法的惩治。
这是穆彰阿搬倒他的最佳机会,因此穆彰阿决定孤注一掷,拼得丢了老脸,也要将惠亲王拉下马,以解心头之恨。
何以说是丢了老脸,而不是获罪呢。
原来,穆彰阿早有预判,史正如今不知去向,惠亲王无法以江仁轩那宗贿案治得住他。要说天门会不会把他杀人的秘密告诉惠亲王,这个时候,已经无关紧要了。
惠亲王犯得是忤逆大罪,在议定他的罪状当口上,无论他告穆彰阿什么罪,都有诬告的嫌疑。道光要顾着保住他,便不能深究穆彰阿的事情。而且穆彰阿当年做的那些事,死无对证,查无实据,说出来顶多让众人心中存疑,却没有办法治穆彰阿的罪。
穆彰阿的时机把握得极好,下手便又准又狠,打得惠亲王方寸大乱。
众人见穆彰阿有逼宫之意,便都群起附和,要求惠亲王坦白。
惠亲王被逼到了墙角处,再无回旋余地。他有心要把天门事关立储大计讲出来,说明他是为了防备别人找天门预测圣意,才教他骑术,带他离开京城。可是这种话在朝堂上怎么说得出口。
便是说出来,那些刁钻的大臣们也会强词夺理,加以批驳,反而更加被动。惠亲王权衡再三,觉得自己受委屈事小,皇上的尊严事大,万不可因小失大。
惠亲王无言以对众臣的相逼,望着道光发呆。
让惠亲王与群臣对证,是文庆的主意,他万没想到穆彰阿身为军机大臣,会不顾大局,领着众人发难。
眼看着局面失控,道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文庆只得硬起头皮,出来解围道:“穆中堂,众位同僚,这儿可是朝堂,当着皇上的面如此吵闹,成何体统。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有事慢慢理论便是。”
“还理论什么,事实摆在这儿,惠亲王身为王公大臣,行为不端,应交宗人府查办严惩。”那位御史叫嚣道。
文庆终于抓住破绽,当即喝道:“尔作为言官御史,直言进谏虽是你的职责,可惠亲王交不交宗人府,要请皇上的旨意,你口出狂言,意欲何为!”
那位御史意识到失言,当即闭口退到一旁,众人这才消停下来。
文庆趁机奏道:“皇上,臣以为,惠亲王领旨办差,可以便宜行事,没有奏请延期算不得过错。至于擅入健锐营一节,可传健锐营统领前来对质,若惠亲王真是练习骑术,并无其它僭越言行,加以申饬,令其检点反省便是……”
穆彰阿道:“文大人的话臣不敢苟同,按大清律法,没有皇上旨意,不得擅入兵营,调动一兵一卒。臣斗胆说句大敬的话,如今皇上年事已高,皇子年幼,以惠亲王的身份,擅入健锐营,怎能不令人忧虑!岂是一句练习骑术便可搪塞的!”
他这句话够歹毒,像一把尖刀,正戳在道光的心窝里。
做皇上的最怕别人惦记皇位,道光年老神衰,疑神疑鬼,对选个储君都犹疑不定,若说年富力强的惠亲王有异心,岂能不疑。
经穆彰阿一挑唆,道光的思路便被引入歧途。
道光想,老五的行为是有些诡异,主动请旨去热河,又不按时起程,却跑去健锐营,而且,还把身怀奇术的天门招至身边,难道他真有反心,要借朕去围猎之时,趁机谋反夺位!
道光打量着惠亲王,脸上的神色凝重起来。
文庆心说不好,皇上定是被穆彰阿话的蛊惑了,开始怀疑惠亲王,这个结可不好解。
惠亲王道:“穆彰阿,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本王的品行皇上是知道的,岂会相信你的挑拨。”
穆彰阿冷笑道:“惠亲王的品行如何,不仅皇上看得清楚,众位大臣也都心知肚明。一年前你还韬光养晦,托病不出,摆出一副闲云野鹤的姿态。可是看到皇上龙体欠佳,便立刻跳出来,借查多年陈案之机,清除异己,安插心腹,网罗术士妖孽,如今又遁入兵营,排兵而阵,这一切,你作何解释!”
穆彰阿的话,不啻于晴天霹雳,把惠亲王一下子击懵了。
惠亲王脸色苍白,指着穆彰阿,道:“你,你,血口喷人!”
话说到这份上,文庆便不敢轻易说话。
道光冷冷地对惠亲王道:“你还有何话讲!”
惠亲王颓然倒在座位里,苦笑道:“皇上,你不要听信佞臣谗言,臣弟是何等人,你最明白……”
“朕从前糊涂,现在有些明白了。”道光说:“你来说,穆彰阿所言可是事实?”
怎不是事实,那些事都是惠亲王做过的,可是经穆彰阿巧言令色一番说辞,惠亲王竟无力辩解。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惠亲王魔怔了一般,反复念叨着。
道光高声道:“来人啊,将惠亲王绵愉交宗人府……”
文庆闻言焦急万分,若把惠亲王押入宗人府,不管是会同刑部审查,还是直接圈禁,再想出来可就难了。
他赶紧跪倒说:“皇上且慢,仅凭穆彰阿臆测之言,岂可将惠亲王定谳。健锐营统领和邵天门押在外面,何不传他们进来,听他们的口供再作定夺。”
“皇上,那统领和邵天门都是惠亲王的心腹,他们的话不足为凭。”穆彰阿道。
“穆大人,你这就不对了,你便是欲置惠亲王于死地,也得让他心服口服,铁证如山才可以……”
“不要争论了,先把健锐营统领带进来问话。”道光说。
那统领知道擅准惠亲王进入兵营,犯了大清律法,如今事发,其罪不小,因此被押进来后,跪在地上,如筛糠一般,抖个不停。
文庆道:“皇上有话问你,要如实回答,如有半句不实,你可知道后果?”
“小的知道。”
道光懒得发问,道:“文庆,你替朕问他话。”
“臣领旨。”文庆转而问那统领道:“可是你准许惠亲王进入兵营的?”
“是。”
“他可出示皇上谕旨?”
“不曾。”
“那为何置国法军令于不顾,擅自请惠亲王进兵营。”
“此前,惠亲王多次带阿哥们来健锐营习学骑射,都是传得皇上口谕,这次也说要练习骑术……因此便没有拦阻。”
“他可与你谈论过别的事情?”
“惠亲王只吩咐小的,派个教官带一个少年去马场练骑术,不曾说过别的事情。”
文庆很满意他的回答,略加沉思,问道:“惠亲王没与你说过调兵什么的?”
“不曾说过。”
穆彰阿插话道:“文大人,你这样问话,他怎会说实情,依臣之见,把他交到兵部,会同刑部严加审讯……”
“穆大人,你是要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吗?”
那统领知道此事惊动皇上,绝非儿戏,磕头赌咒道:“小的讲的话句句属实,如有半句假话,愿赔上全家老小性命!”
文庆回禀道光:“皇上,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道光摆摆手,道:“交兵部依军法议罪吧。”
押走那统领,文庆叫传天门。
穆彰阿奏道:“据臣所知,邵天门乃江湖术士,擅于诡辩,朝堂庄重,岂能让这种人登堂入室。”
文庆含笑道:“穆中堂,我可听说你欲和邵家结为亲家,将孙女嫁给邵天门的。”
穆彰阿被揭了短,顿时讪然,辩解道:“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本官只是和邵如林说笑罢了。”
文庆本不愿和穆彰阿作难,但今日见他气焰嚣张,非要陷惠亲王于不仁,不由心里愤恨,便奚落道:“穆中堂,儿女终身大事,可有说笑的?你是看邵家落势,不想认这门亲事吧?”
“文大人,我们说惠亲王的事儿呢,怎么扯上我啦?”
“路不平众人踩,你污蔑邵天门是妖孽,我当然要和你掰扯掰扯啦!”
办大事要紧,穆彰阿不想和他纠缠,道:“传邵天门进来。”
天门被侍卫推搡进大殿,扫了左右两眼,大摇大摆走到中间站定,等道光问话。
文庆示意他跪下。天门视而不见,面含微笑,玉树临风一般岿然不动。
先前那位御史喝道:“大胆狂徒,见了皇上为何不跪。”
穆彰阿奏道:“皇上,这等轻慢君王的狂悖之人,应该杖毙。”
道光知道天门从不跪人的禀性,只是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不守纲常,实在嚣张。
道光顾着自己的尊严威仪,正欲发作,穆彰阿瞧准了时机,断喝一声道:“来人啊,将这个不仁不义,冒犯天威的东西拖出去,杖毙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