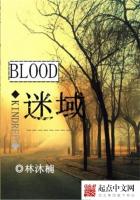整整一夜,我都未能合上眼睛睡觉。不是因为家里放了十五万块钱,而是因为只要一闭上眼,就能看见一张猥琐的男人的脸,朝我凑过来。那么淫邪,那么恶心。
我的脑子里像塞满了乱麻,想理也理不清。这些天来一直隐隐作痛的头,又剧烈地痛起来,而且伴随着阵阵恶心呕吐的感觉。我想,一定是大前天给摔的,兴许真被摔成脑震荡了,不然,怎么老会有这种症状?我应该抽时间去医院检查检查,以免延误了治疗。
可眼下却根本不是考虑检查治疗的时候。尽管我恨死了苟占光,恶心他那张猥琐的嘴脸,却不得不优先考虑如何跟他交易,拿自己的身体,换取儿子和几个侄子的自由。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想,我就是为他们几个混账家伙的糊涂行为而牺牲的“佛”……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去苟家,叫出苟占光,告诉他我愿意满足他的条件,不过,得等玉树几人放出来之后才能兑现。苟占光听我愿意满足他的条件,先是一喜,接着却冷笑道:“钱的事可以等玉树几个放出来才兑现,但那件事不行,必须得先满足我。否则,我怎么敢断定你一定会认账?”
这家伙真他娘是个老狐狸!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把戏,他是怕我到时反悔呢。我没别的办法,只好答应,并恨恨地说:“你就不怕我到时不认钱的账?”
苟占光嘻嘻笑道:“娟,只要咱们上床成就了好事,其他的,我还用担心吗?”
苟占光说得猥琐淫邪,我只觉得一阵恶心,恼怒地道:“那就赶紧跟老娘去公安局!见到你****的就恶心!”
“好!我这就跟你走!”苟占光胜利地笑了,笑得真他娘的开心!
到了县城,苟占光找了一个偏僻的旅馆开了间房。我知道我已经是他砧板上的鱼肉,由不得我挣扎了。不得不横下心来,想他不就是想要自己的身体吗?老娘又不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怕什么?凭什么两个人上床,就非得说成是男人占女人便宜?不能说成是女人占男人便宜?……
我躺在床上,把眼睛闭了,不愿意去看那张让人恶心的嘴脸。苟占光像一头饿得快疯了的公猪似的,一张嘴在我身上乱拱,并发出一阵剧烈的哮喘。他的手跟刨山芋似的,急迫地剥了我的衣服和裤子,然后一个虎扑,便将我压在了身下。
我几乎咬碎了银牙,咬破了嘴唇,才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我知道,我的身体从此不再仅属于亮子,从此不再神圣,不再干净……我的眼泪,顺着双鬓疯狂地流下,淋湿了枕巾……
半个钟头后,苟占光完事了。急慌慌去穿他的裤子。我却躺在床上,像一具毫无生气的死尸。苟占光见我不动,嘲笑地问:“你干吗不起来?还想再来一盘?”
我不答。我的心已经碎了,不,是已经死了!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死亡。我的脑海里一再闪现出残忍的一幕来:我看见自己走上跨江大桥,纵身一跃,便从几十米高处,跳进了渠江……
“娟,赶紧起来,咱们还要去公安局不是?”苟占光已经穿好衣服,走过来,拉开覆在我身上的床单,俯下身来,色迷迷地看着我的身体。
我一把抢过床单,重新给自己盖上,心里的悲苦再忍不住,竟嘤嘤地哭了。
“你不起来我可走了哦!”苟占光急了。
我依旧不答,只管哭。屈辱让我忘记了自己受如此奇耻大辱到底所为何来。此刻,受辱这件事情本身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想不了别的。
“女人就是女人!麻烦!你说你有什么好哭的?你就像一截木头躺在床上,既不解风情,又不懂享受,害我累得要死还不快活,我没说不满意,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跟你说我要是叫个小姐来,人家会服侍得我舒舒服服的!早知道和你这么没劲,还真该收你两万块钱算了!”
苟占光愤愤地说着,拍了拍屁股,竟拉开房门说:“你就躺着吧。我到公安局办事去了。记得玉树几个出来后,给我那二十万。不然,我把你大腿根有块紫色胎记的事告诉你家亮子去!”
苟占光离开了,临走连门都没关,他这是要逼我赶紧起床。他可真是个混蛋,阴险十足的小人!
房门敞开着,我再不能只顾沉浸在无穷的悲伤里。所谓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要是服务员见门开着,进来看见我这个样子,一定会认为我是出来卖的,到时我可怎么回乡见人?我赶紧擦净身子,穿上衣裤,梳理头发,佯作镇定地走出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