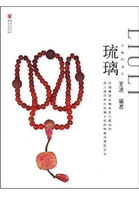“剑诀怎么会入魔?”谷风纳闷道:“师父,伯兮炼紫极生灭剑时并无异样啊?”
入魔有两种,一种是指修炼心法以夺取旁人精血、性命甚至神魂为主,为天道不容,最后被反噬丧失人伦;一种则是所有修者都会遇到的,在突破境界时遭遇心魔,不能堪破就此入魔。伯兮显然不是前者,而后者,从他平时行事也可以看出来,谷风几十年没有见过他,说话虽不如以往亲密无间,却也听不出有什么偏激愤恨的地方。
召南摇头:“不炼的人实难体会,我亦不能确定此事。天下剑诀何其多,伯兮有吞月赤髓剑体,什么剑诀炼不成?断骨锁魂狱一年断一次根骨不假,若非如此保不得性命,只是我所希望的,从来不是要他日夜承受痛苦折磨。”
颜晓棠猛想起“师祖”说的一句话来,但她不确定该不该说,当时“师祖”是当着伯兮面说的,“一剑生,一剑灭,既能使万物复苏,亦能屠尽万物。”伯兮知道,但他为什么不说?即使如此他还在修炼紫极生灭剑,几乎没有一天停顿。
颜晓棠扭过头看了看伯兮,伯兮手指指尖用力过猛,都陷进了石砖缝里,骨节发白青筋纠结。
他知道的比召南多,但他没有跟召南说。
颜晓棠傻的时候不多,很快就明白过来,修炼其他剑诀是可以,可是修为却回不来了,不管他以前是什么修为,只要断骨锁魂狱还在他身上,他的修为最高就只有筑基,想要结丹,没个几年,灵体也做不到,而他只有一年的时间,要是没有办法在一年内筑基的话,他甚至只有炼气期的修为,这么点修为,跟落霞宫的弟子一样,一辈子都出不了头了。
换个人,或许在重重艰难前会放弃,毕竟这么难,连敬仰的师父都不允许他再炼,还用誓约来约束他,更没有一个人支持。
一个人反对,可以坚持,一半人反对,还是可以坚持,但是所有人都反对呢?凭什么确定自己是对的?
放弃的理由有一百个,坚持的理由只有一个,颜晓棠想就算换到自己身上,恐怕也坚持不下去了。
但伯兮不会的,颜晓棠很笃定,不管看起来多温顺服帖,伯兮的心气从未被磨平。
召南想要用断骨锁魂狱让他放弃紫极生灭剑,可恰恰正是因为断骨锁魂狱,伯兮才不可能放弃紫极生灭剑。
颜晓棠跪直身,目视召南道:“师父,你曾说过,熊胆和紫河车虽取之不详,本身是没有好坏区别的,紫极生灭剑到底会不会让大师兄入魔,你也不清楚,我觉得与其相信紫极生灭剑剑诀让人入魔,不如相信大师兄的心念——他是你教出来的,你都不信吗?”
召南默然沉思,颜晓棠乘机朝师兄弟们看了一圈,月出是没胆,徙御……更没胆,就只有谷风悄悄对她竖了个拇指,看来谷风跟伯兮的关系确实不像她以为的,不过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分别,她只分别出伯兮一人就好,因此也没理谷风。
谷风早习惯了她的态度,并没有当回事。
召南想过后道:“颜颜,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断骨锁魂狱已经跟伯兮成为一体,硬要取出的话,难保神魂不灭。”
不能取,又不能炼紫极生灭剑,是要伯兮像虫子一样死在泥尘里?
颜晓棠心口一堵,气话冲口而出:“师父,你自己都说不能确定会入魔,既然不能确定,为什么要逼大师兄立誓不用紫极生灭剑?还特意把断骨锁魂狱炼制成了压制紫极生灭剑的枷锁!徒儿不解,请师父回答,当初把大师兄带回来,究竟是为了他好,还是只为了壮大太微仙宗?”
“颜颜!”谷风喝斥了一句,然而没什么用。
颜晓棠根本没有停顿。
“如果是为了他好,为什么不能给他机会!?可见是后者吧?紫极生灭剑不是大师兄自己选的,一开始修炼也不是他决定的,发现了不能证实的隐忧,担心他将来可能会威胁到太微仙宗,就干脆地牺牲掉他的话,我无话可说!”
“颜颜!住口!”谷风再次喝斥,却被召南摆手止住。
事涉伯兮,伯兮没说多少,一开口便是自承错误,师徒间不正该如此么?偏偏颜晓棠爆发了出来,跟她一向做事风格一致,从不胡搅蛮缠,几句话就扒皮见骨,哪怕是对着师父召南。
召南长叹,叹息声未落,四周寒气聚拢,召南脸色一变,立即喝止已经来不及,匆忙挥手出掌,一道青光把伯兮对颜晓棠挥出的剑芒打散。
伯兮动手动得毫无预兆,跪直起身,漠然地看着颜晓棠。
别说月出和徙御,连谷风都没料到伯兮会出手打四师弟!
颜晓棠的质问句句在理,在伯兮动手前的那一会,他们谁又敢说自己没被说服?召南不是其他随便什么德高望重的长辈,他是一方仙宗的掌教,事事都要把太微仙宗放在他自己之前,早在谷风做普通弟子的时候,就知道召南是担心自己有了私心,所以不收亲传弟子,不是伯兮太特殊,恐怕根本不会破例。
为了壮大太微仙宗,可以破例收有吞月赤髓剑体的孩子为徒,同样的,为了解除太微仙宗的隐忧,再亲手将这个弟子关起来……合情合理,冰冷得骇人。
连徙御都心寒地想到,召南之所以如此关切他们的心情,担心他们走上歧途,也不是为了他们几个,而是为了太微仙宗。
月出最不想相信,他只是不想相信而已。
他们都动摇了,结果伯兮突然出手维护召南,颜晓棠是最没想到伯兮此举的人,直愣愣回头看着伯兮,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伯兮冷冷道:“不得冒犯师父。”
颜晓棠张了下嘴,脑子里却是空的,震惊?难过?她其实什么都感觉不到,眼眶一点点的红了,在丢脸之前拔身而起,两下轻踏地面,人就消失在墙外竹枝梢头。
召南没有阻拦,眼睛前方散落的白发被他少见沉重的呼吸拂得微微抖动,他把伯兮看了一眼,不知是心疼抑或是懊悔,都被压在重重的眉睫下面。
“散了吧。”说完,召南转过身,把房门一闭,跟徒弟们隔开。
他首先是太微仙宗掌教,其次才是伯兮的师父,不被徒弟当面指责质问,他甚至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把太微仙宗放在伯兮之前,但两边他都尽力在维护,错了吗?这般对伯兮,果然是错了吗?
在颜晓棠看来,他根本没有为伯兮做过什么,事实真的如此?
召南捏起自己一缕白发,苦涩无比地笑了出来。
颜晓棠疯了一样往山里跑,没有树枝可踏,她就像只鹿逐波落草而过,有树的地方,连她的身影都看不到个完整的,几个猎人还以为是什么飞禽经过,提弓引箭地追过去,只见到打着旋落下的树叶,她风一样掠过枝头和水面,没命地朝前跑。
为伯兮做了那么多,可他知道什么呢?
每天都在替他考虑,他又感觉到什么了?
在她帮他说话的时候,他居然为了什么“不得冒犯师父”的破规矩,向她动手!
颜晓棠就像呛了一口酒,辣在喉咙里,再慢慢发散向四肢百骸,她不求道谢,她只想伯兮少点痛苦,明明是天之骄子,却被最尊敬信赖的师父奉上了祭台,活得生不如死,卑微无比,只敢在人后才卸下点点防备露出真正的性情,连堂堂正正做人的权利,都被夺走了。
被伤得这么深,却还是要去维护师父。
颜晓棠想笑笑不出来,师父教得多好,都走到今天的地步了,伯兮还是师父的乖徒弟,可惜师父不领情,不相信他。
她不知道是在为自己难过,还是为了伯兮难过——伯兮真的不曾怀疑吗?不,她早就看见了,伯兮怀疑过的,但他好可怜,因为只剩下师父一个人在维护他,所以即使是师父亲手给他加诸了断骨锁魂狱,还把他关进了十渊牢,他还是逼着自己去相信师父,就怕这最后的维护他的人也背过身去。
这一份畏惧,伯兮藏得更深,不是今天朝她动手,她都不会察觉出来。
她很想回去对着伯兮大吼:明明最相信你,最在乎你的是我!可……她有什么资格去吼叫宣扬?陪着他五年多,无数次机会可以向他表明身份,都无意或者故意地放过,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根本没有真正关心他需要的是什么,到今天,才知道伯兮也怕孤独。
没有资格去吼,既为自己心痛,也为伯兮心痛,颜晓棠从来没被如此复杂的情绪纠缠过,站到一个无人的乱石滩上,迎着风喘气都没办法纾解胸口的重压。
身后一道风响,颜晓棠下意识朝旁一避,侧肩回头就看到伯兮一手剑指向她点过来。
颜晓棠那一股散不开的郁结之气立即冲开了浑身筋脉,心底道了声:“好!”反正已经陪了五年,要打就打,她照样奉陪!
伯兮不用剑气,她也不用兵器,伯兮看似对她动手,连真元也没有动用,每每要触到她立即移开,颜晓棠倒没这么客气,可就是……碰不到。
预判在伯兮身上是不会有用的,别人不用到死不能变的招,在他可能起手就是陷阱,哪怕看到他施展出了变化,也无法断定确实的剑招,他有时是水流中的飘萍,难以力取,有时又是四合八荒沉重的暮色,找不到可供下手的地方。
颜晓棠拼命地追上他的脚步,她很多时候都在千流剑洞里追伯兮的脚步,即使现在面对面也没有什么不同,她还是疲于奔命,身上的气憋着她死活不愿意放弃,哪怕伯兮在几招后就倒背双手,只躲不攻了。
避让之间,伯兮踩到了一块石头的尖角,身体些微晃了一下,颜晓棠抓住机会旋身追上,回手一抓,抓住了伯兮的头发,她立即就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