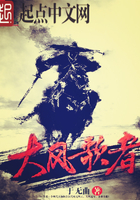仗着自己还是十岁,朱林议扮可怜,耍赖赖,朱天棠最终还是没能忍心下手拿家法打他,至少这次朱林议也是立了大功的,便算是信了他的话语。
当然,朱林议借此把那边盗贼是飞龙会的人,飞龙会背后可能有赵文华、严嵩的影子说了。
朱天棠也只是叹了口气,不多说什么了,反正如今也是假冒张居显一日是一日,至于飞龙会是不是会报复,那就再说了。
之后,朱天棠换了七品县令官服,开始正式办理嘉定县的政事,所谓万事开头乱,好在许多事情都是下面的胥吏在经手办理,虽然这也给了胥吏们耍刁弄虚的机会,可如今也没有别的人手,朱天棠只能作了一番训话,便让他们去办了。
由于县里缺少许多职位,王大木等几个一起从匠户村出来的匠户,便临时担当了县里的一些职务,当然,也只能管些简单的,这些匠户毕竟都是粗人,一些动脑子的事情也都干不了。
朱天棠别的不懂,可不误农事还是知道的,对地方上百姓农户的想法也是了解些的,反正自己这县官也不知道能做多久,所以他就颁布了借粮种的政令,另外又发布了一些利农的政策。
只可惜,这些利民政策也挽救不了之前留下的烂摊子……
朱天棠上任之后,便颁布了一些利民的农政,几乎把他从苏州府搬来的粮食分下去了八成以上。
就是这样作为春粮种子这些粮食还是不够的,所以朱天棠寻到了县里的粮商,用官饷采购了一部分粮食,这才满足了这次借粮种的政令。
不过,朱天棠这么做,差点让手下那些胥吏们闹了起来,但之前朱天棠也想好了对策,及时的也给他们发了银钱,还比常例多了几分,这才让胥吏们安下心来。
反正朱天棠这样做,日后要是出了什么差错,那也是朱天棠自己的事情,在这些胥吏们看来,朱天棠就是一个不会做官的傻书生,县官老爷虽然口中说着为民做主,却哪里有真的这样做的。
而如今朱天棠将官粮、官银分发给乡下贱民,其实是违规的,日后要是上面查起来,说不定朱天棠的官位都保不了,但这些胥吏们对初来乍到的朱天棠有什么背景来历都不清楚,以为朱天棠这样做,上面是有人罩着的,所以他们自己得了好处,当然也就不会对这件事情多管了。
只是这趟朱天棠从苏州府弄来的粮饷,差不多就剩下了五百多两银子,和少数粮食了,只是为了不误农事,原本筹建的乡勇计划,就只好先暂且停了,再说,如今县衙也没足够的钱粮满足乡勇的组建了。
请来的武僧空言便训练起了县中的铺房衙役,和那百来个调派来的兵丁,倒也不算是没事做。
这样,在县衙里面坐了十来日,朱天棠初步的了解些嘉定县基本情况后,感觉县衙里暂时也没什么事情,便想出去看看各地乡镇的具体状况,也算是实地考察一下。
确实如此,别说现在嘉定县破旧成这个样子,就算是以前倭寇没来的时候,其实知县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多,电视里那些敲鼓告状的现象,一个月也难得有几起,衙门深似海,有理无钱莫进来,普通老百姓一般有事情也不会上衙门,乡间宗族长老便会私下解决了小纠纷。
除非是盗贼、杀人的大案子,否则很少会惊动县衙,其实就算是杀人,有时候一些乡下宗族也敢私下里隐瞒下来,动用族刑,什么浸猪笼,杖毙之类,死了个把人,就往上报是掉河里淹死了,或者是生病死了,一般县衙也不会深究。
这就是封建时代,绝大多数地方上的管理体制现状,在封建早期是世家大门阀掌控地方的具体管理,到宋朝以后便是乡下的大姓宗族控制地方的具体乡务了。
哪怕是知县大人,在很多时候也不得不给这些宗族族长的面子,因为这些大姓宗族的关系网遍布大明各个阶层,一些宗族中人甚至是朝廷中的高官,知县也得罪不起。
这种宗族体制,最早是受朱元璋里老制度影响,渐渐发展起来的,到后来变成了大明士大夫阶层及其代表的宗族,通过宗族的乡约,强化对族人管理的手段,也是大明地方上重要的自主治理体制。
一般宗族内有宗正一职,就具有一定的审判权力,包括“据理割断”的审理权和“量情轻重责罚”进行处理的判决权,甚至通过族中长老会商,可以杀人。
闲话不再多提,所以地方上的知县,很多时候也是比较空闲的,朱天棠初来乍到,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故而就更清闲了。
朱天棠不想整天无所事事,就准备微服私访乡里,看看嘉定县的真实状况。
当然为了保护知县大人的安全,防止飞龙会的人伺机报复,武僧空言去掉了僧衣,带了个帽子,遮了光头,一起跟了出来。
虽然之前朱天棠也派人去那个曾经藏了飞龙会嘉定分舵的山谷密寨调查,但去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个寨子被飞龙会的人抛弃了。
不过飞龙会的人,会不会来报复,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朱天棠也不得不请了空言跟着保护自己。
但这次出行,另外还跟了朱林议、王小丫,王翠儿,王东宝四人,朱天棠被缠着没办法,也只好答应了这四个小辈。
王小丫、王翠儿两个丫头又换了男装,和王东宝、空言一样,扮成了朱天棠的跟班,一行六人在四月的阳春下,如踏春般恰意的游逛,只可惜常常会遇到方才这样的无奈事情,败了兴致。
这次下乡,原本就是为了调研民情,只不过是民间百姓实在艰苦,让人无法开怀罢了。
如此,一路行走,到了傍晚时分,朱天棠一行六人来到了嘉定县西北侧的一个村庄。
这还是朱天棠几人离开县城,遇到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看上去略微富裕的村庄,村里竟似有千多户人家,其中还有几户人家是青砖砌垒的深宅大院,都像是个小镇子了。
见到朱天棠他们这些外人进了村,一些小孩儿便围了上来,在旁边嬉闹着,还有几个孩子来到朱林议身边,稚声稚气的问,你们从哪里来啊?
朱天棠抬头看了看天色,便转头对那王东宝说道:“东宝,今日天色也不早了,你去这边问问,看看,能不能找户人借住一宿。”
王东宝如今十六岁,假扮一个小跟班正好合适,所以他答应了一声,便向村子里跑了过去。
这边朱天棠又对扮成俗装的空言道:“陆栋,我看这边村子里的人家似乎并不是太穷,不如我们到村里逛逛,看看他们是否还有别的营生,听说这边的人家以机为田、以棱为耒,有不少以织绢为生的机户,我看,这村子里,也许有这样的人家吧!”
陆栋是空言原本的俗名,如今换做了俗装,自然也恢复了俗名称呼,他笑着道:“张大,呃,我又忘了,嗯,天棠兄是读书人,自然比我这个武夫懂的多,不过,这边的地方确实有不少人家专门织布织绢,唉,也都是被这世道逼的,好好的田地没法种,却只做这些事情。”
“陆叔,你这话,我觉得不对,这种织布织绢的活也不错啊,至少也能在没田地的时候,织出绢布也能养家糊口,其实织布卖钱,未必比种地来的钱少!这是时势发展的必然,土地集中后的无产者寻找新活路的方向!”
朱林议听空言和尚对这种织布作绢的行当很是不屑,忍不住插口说着,其实这种织户人家也确实是民族资产阶级萌芽的表现。
“水儿,正所谓民以食为天,陆栋说的没错,农耕女织,乃是古之良训,农耕毕竟为主,女织不过为辅罢了。而如今农家不种田粮,家家户户却做那养蚕弄丝,织布纺绢之事,却是舍本逐末了,若人人不种田地,那又何来粮食养家呢?唉,不过,农家无地,却也是无可奈何!只是如此便说,这是时势发展之必然,水儿,你太武断了!”朱天棠在一边对朱林议教训道。
朱林议心说,农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只会让社会停步不前,无论封建经济如何保守,自然经济是绝对会被商品经济替代的,只可惜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却被野蛮的满人硬是用屠刀砍杀了,让中国从此落后于世界文明的发展。
但这个事实却不能说出来,总不能说,自己知道历史走向,他在脑中想了想说道:“爹,人人不种田地,那么米钱就贵了,米钱贵了,自然又有人去种田啦,这就是利之所趋,其实人世间的云云众人,皆为利来,便是考科举做官,也不过是为了获取权利罢了!”
“嘟,逆子,小小年纪,不专心用学,却想着这种邪说,人皆为利,科考做官,为求私利,那把礼、义、仁、智、信、厚的文人风骨丢哪去了!你这纯属是那些奸猾的商人为逐利而言的借口,我等读书,便是为了学道理,修炼儒家风骨,学的经世才,报于君王家,治理天下,调教百姓,使得民有其食,世事循良规,不让那些奸邪之徒,以邪说霍乱百姓!这便是圣人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逆子,平日里不好好用学,整日里就知道好勇斗狠,等这次回去,好好的把论语,大学两书,读上百遍!”朱天棠听朱林议还在狡辩,便不由得怒声喝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