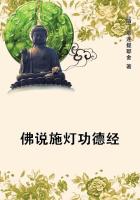要没了那种声音,他们的故事,该是会变得枯燥不少吧。
在那一个半月里,它就这样张牙舞爪明目张胆地窥视着一切,它心里什么都懂,但它不戳穿,暗红的眼睛一直转啊转。
贯穿生活的声音,藏在生活中每一个缝隙里的声音,就会被人常常忽略,于是黄鹂辛勤的叫声就被煊徵给忽略掉了。直到漪亦岚离开的那一天,煊徵一抬头,又听到了那种声音。那一刻他才想,原来那只黄鹂的叫声是这样的啊……那么清越,却又像一曲挽歌。
他们故事里的小精灵,这倒是他第一次注意到它的歌声。
“我也不记得了,”漪亦岚吐吐舌头,夜风把女孩的头发扬起来,飞扬的长发在昏暗的夜色里就像蓝色泼墨,“或许我跟本就没有想到给它起一个,它根本就没有名字吧。”
漪亦岚笑起来,煊徵摇摇头,也跟着笑起来。
一年了,只有这一刻,煊徵才觉得他又看见了原来的漪亦岚,说话还是那么毫无逻辑,那么没脑子。
“不过我叫她小黄……好像是这个名字来着,为了方便,却不是它的正式名字。”漪亦岚说,“我离开台北的那个早晨,打开了笼子,想放生它,可是小黄还不愿意走。这样一只鸟,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想的,低头啄几滴水,又抬起脑袋,通过洞开的笼门看看我。我没听说过还有这么执拗的黄鹂。后来我走了……它也走了吧。”
煊徵心想,有这么执拗的黄鹂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么执拗的主人吧?
“嗯,它飞走了。”煊徵想起了窗台上空空的铁笼子。
“后来我的病情恶化了,在新竹的一家医院住院,有一天清晨,我又在窗户外面看到了它。它停在窗台上,走过来走过去,收拢着翅膀,用红色的喙敲击着玻璃。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找到我的,又怎么从台北飞到了新竹。”
煊徵抬头看看漪亦岚的脸,她的脸在夜色里模糊不清,煊徵看不清她的表情。
这一刻,煊徵真的想告诉她,想告诉这个女孩,如果当初知道还能找得到她,翻多少山,越多少水,他也会去的。但他坐着火车从北而南再向北,围着台湾转了一圈又一圈,也没有找到她。他的运气还不如一只黄鹂。
煊徵最终没有说出这句话。
“那后来呢?”他问。
“后来小黄死了,死在了回台北的火车上。其实我早应该想到的,这一个多月来,我就和它在医院里,那样的一个生灵,毫无防护地暴露在各种病菌之下,又怎么能经受得住呢?我出院了,它却倒下了。它是回程的火车上闭上眼睛的。我回到了我们的小店,挖了个洞,在石子路旁边埋葬了它,上面插了一根木条。就是那时我发现墙边的木板位置被挪动过了,而且旁边杂草的长势也很奇怪。于是我知道,阿兄不久前你回来过,但我没有再见到阿兄。”
煊徵默默地听着,突然意识到她用了“我们的”小店。“我们的”,不是“我的”。煊徵知道他没有听错,没有听多一个音。因为你知道的,在英语里,“我们的”,和“我的”,是多么不同的发音啊,完全相异,泾渭分明。
“我去找过你……可是没有找到。”煊徵说着,忽然觉得鼻头一酸。
这是种什么感觉啊,他在委屈么……他坚强了自以为女孩已经永远离开了的整整一年,却在女孩离他最近的一次被彻底卸掉了防御。他攥紧双拳想要阻止这种情绪的蔓延,但他做不到。脆弱就像瘟疫,沿着他的血管传播。
“我知道。”漪亦岚轻轻地说。
在温柔的夜风里,煊徵的右手颤抖着,向着女孩的手,慢慢地沿着地面爬了过去。一如台北的那个有笛声的夜晚,两个人坐在满天星光的房顶上一样,时光一瞬间倒流了,两个人的形象与一年前的春天重叠了起来。他碰到了女孩的手,还是去年夜晚的触感,软软的,凉凉的。
漪亦岚没有躲。
那次没有,这次也没有。
“阿兄,我说起小黄的事,是想告诉你,它死了,那个过去的我,也已经死了。我或许不是死在了癌症里,但仍旧变成了另一个人。阿兄,我真的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漪亦岚了,”漪亦岚的脸转向背对煊徵的地方,似乎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的表情,“所以,请不要,再从回忆里找我的影子。”
煊徵看着她,摇摇头,手又握得紧了一些。
他知道漪亦岚在担心是什么。漪亦岚不再是那个漪亦岚了,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柔弱的姑娘,这他早就知道了。他不打算开口说什么,反而用这用力的一握,告诉她,别担心。
漪亦岚笑了笑,似乎果真就不再担心了,仰头望着满天星光。
“你还记得那个晚上么,一切心扉洞开,和一切分离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阿兄,这次你会让我喝酒么?”
煊徵也看着头顶流动着的漫天星辰,他当然记得啊……那个晚上,漪亦岚的笛声在夜风里像绷紧的琴弦一样忽然断裂,女孩哭着告诉她,他想喝酒。那个时候女孩已经做好抛下一切离开的准备了,第二天清晨就留给了他一个空荡的店门。
漪亦岚所说的,一切分离的预兆,和一切不可追之事。
煊徵郑重地点了点头。
不像去年的三月份那样,那一次,他拒绝了漪亦岚,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兄长,而喝酒是伤身体的事,就有必要拒绝这种任性的请求。而这一次,他同意了。他还是她最亲最爱的兄长,喝酒仍旧是一件伤身体的事……但他会陪她一起喝。
两个人,坐在慕尼黑六月底夜晚的夜幕下,两只手自然地合拢在一起,再无他言。
也不像去年三月的那个夜晚,这一次,直到深夜,漪亦岚的手再也没有抽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