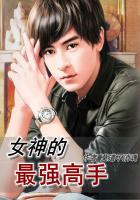角落处,杨涛与黑色鸭舌帽的男人就这样静静地对视着,直到良久以后那男人才默默地将帽子朝下压了压,黑色遮住了那白皙的脸庞。
“上次在沈家,我原本是打算带你走的,哎,但是却被发现了。”
“没关系,走不走都一样的。”
“不一样,做为一个医生我必须对你负责!”男人一边说着身子一边靠到了角落处:“火灾事件过后,我才知道你并没有死掉,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逃出来的,但是我还是有必要找到你,跟你把一切都说清楚。”
“其实我更愿意自己没有逃出来。”杨涛的牙齿紧紧咬着嘴唇,脑海之中浮现着惨死的少女,随后他定了定神:“你…为什么你…会认识我?”
“嗯,这件事说来话长,我也是根据一系列的线索,好不容易在这找到了这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聊聊吧?”
“嗯?”杨涛露出了疑惑,他轻轻地摇了摇脑袋,但是脚步却没有离开的意思,他疑惑的脸上眼睛转了转,然后又看了一眼面前的男人。
“怎么了?”男人问道。
“没事,我不想离开这,我习惯了流浪的生活,就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这就好了。”
“我可以带给你全新的生活,相信我,上一次没有救下你,这一次我会改变你,我不想让我自己的内心留下一道心结,相信我!!”
“哦?”杨涛的话音居然带上了一股冰冷的嘲笑。
“沈家给我三百万,让我帮他们做一个眼睛的移植替换手术,我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加上欠着沈先生的人情,所以只能妥协。”男人的声音顿了顿,转而继续道:“但是内心终究是无法接受这三百万,所以,我找到你,想要带你离开。”
杨涛抬起了头,蜷缩在地的他此刻可以看到鸭舌帽下的那张脸,那张脸正涨红地看着她,那眼神之中似乎充满了期待。
“真的,我说的一切都是实话,相信我,我会弥补这个遗憾的。”男人的一双手已经激动地抓住了杨涛,手的力道情不自禁地放大,眼神中的色彩没有一丝的作假。
杨涛的眼神露出了疑惑了表情,他认真而仔细地打量着男人,看着那身体微微颤抖,激烈的情感在脸上洋溢着一层层的红润,他终于有所妥协。
“没关系的,这种遗憾又不是你造成的,无论是不是你,都会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医生存在。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不,有必要,绝对有必须要!”那青年医生坚持着。
“不用,我就要结束了,这应该是我的最后一天了。”杨涛苦笑,他与白狐面具女人的约定已经到了这最后一天,三周在各种冷漠、无助、颓然与黑暗之中度过,而自己并没有接受这份黑暗,所以想必那个女人也不会再接受自己了。
“跟我走。”青年医生的话音从激烈变成了安静,他突然俯下身轻轻说了三个字:“诗梦语。”
“什么意思!?”杨涛猛地一惊,他连忙从地上跳了起来,一双充满血丝的双眼紧紧地盯着那青年医生:“你说诗梦语,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或许并没有死,去我那吧。街道的尽头,黑色的车,副驾驶没有上锁。”青年医生的话音变得平静起来,他慢慢地拿开了杨涛抓住他衣服的手,连忙退后朝着街道的另一个方向而去。
杨涛紧紧地盯着那个黑色披风的背影,那带着帽子的影子与他在沈家那几日看到的白大褂的形象千差万别。只是,他并没有思索很久就抬起了脚步。
毕竟,对于一个生命就只剩下一天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是值得恐惧与害怕的。更何况,这一声口中关于诗梦语的消息,他也没有任何的选择。
杨涛路过那家便利店的时候,里面的老板娘刚好出来,她突然紧紧地将手中白色的塑料袋塞入了包中,整个人退后二步。
透过白色的塑料,杨涛看到了里面一张张红灿灿的钞票,他一笑,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天以来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那一沓沓的钞票。
不过,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不是为了金钱呢?所有人都只会嫌弃钱多,不会嫌弃钱少,包括当年可谓富甲一方的沈先生。
玻璃门很快被反锁,女人一副小心翼翼地神色望着杨涛,杨涛苦笑,他望着街道上已经路过的三三两两的行人,知道自己的复仇的机会已经结束。
只是,脑海中少女的惨死他却是忘不掉的。
他的心猛地一痛,整个人控制着那股撕心裂肺地疼痛,逼迫着自己一步步朝着街道的另一侧而去。
每走一步,心都仿佛被利器切割了一刀,信誓旦旦的复仇之言,到现在,凝结为了一个个一边刀割一边撒盐的伤疤。
直到进入了副驾座,心如刀割的痛楚才慢慢地转移。杨涛望着坐在车上的青年医生,他依旧带着帽子,但是却不再是黑色,而是蓝色。原本黑色的披风也一样,他整个人黑色的套装依旧换成了彬彬有礼的蓝色。
“坐稳了,所有的事情等我们到了再说。”青年医生一边说着,一边拉上安全带,那深蓝色西装的袖口从杨涛无比肮脏的衣服上擦过,男人却连眉头也没有皱。
车子很快启动,穿过了喧嚣的都市向着外围而去。在路过一座红色的大桥时,杨涛呆滞的眼神忽然有了一丝的色彩,他的脸贴着车窗望着那在桥二端高高弓着的红色桥梁。
“这是彩虹桥,中间最高的地方距离有二十多米呢。”男人撇了一眼杨涛,淡淡地帮他解释着。
“彩虹桥?”
“嗯,不同的时间点会有不同的颜色,而且还不止七种,一些小年轻的也称它为许愿桥,深更半夜的时候经常有人想方设法爬到桥的最高处,然后在黎明前许愿,听说很灵。”
许愿?
杨涛轻轻叹了口气,混混欲裂的脑袋慢慢地缩回了座椅上,愿望对于他而言是多么的简单,却又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