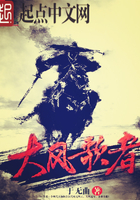我高高站在阶梯顶端,看着那十余名群众小心翼翼地走进院中。
两侧百名壮汉虎视眈眈,更有枪矛森森,寒光闪烁。
“小、小民参见马大人!”还没走到我面前,便有人带头仆倒在地,朝我大声喊道。
其余人立刻争前恐后跪倒一片。
被人顶礼膜拜的感觉总是十分爽快的,城府不够深厚的我忍不住一脸微笑着走下阶梯。
庞淯三步并作两步插在我与群众之间,我微微一怔,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早在这些人进院之时,我就已经将他们的肉搏能力摸得一清二楚,在我面前,这些地头蛇的作战能力无限接近于零。
“都起来吧,不必行此大礼。”不过庞淯这一阻挡,也打消了我亲自搀扶他们的计划。我就站在石阶上向他们喊道。
群众们互相看了看,迟疑了片刻,才陆陆续续爬了起来。
“请随意就席。”我摆了摆手,率先回到正厅,在主位上端正着坐下。
众人礼节性地谦让了几下,便各自坐下。
我开口道:“本府听说,月前本县大小十几口官吏,都被县民杀了?”
“是。”
“为何?”
“公孙度父子一再强拉青壮入伍,百姓苦不堪言,只能杀官。”
我点了点头。
人群中,有人朗声道:“将军口衔天命,奋马门伏波之余烈,为大汉诛公孙父子,实乃我辽东二十万百姓之福啊!”
马门伏波……指的当然是马援了。能说这两句话,至少证明,这货是个文化人!
我循声去看,说话者四十开外,瘦削身材,乍一看去,还真有些儒者气质:“怎么称呼?”
对方急忙敛袍一揖,恭恭敬敬地答道:“回大人,草民姓乔名凯。”
姓乔的?乔玄乔瑁的亲戚?“刚才听你言语,也是通晓文字之人,家中可有为官者?”
乔凯微微低头:“并无,草民只是城中一名教书先生。”
“教书先生?”我轻轻拍了拍大腿,“可通晓汉律?”
“草民不才,能懂一二。”他很谦虚地回答。
我点头,示意他坐下,而后环顾大厅:“座中诸位,在本县都有些名望,本府打算在其中选择几位担任县中长吏,你们有何意见?”
地头蛇们面面相觑,却都流露出不小的欣喜。
那乔凯却道:“大人,据三互法规定,不得在本郡国内担任官职。”
“三互法?”我略一思索,虽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但从他后半句话大致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我辽东距离京洛太过遥远,任命县吏往返数月,在此期间,也必须有主事之人,暂代处置本县事务,这并不违法吧?”
他急忙拱手:“大人考虑得是,草民惶恐。”
我向厅中扫视了一圈:“诸位可推举出适当人选来做这代行县长,当然,若是认为自己适合,也不妨毛遂自荐。”
地头蛇们集体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端起木碗,庞淯急忙弯身倒水。
有时候,我会感觉观察他人的神情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众人各怀鬼胎之时。
可惜这群人没能让我欣赏到这一幕。
“大人,”座中年纪最长的老汉咳嗽了一声,缓声道,“老朽等人虽小有家业,但若论通识律法,还要依仗乔凯先生。”
“是,”另一名老汉附和道,“辽东不比中原,文士本就难得,与其让我们这些粗人来瞎做,不如让乔先生来治理本县更为妥当。”
其他几位地头蛇也大多点头赞同。
我颇为惊异,这乔凯只不过是一名教书先生,竟然能让城中的大户推举他,这也十分难得。
“乔凯,你若为西安平长,可否胜任?”我转向被推荐人。
乔凯微微颤着声音答道:“绝不负命。”
我啜了一口热水,缓缓放下木碗:“本府的意思是,你区区一个教书先生,即使成为县长,又能否镇得住城中的大家大户?”我的目光越过乔凯,毫不避讳地射向他身后的众位地头蛇。
他一怔,明显想不到我会问得如此直接。
最年老的老人反映得极快,当即推案躬身,拜服于地:“府君在上,我等既然已推举乔凯为长,便决意听奉其命。若是草民阳奉阴违,甘愿受府君任何惩处!”
其余地头蛇也各自惶惶地趴伏于地,满口忠勇之词。
“既然各位都表了决心,本府便放心了。”我终于点头,清了清嗓子,喝道,“乔凯接令!”
“草民……乔凯……”乔凯忽然抖抖索索起来,舒展双臂就向下拜服下去,上身完全贴在地上,却依然难以遮掩地颤个不停。
“从此刻起,你便代行西安平县长,自县丞以下大小吏员,皆可自行任命。你可听清楚了?”
以我的耳力,即使在嘈杂的环境下,也能够清楚地听到一个人的呼吸。乔凯在我讲话时,呼吸一度加快,但在我话音落地之后,忽然恢复如常,甚至更为平缓。
他吸了口气,一点点抬起头来:“属下……乔凯遵命!”
我微微一笑,他对角色转换的接受速度倒是很快:“若无要紧之事,每隔一月派人向襄平汇报一次即可。虽然你初任官职,但现在秋收已过,今年的赋税还要尽快收缴,不能耽误正事。”税赋绝对是正事,这可直接关系到我的钱袋与粮仓……
此话一出,不仅乔凯,他身后十余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色。
“怎么?”我忍不住皱眉,难道……辽东这里的农民都不用缴纳税赋?难道这远离中原的偏僻之地,已经领先全国三千年、大踏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属下不敢欺瞒府君,”乔凯连同众人一起伏身于地,“近两年,公孙度连番用兵,不仅征调了大批青壮,更逼迫不少男丁离开乡土,如今的西安平一县,大半都是老弱妇孺,收成大不如前,若再征收重赋……”他稍停了两秒,又道,“百姓定然承受不起。”
我心中一沉:他所说的确是实情,直到今日,右北平的荒野上依然躺满了数万幽北男儿的尸体,这巨大的人口空缺,十年之内是不可能填上了。没有足够的青壮,农业便无法保障,我手下这两万余士兵的粮草便难以为继啊!
“只能少收一些了吧?”庞淯极力压低声音,在我背后嘀咕道。
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只好妥协:“公孙度之前征收多少?我们酌情减一些吧。”
老汉答道:“去年的田赋是八税一,人头税两百,许多百姓就算掏光家底也只是勉强凑齐,今年……恕草民直言,就算减半,也会有人活不下去……”
我大手一挥:“今年二十税一,人头税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