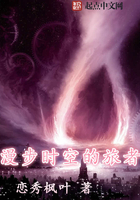紫石街在县城北边,是阳谷县最偏的小街,也因为最偏,租金便宜。阳谷县衙在县城南街,与紫石街隔着两个十字街口。由于街道狭窄,麻石路又不平整,加上那王婆身子软瘫,全凭武松提着才往前移步,走得并不是很快。一高一矮两个随从,各挂一把腰刀,一左一右跟在武松侧后。
武松半推半提着一个人,走得却急匆匆的,两随从被丢下一截,矮个子向高个子不停地挤眉弄眼,用下巴指了下武松。高个子眨了下眼睛,也用下巴指了下武松,好像示意矮个子上去。矮个子就看着武松。虽然武松前面血迹斑斑,后面看,都头袍倒还干净,那头乌黑和头发披在肩上,一弹一落。矮个子又看了下高个子,二人突然一转身,众高邻及后面看热闹的立刻站住不前。两随从又对视一会,同时转身向武松追赶,后面人也都加快了步子。
街两边早有看热闹的,木楼上也有小姐、媳妇扶住窗框,把粉白小脸探出窗外。看热闹的人虽缩在街道两边,能留下的路面宽度还很有限,不容三人并排行走。高矮两个随从追上武松后,又慢下来。再过一十字街口,能看到县衙,矮个子突然跨前几步,抢到武松前面,拦住武松的去路。武松一惊,盯住随从腰间挎刀,“张小四,这是干什么?”
“都头,你真的要去县衙送死?”
“俺去交差,何为送死?”
“以小的看,还是不要去县衙了!你想呀,杀人尝命,都头连取两条性命,我等也属帮凶,定然都会没命,可家中还有爹娘。不如就这里逃走。”
武松站住,“逃走,去哪里?”
矮个子随从说,“我等随都头出差东京,路上已知都头武艺高强,五七个强人不在话下。我等何不占个山头,好歹多活几年。”
大个子随从应和,“兄弟说的极是。武都头到哪,我俩跟到哪。都头要是不愿落草为寇占山为王,俺三个找个寺庙出家,做和尚,也比白送了性命好!”
那王婆这下开得口来,“都头做和尚,我这老婆子甘愿为你三个洗衣做饭,只要不去那衙门。”王婆还要说,武松一手力,“哪有你这刁婆多嘴的份!”王婆哎哟叫了声,止住了。武松如同自语一般,“做和尚,即是出家,断不可杀生伤命,今我武松连杀两命,哪还有资历进那佛门净地?也再无脸面见师傅高僧。”矮个子随从说,“那就找个别的去处。请都头随小的到一旁说话。”
武松把王婆交给大个子随从,随张小四拐进一个巷口。张小四说,“都头,小的可不想就这么死了呀!小的还没成过家,潘金莲就算心毒,也还生得漂亮,那么好一个身子,都头却要一刀结性命。”
武松厉声说,“武二正在气头上,你如何说出这种话来激我?”
张小四说,“我看那潘金莲死得有冤,小的一直盯那女人看,可她不看小的一下,就是拿眼来看都头,都头却不瞧视她。她临死似有话说,喉管一直在动,只是都头不瞧她一下,她才没有说。都头剌的是那胸口,可她却总是捂着小腹那块。都头去杀西门庆时,众高邻看女人尸体,竟没全死,一手捂了小腹那里,说什么‘武家后代‘呢。这可是众人都听得清楚的。”
“你是说,那淫妇怀了我哥哥的后代?”
“千真万确。”
“如何不早说?”
“都头正杀气凌天,小的哪敢多嘴?就那众高邻,不都噤若寒蝉么?”
“果真如此,我武二就一刀杀了两命,还有一个至亲的性命!”
“一命两命还不都是一样尝命的事?小的只是不想就这么再送了性命。”
武松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了,“要不,你们走吧,不要去县衙了。”
张小四说,“要走,都头去找西门庆时,我们两个早走了,可是我们要与武都头生死在一起。武都头要再有个三长两矮,武家可再不会有续香火的。令兄武大起早贪黑,对那潘金莲百依百顺低三下四,不正也想有个后嗣,延续武家香火?”
武松没有说话。
张小四左右看看,说,“小的早听附近水泊梁山有林冲晁盖聚义,凭武都头功夫,前往入伙还不坐得头把交椅?到时弄个压寨夫人,小的也可娶个媳妇,延续香火。”
“今不是我武二不想活命,只是武二还有事没了结。”
“气出了,人杀了,大郎仇也报得,都头还有什么没了结的?”
武松说,“想我武二哪有杀人动机?只怪那狗官贪赃枉法,逼武二做出这等事来。武二虽死,也要揭发那狗官苟且之事。那史文魁貌似清廉,却在虎骨下藏得一千两雪花白银,这事只我武二知情,武二理当揭发。”
“那,我二人可不陪同都头了!”
“你俩个去吧!先把家里料理一下。武松班房尚有些银两,拿去交家里用。”
已是傍晚,史文魁听得鼓响,慌忙整衣升堂。堂上烛火通明。武松因连杀二命,难以敕免。但知县史文魁念及武松出差东京之功,问武松是否有因防卫误杀,武松说,“西门庆是小的自去寻斗,淫妇潘金莲受诱奸之计杀死武松兄长,却是女流之罪,手无寸铁,武松只一刀结果了性命,并无防卫误伤。”
“本官念你一身武艺,打虎有功,似此,本官却如何保得了你性命?”
武松说,“大人如若有意保全武松,为民作主,前日武松便把兄长骨殖及郓哥、九叔带到公堂作证,大人因何置之不理?如今逼武松弄出事端,却又假心假意,真叫武松鄙视!你这狗官,貌似清廉,却一肚子贪脏祸水,武松几乎被你蒙蔽。今我武松既来投案,断无祈怜之想。武松今日要说的是,你来阳谷不及一年,年奉不足三十两纹银,却何来一千两雪花大银,叫武松送你东京家中?”
“你你你,大胆刁民,竟然污陷朝庭命官!急杖八十在板,收监再审!”
史文魁没有看到武松挨板既已气昏,被衙役扶入后堂。两个持杖衙役哪会对都头真的用力,只虚张声势,草草地数过八十下。
夜间,李师爷探视武松,说及知县大人不计武松气头之言,还有开脱之意。只要武松来日厅堂不再胡言。武松不为所动,把那李师爷骂了个狗血喷头。
李师爷回头把武松的态度转告史文魁,史文魁即按大宋律例,要定武松斩首示众。李师爷进言,“死刑判例均需上报朝庭批复,那武松本已当堂言及大人收有贿银之事,武松秉性刚直,既敢说,势必有证据,也置身死于不顾,倘朝庭派来钦差监审,必牵出诸多事端。以小的看,不如判他终身监禁,再奏请朝庭剌服边陲,这类案例较多,省院不甚得视,不会差人监督,可以万无一失。”
宋朝许多案子,不是当庭审理宣判,都是幕后定下调子,只是当庭宣读早已拟定的文书。
史文魁让李师爷起草判决文案,第二天,一面差人上报东平府,一面升堂再审。史文魁读完判决文书,却有围观百姓齐刷刷跪至厅前,并端上乡绅上户人家凑得的纹银千两,为武松减刑开脱。史文魁扫了一眼呈放在台面一的银子,“本官熟读诗书,一向清廉,既众人有意开脱,本县当再拟表报请州府批示。”
原来武松斗杀西门庆后,一劳永逸地除了阳谷一霸,屡受西门庆欺压的乡绅财主扬眉吐气,奔走相告,一夜之间,自发凑齐千两白银。
东平府府尹陈文昭也是进士出身的文官,是当时少有的为人正直、秉性贤明的一个五品官。在连续接到两份不同判决后,陈文昭即取武松、王婆等到东平府亲自审理。审理得知武松刚强正直,深得百姓喜欢,考虑到附近多地盗贼猖獗,想留武松身边维系地治,只是连杀二命,找不出借口开脱,一边将当地乡绅财主要求开脱武松口辞录文签字,一边将地方需要武艺将士维系治安情况赍一封紧急密书越过省院直禀京师刑部熟识官员,并与史文魁再三商议,做成“因王婆哄诱通奸,迫使本妇潘金莲下药毒死亲夫,而后又要本妇驱逐夫弟武松,不容武松祭祀亲兄,违背人伦情理,至武松怒起,失手伤及人命。王婆拟合凌迟处死。武松系报兄长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淫妇,虽则投案自首,情不当敕,判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服刑三年,视其悔悟表现,或安排差事将功赎罪。其余一应证人,各自回家置业。批文到日,即便施行。”
不及一月,朝庭批复到东平府,武松出得监狱,开了二十二斤铁锁长枷,换一面七斤半铁叶团头围颈枷锁钉上,贴上封条,并于左额刺上一颗金印,发配二千里外孟州牢城。
武松发配之日,正是王婆行刑之时,大街小巷,观者如潮。
武松二月初杀人,坐了二个月牢狱,路上又是二月,走到孟州境内时,已是炎炎火日当天,烁石烫手之夏。
两个东平府的押送公差,因听了府尹授意,一路对武松小心管护,不曾虐待丝毫。武松有乡绅资助银两若干,自是夜突破晓行,遇店喝酒。这天,到一个叫孟州道十字坡,又见得一座酒店,前面一面旗招迎风飘摆,上写“十字坡酒店”。
三人便进去卖酒喝。
刚坐下,后面转进一个妇人,头上黄烘烘插满钗环,鬓边红肜肜贴满野花,上面穿一件绿衣短衫,下面系一条鲜红绢裙,满脸堆笑,张口白齿,“原是三个公人啦!请问要什么酒菜?本家有上好米酒,上好牛肉,要点心时,还有好大牛肉馅玉面馒头。”
公差看武松,“不知都头想要什么?”
武松对那妇人说,“牛肉先切三五斤上来,酒不要问多少,先搬一坛上来便是。如有黄牛肉馒头,也上得一二十个,反正不少你钱!”
那妇人听两公差叫武松“都头”时,眼睛不易觉察地闪亮了一下,这下又听武松点了这么多生意,睃了旁边两个大包裹一眼,应道,“好来好来,酒家这就去,客官且先歇着喝茶。”
武松等了一会,不耐烦走到板壁缝前,贴那板壁朝里看,刚回到座上,就见那妇人一手托一个大酒桶,一手托一只大圆盘,稳稳当当上得堂间。大圆盘里是一推紫红牛肉,二堆山头似的玉面馒头。
二公差叉起牛肉便嚼,武松掰开一只镘头,咬了一口肉馅,吐在地上,又贴着眼睛看,用两个手指牵出里面一根黑色的毛来。武松又瞧一眼妇人,那妇人坐在门前檐荫下纳凉,用手扇风。武松说,“洒家,却如何不见小二来服侍?莫不你就是这酒店主人?”
妇人回转头,“正是。客官有何吩咐?”
“你这妇人家,如何杀得死黄牛来做肉馅?”
“到时自有人帮忙宰杀。”
“也杀黑毛牛么?”
妇人起身进来,“你这客官好生胡说,黑毛猪却见过,哪有黑毛牛?”
武松便把那毛拧到妇人眼睛前面,“那,这是人身上的毛发不成?”
妇人胸有成竹似的,脸不红心不跳,“莫不宰牛时,不小心落下一根头发,却要大惊小怪!要不,这一盘馒头,不收钱了吧!”
“不收钱的馒头,却也吃一个。”一个公差咬了一口,嚼了两下,腮帮不动,伸进嘴里两根指头,抠出月牙似的一小块硬片,对着门口的光,“倒像人的指甲。”
“可不,宰牛时不小心切掉的。反正是送给客官享用的。”妇人想也不想就说。
武松看那妇人把一桶酒水一只手托着来时,就觉这妇人不一般,当时想,这妇人大大咧咧,一点也没什么过意不去的意思,倒是江湖老手!就说,“一个女人家,把持这个大酒店,却不见你男人上来帮助呢!”
“小本生意,男人挑担到村里跑外卖去了。”妇人说,盯着酒桶,“我这里端的上好的米酒,我给三位客官便宜些,要待我那位回家来,可要按规距收费的。
“哦,你男人不在,倒让我等占便宜!”一公差说,就从桶里打出来三碗酒,一人面前摆一碗。武松端起酒碗,眼角睃了眼妇人,妇人赶紧回后面去。两公差一饮而尽,口里叫着,“好酒,好酒!”又去桶里剜酒。武松趁公差剜洒弄出的水响,把手里的酒朝墙脚下一泼,空碗含在口里,碗底朝天,“端的好酒,一路不曾尝过这么好的酒。”
妇人听得声音,转到堂厅,“却不是么!自家酿的。还是酒家给三位倒吧!”一边端起酒桶来。
武松说,“你且放下,我们自己来。”
两个公差,一个又喝下一碗,站起来又要剜,可是没站得直,就蹲在地上,又侧身倒了下去。另一个要扶他,没扶起来,自己趴下了。旁边妇人盯住武松看,武头往左边摆一下,又往右边摆一下,听得那妇人说,“倒也,倒也。”
武松听话地“倒也”了。
“还都头!与老娘斗,嫩了点!”妇人用脚尖掂了掂武松,喊,“兄弟们,有活了,快来干活!”
进来五大三粗两个汉子,一人一个,把两公差扛走。妇人提了下桌前的包裹,又打开公人的缠袋,全是金银,复又系好,喜笑颜开提到里面。出来时,两个汉子正一头一脚搬武松,哪搬得动?一个身体直挺挺在地上,似有千万力气。妇人看了,嘴上不饶人,“你两个狗东西,亏我那厮当你们兄弟,只白养着吃饭,全没些用处!今天好不容易得这三个行货,管着了十天生意,却要老娘亲自动手。那两个松垮肌瘦的,只当水牛肉来卖,这个板结的,身板比我那厮还壮,难怪还是个都头,习武练得精肉板结,这回只当黄牛肉来消化。扛进去后,老娘先自剥了这厮!”说罢,蹲下身来,双手提武松两臂往肩上扛,哪提得动?松了手,解下绿裳绢裙,只穿得兜肚裤衩,吐一口吐味在掌心搓了,胸脯一抖,又捏造住武松两胳膊往上提,先还是提不动,后来是那“倒也”的胳膊腾地一下自己竖起来,按住妇人肩膀,妇人身子一下不能挺拔,变形地弯下来。“倒也”那个又环抱妇人胸脯,妇人张大嘴巴,还没叫出声来,被双腿夹住胯下那块,动弹不得。妇人杀猪那般尖叫着伏倒在地。武松压在了上面。
正在这时,一个挑卖担的壮汉到了酒店门口,见妇人被一个汉子压着,二话不说,歇下担子,抽出扁担,就朝妇人上面的武松劈来。武松本来头向里面,后背朝门,加上妇人尖叫,没听到有扁担劈将来,只听后面运气似的“啊……”了一声,才心里叫着“不好”,往旁边一滚,扁担挨着那妇人的头削到地上,一撮硬梆梆的黑土溅到墙上。汉子一下劈了个空,就那扁担做柱子,撑着身子,整个掀起来,双脚半空中向武松一扫。这一招,武林中叫“悬空扫堂腿”。腿的力气,本来是手的十倍,加上双腿合并和整个身体的重力都聚在腿上,所到之处,没有不山崩地裂的。那腿还没有扫到武松,一阵风就吹得武松项颈一凉。武松正待站立,这时干脆趴下,悬空扫堂腿扫了个空,扁担旋了一圈,那腿又一次扫将来。这回又加了一圈的惯性力度,汉子也已在转圈过程中运足了更大力气,发出“呀……”的一声。武松在刚躲过那一扫堂腿后,正要抓紧机会起身应战,一个鹞子翻身还没完成,躲闪自是来不及了,举起双手隔在胸前。那腿遇着武松双手,就像铁锤撞上岩石一样,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武松往后滑了一尺,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汉子双腿落到下面妇人背上,竹子扁担裂得哗啦一声。妇人本要慢慢地爬起来,被汉子一压,复又趴下,骂声,“压老娘倒有本事!”汉子说声“娘子错怪了”,慌乱滚到一边。妇人撑手一撺,站成弓箭步,双臂一张一合,完成了一个短暂的运力,就朝前面武松冲过来。武松刚站起身,复又后仰了下去,一只脚平行伸在地面上,正当妇人身体冲到脚上面时,武松一提,妇人直接头朝下,脚朝上,越过武松头顶翻了过去。这一招,一般壮汉都会没命,但那妇人落地的并不是后背,而是双脚,竟立成一个马步。武松仰面往后一看,知道遇着了对手,眼角余光里又看到汉子手里,扁担划着破碎的弧线劈来。武松往外侧一滚,扁担又一次劈到地上,这次因为扁担是裂开的,撑不住汉子的体重,汉子啊呀叫了声,俯倾下来。武松一个兔子翻身,一脚尖压在汉子肩膀上,汉子挣了一下,复又趴下。那妇人却一拳朝武松面门砸将下来。武松本欲双手接应,可左手被自己的身子与墙体夹住,只抬起了右手,接不住妇人拳头,相互对击了一下,发出了肉裂的声音。
武松己顾不得手皮是否裂开,这时只想到,在这个逼窄的厅堂,没办法施展拳脚,就在那妇人看着手,并在空中抖动的瞬间,一个弓身,借着汉子肩头的脚一发力,腾空到了门口,一跃,到了外面。
赤日炎炎,眼花燎乱。
汉子在屋里叫了声“休走!”撺了出来。接着,妇人与两个五大三粗的伙计冲将出来。两个伙计各持一把油光闪闪的剥皮刀。
“一顶四!”武松想,“本不再杀生,生却要杀我!武松有何罪过?现在一顶四了。”一跃到了楝树下。树杆上靠着两根公差押送犯人的哨棒。武松操起一根哨棒,一跳,到了场上,舞了一阵少林韦陀棒法,只觉哨棒轻了些。
汉子看了眼手中裂开的竹子扁担,一扔,也跃到楝树下,伸手拿另一根根哨棒,可汉子的手在握住哨棒后站着没动,眼睛盯住地上贴有封条的围颈枷锁。
妇人对一伙计吼,“吃饭的,把刀给老娘!”接过刀就要向武松冲。武松见那妇人弯腰冲得低,加上手中哨棒过轻,正应以打狗棒招势,却听得汉子说,“娘子且慢,先问这厮来路。”
“一个都头,欺压百姓的狗官!”妇人只是冲来,刀到处,棒也到。金属与木料,碰出又清又混的声音。棍来必来,妇人没有退缩,又往前直剌而来。刀来必让,武松闪在一边,脚尖勾住地面,一掬土还没起来,又听那汉子说,“却有一枷锁在这里。”
“莫不是罪配军!该当栽在老娘手里!”妇人更加抖擞精神,杀配军不犯法。
武松抖擞棍棒,“来吧!俺武松单杀邪恶之人!”
汉子问,“好汉,刚才说什么?”
“武松单杀邪恶之人!”
“你是武松?”
“正是。”
“莫不是景阳冈打虎英雄?”
“正是。”
汉子扔下哨棒,三两步到武松跟前,抱拳施礼,“大水冲到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早听我兄长鲁智深说起武松大名,一直无缘相见,今天幸得会面,却是这般开场,张青愧煞!娘子,还不来拜见武都头?”
那妇人听武松姓名,已自把刀垂在胯边,这下手松了,刀落了,自个迎上来施礼,“奴家有眼不识泰山!”
武松一个多月的牢狱,加上一路上煎熬,何曾有这放开手脚打斗的机会?这下一对四,又还是武艺高强之人,正提了棍棒,气运丹田,被眼前两个施礼的男女泄了气,丢下棍棒,抱拳相问,“二位却是为何住了?”
汉子说,“先坐屋里,边吃酒边说。”
屋里那张旧桌子不知什么时候翻了,酒桶也翻了,馒头、牛肉、酒水洒了一地。七手八脚打扫收拾好地下杯盘,搬上来一张新桌子,端上酒肉,男女衣次坐下。武松却不动手。汉子做主人姿态,端起酒碗,“武英雄请喝洒!”
武松在打斗时不及细看汉子模样,在清理堂间时,把汉子暗地打量一番,但见头裹青纱缠巾,上穿白布麻衫,下穿漆黑短裤,腰系红布武师带,脸上颧骨鼓突,嘴边略有胡须,三十左右年纪,虎痛熊腰身躯,不由暗自佩服,这下见汉子举酒过顶来敬,却不应对,说“还不知壮士大名,如何敢喝得这酒。”
汉子笑起来,“倒是忘记介绍。小的姓张名清,这个女人并是小的浑家,因好使拳闹事,打斗不曾输过,江湖上叫母夜叉孙二娘。”
武松说,“失敬失敬,因武松从远方发配而来,路经此地,不曾听说,适才冲撞,还请大嫂原谅。”
妇人说,“怪酒家有眼不识英雄,一时不是,还望兄弟恕罪。”把一只血迹未干的手伸到武松眼前,说,“兄弟也不吃亏,我这娇嫩的手,杀过一都头的,这下被兄弟打得开裂,任何人,酒家都得报仇,今兄弟这仇便不报了,算是陪罪。”
众皆大笑。
酒来筷去,武松问,“武松不曾见过二位,你说的那鲁智深,武松也不曾见过,他却如何说及我姓名来?”
汉子说,“武都头可在柴进庄上呆过?”
“是的,呆过一年有余。”
“那就出得名了。小的姓张名青,原来这十字坡是个寺庙,唤做光明寺,小的在寺院种菜,人家便叫小的菜园子张青。只因为一些小事看不顺,小的性起,把寺僧杀了,放火烧成平地,竟没有官府来问。小的就盖了几间茅房,在这里过活。周边人见小的胆大,送来一些小孩,要我传授武艺。前年有一天,一个老头路过十字坡,指出小的枪棒中许多破绽,小的不服,与他比试,不到二个回合,小的被打倒在地。原来那老头年轻时就是拦路抢劫为生,因吃了官司不敢留宿家中,在外闯荡。那老头原驻孟州城,见小的手脚还算灵便,便带小的去了孟州的家里,授我一些松棒本事,还把这个女儿孙二娘许配给我。谁知官府一个都头,知那老头回家,带了三五十人上门捉拿,小的便与浑家孙二娘与他们打斗,结果小的岳父被那都头捅死,小的夫妻杀了都头等三二十人,才跑到这十字坡开酒店来,官府也没人来过问。虽则开酒店,这乡村野地的,哪多少生意?实指望有过路行人,看得上眼的,蒙汗药来蒙翻,取了包裹财物,把那人肉做成牛肉馒头,赚些外块。小的刚才跑外卖回来,听得浑家叫喊,谁想得到竟是武都头!”
孙二娘先抿嘴笑,这下开口说,“酒家对官府最是痛恨,听二位公人叫你都头,才动了劫财害命的意念。对了,那两公人现在不知如何了?”便下得后房,一会跑将上来,“正待开剥,待会咱三个就用那厮们心肺下酒!”武松说,“岂不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千万使不得。”三两步跑着到后房,见那剥肉凳上,躺着两具油腻腻光滑滑尸体,一个仰面向上,一个后背向上。旁边炉锅子,汤水翻滚,白气蒸升。两伙计正一人一边,用那剥皮刀在头发上磨擦。原来这十字坡酒店,但凡主人在家要取心肺下酒时,便与胸前剖开,怕在后面把肝胆弄碎,苦了胃口。而要做牛肉馅时,便在后面下刀,挖了股腿上精肉。这两个公人,本来都要做成水牛肉馒头,却听张青与武松要一处喝酒,两个开拨的,就把其中一个翻过身来。一个伙计在仰着的公差头发上擦过刀,对着颈下正要下手,听得武松说,“且慢。”回过头来,见张青、孙二娘也跟着到了里面。孙二娘说,“武都头不准杀这二个行货,且放了他们。快调些解药来喂了。”
三人回到桌上坐好。孙二娘又看了武松半天,叹口气说,“真是差点误了大事,结果了都头的性命!只是,武兄弟既是都头,因何又被发配到这孟州来了?”
武松就把自己柴进庄避难、景阳冈打虎和斗杀西门庆诸事细叙了一遍。张青夫妇惊叹不已。那孙二娘还是心有余悸,“刚才武弟进酒店时,项上也不戴得枷锁,额上也不见得金印。我那厮张青吩咐过酒家,三种人不准伤害,其中就有剌配犯人。要不,酒家哪会于酒中下那蒙汗药呀!”
武松撩起额前头发,“你们看,我这还有颗新剌的金印!”
孙二娘凑近看了,心疼地用手指摸了一下鲜红的肉印,“要是看到这剌配金印,也不会下手害你,只怪武都头头发遮拦,差点造成大错!”
张青说,“我说不能害的三种人,一是云行僧游道,二是行院妓女,三是路经此地的流犯配军。武英雄你想,那和尚道士,与世无争,又不受过多享乐,自是杀他不得。行院妓女必是家庭艰难,免强苟活,冲州撞府,不知受多少辱屈,才挣得些卖身的可怜钱,劫她们财,害她们命,不光江湖不耻,自家良心也过不去。流犯配军里更有英雄豪杰,有许多被忌恨陷害的好汉,但凡提不起放不下的,谁来忌恨?又如何当得了配军。这便是小的三个不杀的缘故。可浑家女流之辈,一再误我大事,去年竟差点药翻一个惊天动地的英雄。那英雄原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账前提辖,姓鲁名达,为救卖唱的金老汉父女,三拳打死镇关西,逃走五台山,落发为僧,因脊梁上长有花纹,江湖上都叫他花和尚鲁智深,使一条六十来斤的浑铁禅杖。从此经过时,浑家见他浑身肌肉,便于酒里下得蒙汗药,要做黄牛肉馅馒头。正要开剥,小的卖馒头回来,见那禅杖非同小可,才调下解药救了。那鲁智深不计小的浑家过错,还感念小的救命之恩,与小的结拜兄弟,何等菩萨肚量!近日与杨志占据二龙山珠宝寺,专与官府作对,杀富济贫,倘若做了他,江湖上不是少了个行侠仗义的好汉?可我这浑家虽则有点武艺,到底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教过多少回,不要再害僧人,却在鲁智深兄弟之后,又做了一个僧人性命。”
孙二娘不等丈夫说完,用手击桌,“那云游道僧,断不是酒家有意害他,一怪那厮要在孟州找什么张团练,那个人酒家没听说过,断不是什么义气好汉;二怪那厮对酒家挤眉弄眼,酒家自不理他,他拔出两把戒刀来,场院里跃武扬威。看那手段,酒家自知不是对手,才假意答讪,那僧人以为酒家有意于他,放松诫备,酒家才能酒中下得蒙汗药,翻了那厮。”
众人哈哈笑过一阵,张青接着说,“小的刚回来,见武英雄骑在浑家身上,以为泼皮要行不轨之事,一气之下,冲上前来帮助,没有看到楝树下的押送棒和枷锁,要不哪来这打斗之事?差点又误伤都头。小的再陪不是,请都喝此一碗酒,永不记在心上。”
武松喝下一碗,“英雄不打不相识。”
“既是发配,那两个解押公人,断不是好货色,英雄何故又不准做了他们?”张青夫妇都说。
武松坐正些,说,“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再说那两个公差一路上也不为难武松。”
正说间,二公差和两伙计到得堂间,“都头,喝如此好酒时,也不叫醒我兄弟。”
武松笑,“你二人一路辛苦,睡得香甜,才不忍心搅二位美梦。”
“适才真的做着美梦,在天上飘啊飘啊,遇着王母娘娘,有意招为快婿,正要与那玉皇大帝女儿成亲,又被他俩推醒过来,真是不爽!”
俩伙计笑着抱拳施礼,“还望二位官人恕罪!”
武松在十字坡歇脚三日,张青夫妻酒肉相待自不必说。孙二娘得知武松身世,直把武松当自家兄弟来怜痛。一回酒足饭饱之后,孙二娘要武松演示拳棒,在一边看了,好生惊叹,又问武松,“武头如此高超武艺,断可一下要了奴家性命,因何却要等到张青那厮回来,几个斗你一个?”武松不好意思的样子,想想还是说,“那天嫂嫂去后院给酒下药时,武松已在门缝时看得清楚了,所以没有喝嫂嫂桶里的酒。武松念及一个女人家,操持这么大个店甚为不易,自有生计的难处,不能相帮,已自有愧,哪能伤了女家性命?那会嫂嫂不识得武松,嫂嫂要毒杀武松,那是嫂嫂自有原因的,武松断不可因此就要了嫂嫂的命,所以只想动手教训一下,没有必须杀人的仇恨。”孙二娘听武松言辞真切,两眼顿时湿了,“二娘也是自小命苦,没遇着哥哥这样体谅女人的英雄。家父也曾请先生进门要奴家习学诗文,可就是三从四德、男尊女卑那些调条,奴家一气,不再念书,自要习练武艺。后来遇着张青那厮,总算对奴家有较多依顺,如今在家里也有同等地位,可我那厮在体谅女人上,也不能与都头比的。要是我那厮遇着要毒杀他的,打得赢时,一下还不搠了性命!二娘这条命,也可说是都头给的呢!”又是行礼拜谢。
到第四天,两公差记着交割日期临近,问武松可否早些上路,孙二娘气极,“上什么路?武英雄是酒家兄弟,从今天开始,就是十字坡酒店主人,服什么狗屁剌配刑!且看老娘把那锁枷砸碎!”武松说,“武二深感二位厚待,只是交割日期内不到孟州牢营,官府查来,怕有连累。”张青说,“武英雄如怕连累,不如去那二龙山珠宝寺。我兄弟鲁智深多有书信邀小的上山入伙,也常来饮酒,提及武英雄大名。武英雄在沧州柴进庄离别宋江后,宋江只当都头还要去,每天叨念,那柴进庄上本是江湖豪杰集散场地,武英雄因此江湖有了大名,加上赤拳打虎,更是威震江湖。若去二龙山时,断能做个头领,却不比牢里服刑好了许多?我且写一书信与你赍行。”武松说,“二位好意武松心领了,只是武二在那阳谷县、东平府受百姓关爱,集资为我开脱,才有今天性命。一则武二想在三年刑满之后,回还东平府,报答百姓恩德,二则武松还保存有那贪赃狗官受贿证据,也当回去为民除害,以谢百姓。”
张青夫妇知武松个性刚烈,挽留不住,取出包裹行袋交还,又送十两重大银一锭路上使用。二人送了又送,一直送到孟州道上。
因张青夫妻曾在孟州杀死都头的案子,到孟州境内,不好再送,与武松分手辞别。武松感念张青夫妻款待恩情,与张青行结义之礼,结为兄弟。张青因长武松六岁,武松拜张青为兄长。孙二娘虽小武松一岁,武松还称为嫂嫂,要行跪拜大礼。孙二娘哪里肯受,一把扶起武松,自己反倒弯腰跪拜,“还是我拜武二弟哥哥吧!”泪流满面。张青顺孙二娘性子惯了,依着她,却说,“武英雄是我兄弟,你又是我浑家,当尊你嫂嫂,而你又要拜武都头哥哥,别人听得,却是如何伦理?”孙二娘说,“什么狗屁伦理,老娘就喜欢叫武二……哥哥!”
“你以前说的,只认我张青一个人做哥哥,现在却又多出一个哥哥了!”张青笑着说。
“只怪那时不认得武松哥哥呢!”
孙二娘看着武生好一会,见武松只是低头不语,突然上得前去,扶了扶那项上枷锁,对两公差大喝,“快把枷锁除了!”两公差迟疑着吞吞吐吐,“这不合适吧?”
孙二娘一把反剪起说话公差的手,“什么合适不合适,在这里老娘的话最合适。你两有这狗命,还全赖我武松哥哥心善。解也不解?”
差役唯唯喏喏,“我解我解,却是到大路上,一定还要带上。”
孙二娘说,“那也要等过了快活林酒店,看到孟州城时才轻轻地戴一戴,只做样子,不连累你们。到快活林时,让我哥哥好生喝上一碗,断不许催促。”竟又泪流满面转对武松说,“哥哥这次服刑,怕有的苦受。”突然又转对张青,“在那孟州劳营好像有熟人什么的吧?何不写个信让哥哥带着,也会多受些照应,少受些皮肉之苦。”
这张青一拍脑门,“娘子不提起,我倒想不起来。是有一个熟人在劳营管事,也是我犯事后,解救我的兄弟。虽三五年不见,也不会忘记,今恰好央哥哥带些人情银两酬谢答救之恩。咱快找一个地方借得纸笔,写一封书信与你带上!”
三个人因在十字坡休息过几天,武松不曾带枷锁,一路走得轻巧快当,转两个小弯,看到一个小集市,就集市的十字路口,有一间更高的楼房,门前挂有一面招旗,上面写着“活活林酒店”。正要进去,却见对面吵嚷着过来三五个人,个个身系武士腰带,脚蹬武林步鞋,蓝布短束,手带护腕,先武松他们一步到得酒店门前。其中一个粗壮汉子朝里面大叫,“蒋门神,出来!蒋门神,有种出来过招!”
“蒋某来也!”声音起处,一个身材槐梧,膀阔腰圆的汉子站在了门槛上,把个大门上下顶得结结实实,不留天地。武松想,看来这个人就是蒋门神了。
蒋门神一叉腰,门的两边也不见空隙。
三个刚冲到门前的汉子,不约而同后退了几步。
“你个蒋门神胆大包天,连罗员外千金也敢抢来,莫不吃了豹子胆?我等今天只为带那罗春蕉回转,过去事也不再追究。识趣的,就把员外千金罗春蕉给我们带回去,之后井水不犯河水。”
“蒋某新开的酒店,要有人帮工,又不是不付工钱,你等吵闹,好生无礼!”蒋门神一边说话,一边跨下门槛。
“罗员外家又不是没钱,会把千金放你酒店挣工钱?”后面一个弱高个说。
“你说蒋某抢劫民女,何不去官府告状?”蒋门神说。
“就是告了的,告得通时,还要我等来干什么?”
“告了的,告不通,你等却敢来取闹!”蒋门神本在与来的三个汉子论理时走近三个人跟前,这时一抻手,捏住了粗状汉子的下巴,正往上提,粗壮汉子一声尖叫,双腿离地,朝蒋门神腹前一蹬。武松看得心中一紧,暗想这来的三个人还有点功夫。谁知那蒋门神早有防备,一弓身,另一手往上一兜,兜住了汉子双脚,一提,那壮汉腾空一个斤斗,摔倒在地。另两个汉子一左一右,包抄而上,竟被那蒋门神左右开攻,三拳两脚打翻在地。三个人毕有点本事,起来又斗,结果又都倒在地上。那蒋门神却大气不出,毫发无损,向三个躺在地上的汉子招手,意思像在说,“有本事再上。”
武松动了动身子,要往人群前面冲,却被一个解差拉住,“都头,我等公事在身,赶路要紧。再说这些个人,各说各的理,到底谁占了理,还不甚清楚。看那三个以多欺少,断也不是什么讲道理的。”
武松心想,只是没心情歇下来喝上一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