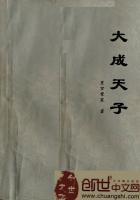西门庆因比武受伤,在家调养,暂不能到副都头任上当班,这给了武松侦查西门庆的时间和机会。武松对捕房事务不是很熟,但在李强一再出谋划策下,一应事务做得又是风生水起。李强疾恶如仇,捕房积下的那些文案,也是李强给武松看的。李强年逾四十,在刑捕房当职差不多二十年,历经四任知县,熟知刑侦程序,上下关系融洽。武松又推存李强做了临时副都头。李强感激不尽,一意协助武松侦查西门庆,一方面为民除害,另一方面也好为自己成为正式副都头扫除障碍。
有些事情,李强出面比武松做起来更为顺便,武松就交李强办理。武松表面做些与查处西门庆无关的事,暗地里还在侦查展招鞋的去向,暗中留意身边人的脸色。
一查,就查出许多事来,原来西门庆还与多种杀人抢夺案有关联,还正在明购暗夺地要收并一家布店。那布店老板说,只因西门庆近日受伤,才没有再来店里找麻烦。布店老板求武松为他作主,扯下一块布料给武松作为酬谢。武松坚辞不受,那店主就泪眼汪汪,“看来武都头也是假意为民作主了!”武松说,“莫非为民作主定要收了百姓东西才行?再说武二这么个大男人,哪穿得这种彩绸!”那店主老板说,“武都头穿不得,你嫂嫂可穿得。”
武松只得收了布料,执意留下银子。
西门庆受伤,蜇伏不动,就像一条鱼伏在草里,网很难捕获。武松得赶在西门庆康复到职前收集证据,一面差人带了开有虎骨的药方,到西药铺卖了腰伤生药,连同生药铺收据、布店老板提供的那份证一齐存在枕头套里,一面叫李强到奚秀英家里,笔录奚秀英丈夫口供。李强为避人耳目,夜间去奚秀英家里,可还没进那木门,被一块从天而降的砖石砸破了脑袋。
武松并不知李强出了事。这天晚上,武松回到紫石街,把一块衣料递到嫂嫂面前。
武松早在哥哥家里住下了。每天吃过晚饭,嫂嫂都烧好热水打到洗脚盆里,把干净暧和的洗换鞋袜放在一边。武松练武跑腿,没有家室,虽然常常鞋袜汗湿,也常十天半月不洗脚,被褥更是三五月难得洗晒,如今衣着干净,每天热水泡脚,睡清爽的被笼,白天精神逾发抖擞,同事羡慕武松。武松说知道这都是嫂嫂服侍的,就把布店老板给的那块布给嫂嫂添置衣裳。
潘金莲显然是等了好久,手在围腰上搓了搓,只顾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叔叔这是干什么?却不折杀奴家了!嫂嫂对叔叔怎么着也是应理该当的。这快布嫂嫂权且收了,二回可不许再做出这种事来。嫂嫂又不是外人,又不是没洗换衣裳,寻常又不出得门去,也没什么难为衣裳的事务。倒是叔叔自己年纪不小,当积攒些钱,作成家的打算。我与你哥正筹划给你讲个亲家,将来武家也该有个续香火的。”
武松听得一惊,差点问出一句哥哥嫂嫂不也能续香火吗?
潘金莲手里捏着布料。那是块上好的料子。潘金莲祖家就是清河县有名的裁缝,自小认得质料的优劣,不用手摸,一眼能看得出来。捏着布料,不由又睨武松一眼。武松只因还没查出一点展招鞋的线索,又想起那两个蒙面人,后悔没有抓住,还在气头上,正喘着粗气,且面色红润。潘金莲看了,牙缝里轻轻吁了口气。
潘金莲自幼学会一手好针线,不几日,量着自己身段,缝成一件冬袄的新外罩。那外套把冬袄一紧,袄里面身段也有了轮廓。潘金莲在梳妆镜前转着身子看,看着看着,喃喃自语,“他丑陋的哥哥对我哪有他这般的关心!我做嫂嫂的自不该有来无还,也当给叔叔置件衣裳过冬。”
潘金莲为武松扯一块布料,取出一件武松的衣棠作样,用手指量着武松衣裳的大小,突然那手指僵住似的半天不动,又把丈夫武大的短衣裳拿来,摆在一边比较,武大的衣裳还不及武松衣裳一半。潘金莲摇头叹息,眼睛湿润,躺在武松的衣裳上面睡着了。
人家说,有滋味的日子如白驹过隙,没滋味的日子度日如年。自武松进得家门,潘金莲既觉得日子白驹过隙,又觉得度日如年。天气冷了下来,雪天也到了。这些天,武松却又不回家来住了。虽然武松不回家来,潘金莲还总是做好饭等他。这天潘金莲早做好饭,温好酒,门口张了好几回,还不见武松身影。武大吃过饭,自上楼歇下,潘金莲还在下面候着。武松刚一进屋,潘金莲就小鸡扑楞翅膀那样迎上去,解下围腰,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地拍打武松身上雪花,眼睛贴住武松耳根,“也不戴顶笠帽呢!,耳朵都冻得红了。”
潘金莲的气息顺着武松耳根下领口入到身上,虽然凉微微的,武松倒感觉痒痒地笑了起来,“嫂嫂,我痒死了。”
潘金莲自知失态,后退一步,注视武松项下那地方,“叔叔还是赶快成个家吧,没个女人照顾哪行!”
武松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潘金莲又说,“就算嫂嫂照顾叔叔,却不能照顾一生世呀。”
潘金莲抬头仰视武松,与平日里低头俯瞰武大相比,竟有扬眉吐气那般惬意。慢慢的,潘金莲心旌摇荡。
“倒忘了,没把火盆端来。”还是潘金莲说。潘金莲牵挂武松,自有女人的细心。天气一冷,窗口看到雪花飘落,想到武松可能受冻挨寒,早升了火盆。武大吃饭时也没有端上来,刚才只顾拍武松身上雪花,没有端出火盆。
从灶间端出火盆,堂间一下暖和。武松被火映得红光满面,逾发有青春可爱的朝气。
潘金莲在对面坐着烤了一会,眼前武松的手伸在火盆上面搓着。那手有都白净,可他兄长武大那手,就是谷树皮!潘金莲也向火盆中间伸了伸手,很快又缩回来,放在膝上。坐着,看着,再也耐不住,就说,“叔叔为何到这时才回家?”
武松说,“县衙管文案的李师爷要拉我去狮子楼喝酒,刚喝两杯,就回来了。”潘金莲说,“还当叔叔有了中意的姑娘呢!却为何只喝两杯又回来了?”
“有个叫西门庆的去了。那酒原来还是西门庆请的。西门庆本来被史大人提做副都头,但他不愿做副都头,却要与我结为兄弟,我先自跑开了。”
“多个朋友多条路。”
“但那西门庆在县衙有许多案子。看样子他没有悔过自新的意思。这种人不可深交。所以就回家来了。”
“这样呀,奴家还以为叔叔想着家里呢!”潘金莲看武松一眼,声音软软地说,“那么,叔叔在那里一定没喝好,不如再喝点酒吧!”
武松想着西门庆为什么不愿做副都头,却又要今天晏请捕房人等的事,从西门庆端杯喝洒的样子看,身体很好,比武那天摔得并不是很重,却又在家调养那么多天,这一想就是没有头绪,也没有听清潘金莲的话。
潘金莲以为武松默许,一边斟酒一边说,“叔叔要是一个人喝酒孤单,奴家可陪叔叔。”
开始各饮各的,武松过意不去,敬了嫂嫂一杯。潘金莲用袖口遮着嘴唇,喝了,给武松斟上,“好事成双,奴家当回敬叔叔一杯。”
武松喝了嫂嫂的敬酒,说,“武二给嫂嫂添忙,日后可从班房派个公差来给嫂嫂做下手。”
潘金莲说,“自家人多自在,添了外人在场,碍手碍脚,有什么好?”此时潘金莲酒热攻心,轻轻拽开领口,颈下酥胸微露,头上云鬟半散,看着武松,目不转睛。
“我还来敬叔叔一杯吧。”
一来二去,四五杯酒落进肚里,春心哄动,潘金莲再也忍耐不住,便端起酒杯绕到武松身后,一手在武松肩胛上一捏,“叔叔要真当嫂嫂是个好人,有这份心,就请饮下此杯。”武松看了下肩上的手指,一时虽不自在,却是不好发着。潘金莲当武松心有所动,想到英雄难过美人关的俗语,又说,“你哥哥已经睡了,他每天三更起床做炊饼,这一睡不到三更不会醒的。只有奴家舍身相陪了。”说着,一干而尽,端杯的手垂下,又放在武松另一只肩胛骨上。
“嫂嫂!”武松叫了一声。
“别叫嫂嫂了,听了别扭。我叫金莲,是你家的金莲。”潘金莲赶紧说,一边把头从武松肩头伸出,再扭过来向着武松看。武松再也忍不住了,一昂身子,软绵绵的潘金莲猛然后退几步,靠在木柱上才没摔倒下。
潘金莲扶那柱子问,“叔叔这是?”
“武二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自小由哥哥养大,不敢做半点对不起哥哥的事来。再说长嫂为娘,武二如对嫂嫂有不轨之心,就是伤风败俗、猪狗不如的禽兽。”
潘金莲脸色由白转红。先前是吓得苍白,后是羞得通红,“奴家为武家传宗接代的大事,刚才酒后吐了真言,想不到叔叔却容不下了!”就唔唔哭着上楼去了。武松感觉自己过份了些,想等潘金莲下楼来,陪个不是,日后也好见面,却没有等到潘金莲下楼,正要回班房,倒是武大穿衣下得楼来,拽住武松,“兄弟这是要去哪里?”
武松说,“回班房里去住!”
武大说,“可不就被你嫂嫂说中了?她刚才就说武二你要赌气回班房,叫我下来劝你。你嫂嫂是有心气的人,拳头上站得住人,胳膊上行得了马,断不是那种树不起的瘪三婆娘!想当年在张财主家做使女时,那财主看她月貌花容心灵手巧,要纳她为妾,她却死活不从。张财主为此要报复她,才要把她送给我这等废人为妻,还不收我一文聘礼钱。武二兄弟,你知道哥哥半个残废的躯体,你嫂嫂哪能打心眼里看得上?能在武家住下,也是哥哥我日夜小心,只许诺她为武家传宗接代,而后便给她休书,任她来去自由。如今兄弟回家来,她再没别的想法,没有走了意思,只求在武家过安宁日子,你倒是这样伤她的心!”
“果真如此倒好,就怕人心隔肚皮,知面不知心。武二就看出嫂嫂有不捡点处。”
“兄弟这话就见外了,你嫂嫂行端坐正,就不说在张财主家守身如玉,就是嫁我为妻之后,清河县多少富家子弟上门来调戏骚扰,哪一个不被她骂得狗血喷头地去了?搬来阳谷县,也是你嫂嫂出的主意。兄弟你想想,她对我这种人称‘三寸钉’的都心无二意,还有哪上面可指责的了?她今天是怕兄弟你受了寒冷,而哥哥我又睡了,才陪你喝酒取暖,那也是心痛你的。我与你嫂嫂来阳谷县,没一个亲人,你嫂嫂正是把兄弟你当亲人才心痛的。她现还在楼上哭,就怕你走后,一则街坊笑我们容不得兄弟你,二则没你在家时,又会有人上门来调戏你嫂嫂也未必。”
武松一脚已跨出屋门,转回身来说,“哥哥,武二虽不曾读得诗文,却也知长嫂如母的道理,就算误会嫂嫂一片好意,也不敢与嫂嫂真的生气。我今天回班房,那是真的有事情,改天再来向嫂嫂陪不是。”说着,一拂手,拐进暗黑的街头。武大没有拉住武松,转到楼上对潘金莲说,“武二由我带大,他就是那种脾气,不会记心上,过两天会来陪娘子不是。”
潘金莲哭着说,“这样便好。奴家自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理,你我只这一个兄弟,特别俺做小生意人家,更当和气生财。就算武家有个传宗接代的子嗣,不余些钱,也会如你我一样,吃尽苦头,可光有钱,没有一个当公差的撑门面,也是要吃苦头,做不得人上人。”
武大唯唯喏喏,“娘子放心,就为武家后代,我明天还会去劝我兄弟!”
潘金莲突然拿起枕边一件大褂子,“你看,我给你兄弟做的衣裳,这冷的天,竟忘记给他。明天你就带给他去。”
武松一连几天没到紫石街来,潘金莲每天叫武大劝说,武大每天回家转告明天会搬回来住。这种话说得多了,武大不好意思再说,就说兄弟是真的忙,早晚会回家来。
潘金莲在家算着,整整五天,武松没有回得家来了。
这五天里,武松一直都在为找寻展招鞋的下落忙活,那些忙活,起始看视有功,实质毫无意义。比如他到奚秀英家,要问奚秀英丈夫伤势如何,伤势越重,越能说明卖假虎骨的危害。但那男人虽然坐不起身子,口词却清楚,“好多了,都头,那药原来真的有效果!我们不能冤枉了好人!”
武松就觉得许多线索无从延续,不如再回到从前,翻出别的状子,从别处找突破口,可他拉开抽屉,那些积压的诉状里,西门庆的状子一份都没有了。
事情明白得可笑,但却查无实据,到第五天,武松找到知县史文魁,把布店老板的口供及奚秀英原来控告西门生药铺贩卖假虎骨的状子等一并交了,又说了诉状不翼而飞的事。那史文魁在宅子里并不戴乌纱帽,一抬手,手便落到头发上。史文魅摸着头发,慢条斯理地开口,“本官饱读诗书,一举考中进士,候了三年,因朝中无人,才来这阳谷县。虽距家千里之外,也自想为民作主,造福一方,也因此,才爱惜人才。虽你我非亲非故,也有意推举你,就是要做出安扶百姓的功绩。可武都头至今也不能拿出让本县信得过的业绩来。就凭这几张纸,要法办一个人,说出去不惹人笑话?本县并不怪罪于你,只怪这地方顽疾深固。如今武都头为那西门卖假虎骨的事,倒让本官想起你打死的那只老虎的虎骨,摆在这里尚不放心,打算送回东京家眷,为日后升迁之用,只是路途遥远,盗贼猖獗,苦于尚无体己人护送。你身为都头,可有良策?”
武松正为许多事烦躁,正想出去清理一下,说,“如大人信得过在下,武松当效犬马之劳!”
史文魁说,“武都头本领过人,本县自是放心,只是此为苦差,要得三五十天才能回转,这其间又有新年,还怕你家兄嫂不允呢!”
武松说,“在下受大人抬爱,当以大人事务为主,一来家里事烦,二来小人不曾去过东京,也可借此去京赏灯呢!”
史文魁说,“那么武都头可挑选四五个随从,尽早起程便是。”
武松安排停当,即回班房取了些银两,叫当班的买了些洒肉果品,到紫石街哥哥家里与哥哥告别。潘金莲早在楼上听到动静,楼梯口探见武松把一些酒肉果品放在桌子上,心想,原来他也与我一样余情不断,到底不是无情汉!重又缩回房间,重施胭脂粉面,再整头顶云鬟,换上艳丽的衣着,下得楼来说,“叔叔一路可要小心了!早去早回!”
武松抱拳恭身,“谢过嫂嫂。”
当时北宋内忧外患,落草为寇、拦路打劫的何止千万。武松带三四个随从护送虎骨到千里之外的东京,遇着的艰险自不必说,都因武松武艺高强,化险为夷。阳谷县知府家属打开封条验收财物时,武松看到里面不光有虎骨,原来还有一千两雪花白银,暗自吃惊。史文魁到阳谷当差还不到一年!那史文魁家属笑逐颜开,要留武松多待些日子,武松心中不平,连赏灯的心情也没有了,急着办了交割文书,回到阳谷县。前后正好两个月时间。武松把交割文书呈给知县,知县史文魁赏给武松一锭大银。当天下午,武松去布店,用赏赐的那锭大银给扯了红绿两种颜色的绸缎,就往紫石街来。
武松推了一下,门关着,武松想,嫂嫂果然贤慧,大白天插着门在家里。就叫,“嫂嫂开门,武二回来了!”叫了好几声,那门还不开,武松门口等着,同时左顾右盼,希望哥哥挑着担子回来。
可是,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武松又不耐烦,就贴近门缝往里看,这一看,竟看到堂间两盏琉璃灯,灯的那边有一块牌位,灯火映着上面的字:“亡夫武大郎之位”。
武松吸了一口凉气,难道是我眼花了?一用力,那门两面边分开,素色灵床堵在了眼前。
“嫂嫂,嫂嫂!这是怎么一回事?”
“奴家这就来了。”潘金莲在楼上应了一声,又过了一会,一身缟素下得楼来。还在楼梯上时,先就嗬嗬哭出声来,“叔叔总算回家了啊嗬嗬。”
武松并不知道刚才潘金莲还在楼上与西门庆同床取乐,听到叫门的声音,西门庆慌忙从后窗跳楼而去。潘金莲寻找孝服,清洗脸面脸面上脂粉后才下得楼来。
武松见潘金莲哭得伤心,劝道,“嫂嫂别再哭了,生死由命。只是武二不知哥哥死前得的什么病?”
潘金莲哭着说,“自从叔叔走后不过十多天,你哥因思念你,患了心疼病症。求医问药,什么法都想过,就是不见好转。”
武松说,“武松从没听说哥哥患过什么心疼病。”
潘金莲说,“叔叔说得极是,奴家也觉蹊跷。”
正说间,隔壁开茶馆的王婆进得门来,说“都头且安身要紧。岂不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死不得复生,倒是活人要紧。”
武松问潘金莲,“哥哥埋在哪里?”
潘金莲说,“我们才来这阳谷县,我又一女流之辈,到哪找坟地去?没奈何,停尸三天,抬出去火化了。这还幸得王干娘帮助做成的。”
武松问,“哥哥死了几天了?”
潘金莲说,“还有两天就过七了。”
“嫂嫂节哀顺变!”武松说,扭头就走,手里的红绿绸缎早掉地上,脚踩到软绵绵的东西才低头看了一下。
潘金莲也看到那两块布,哭得更响。
武松在班房脱下公差服,换了一身素净衣裳,叫上一个随从,到阴事店扯了块麻绦系在腰间,顺带办了香烛、冥纸、米面、椒料等,当晚回到家里,在灵前铺设酒肴,点亮烛火,跪在灵前拜了三拜,说,“哥哥阴魂不远,若是负屈含冤,还望显灵示我,武二当替哥哥报仇雪恨!如若患病无治而终,武二当尽心照顾嫂嫂日后生活!”
武松就在灵床前睡下,可是哪睡得着?三更时分,灵床前琉璃灯半明半灭,昏暗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响,“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坐起来,寻思那声音来源,似梦非梦。
天色渐明,潘金莲下楼烧水,武松洗漱后,问,“哥哥到底因何而死,昨夜托梦给我,说死得冤枉。”
潘金莲说,“昨天不是与叔叔说了吗?这么快就忘了?心疼病死的。”
“谁买的棺材?又是哪些人抬出去火化的?”
潘金莲说,“还不是街上那一班管阴事的人?团头是一个叫何九叔的。”
武松说,“我先去衙里画卯,画好立即就来。武二当为哥哥守孝三日。”
武松哪有心情画什么卯,径到何九叔家里。何九叔见到武松,变得手忙脚乱,开始似有顾虑,后见武松诚恳,才回房间取出两块酥黑骨头,一锭十两纹银,说“我就猜得都头要来,才留下这老大证见。”
武松问,“团头说老大证见,什么意思?”
何九叔说,“在下本来全然不知你兄长武大死因,但正月二十日那天,开茶馆的王婆央小人殓武大尸首,路上却见西门庆大官人约我去酒店吃酒。当时我纳闷,西门大官人何时看得起我?又不敢不从。吃酒时,西门大官人给了我这锭银子,嘱小人‘此次所殓尸首,凡事遮盖些’。西门庆这个人,在阳谷县的势力,都头也是知道的,小的不敢不答应,只在火化时,趁人不注意,收藏了这两块骨头,要为武都头留下证见。因小的在殓尸时看到令兄七窍里有於血,齿唇上有牙痕,明显是中毒身亡。这骨头是酥黑的,就是生前中毒的见证。”
武松说,“我也觉兄长死得蹊跷,只不知因何而中毒?我在衙门呆了些时日,知道凡事得有个来龙去脉才是。”
何九叔说,“这张包骨头的纸上,写着殓尸日期和送葬人的姓名,他们应当知道一些事端。不过小的听到过一些口风,不知实不实。”
武松问,“什么口风?”
何九叔说,“说来也是武都头家门不幸,都说令嫂潘金莲与那西门大官人有奸情。有个卖梨的郓哥,还与令兄到王婆茶馆捉奸,与王婆撕扭起来。满街的人都这么说。”
武松说,“何团头此话可不能乱说,我嫂嫂是有心气的人,拳头上站得住人,胳膊上行得了马,断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浪婆娘!
“听说,只是听说。”何团头有些惧怕了。
“那烦请团头带我去找那郓哥问一问行吗?”
在卖梨的郓哥那里,武松了解到,正月十三那天,郓哥要找西门大官人卖梨,听说西门大官人在王婆酒楼与潘金莲私会。郓哥就与武大商定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四日那天去促奸。那西门大官人一脚把武大踢倒了,过了三五天,武大死了。
武松听得咬牙切齿,对那郓哥挥动拳头,说。“要是冤枉我嫂嫂,武松拳头可不认得你!”见郓哥吓得发抖,又说,“如你所言属实,便该写成文字并画押,与何九叔一道去县衙大厅。”
知县史文魁见是武松告状,想及武松刚为自己押送金银的功劳,又是当班都头,十分重视,加上人证物证俱在,即令衙役传西门大官人及茶肆王婆到堂审问。因武松属当事人,理当不宜参与揖拿。当班衙役一行去不多时,转回禀报那王婆及西门大官人都不在家,知县便叫师爷制作辑拿文告张贴。李师爷在升堂时还伫立一边,这下却不见人。知县正要发怒,却见李师爷正从后面进厅堂里来,对史知县耳语几句,知县点了点头,对武松等说,“上告人武松,你身为本县都头,理应知晓法度。你所告西门庆与你嫂嫂通奸之事,目前尚无证据证实。”
武松说,“大人,在下武松刚才递交的不是证据吗?”
史知县扶一扶乌纱帽,“古人道‘捉奸捉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你那哥哥尸首在哪儿?尸首才是最有力证据。但凡人命关天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齐全。第一件便是尸首。再说,你又不曾亲见他们两个的苟且行径?单凭这两个老小挑唆,你就要与那西门庆做对头,恐有不明事理之处。是不是那西门庆曾与你争过都头之职,还恨在心,因此栽赃陷害?”
武松本跪着的,这下站起来,“武松承大人抬举、开导,已在这都头职上侦案多起,已知何为证据。也因此,才带来若干物证及目击证人口供,也叫来来个人证、以便当堂对质。大人如何说尚无证据的话来?”
史文魁嘴唇半张半闭,半晌,一拍惊堂木,“大胆武松,竟然质问本官来了!今天是你审案,还是本官审案?”
“既然大人不与小的作主,那小的只好自己解决了。请大人且把那二根骨头,十两银子和那张纸条还给武松。”。
史知县说,“这个,既然交到本县,本县当妥为存放,从长计议。待有详实证据,便与你捉拿所告之人。”
原来,西门庆是阳谷一霸,自不会把外来的武松放在眼里,要给武松一个下马威。那天比武失利,他只当试探武松的功力,其实自己伤得不重,也不在乎什么都头不都头的公差,受人指使,要不早就在武松来阳谷县前,使银子成为都头了。能成为地方一霸,也自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勾结。武松一应行踪,都在其掌握之中。得知武松有意查办他,就欲除之而后快。武松出差京城,本是史文魁淡化武松与地方矛盾的一着棋,新官上任三把火,武松拖得长了,自会对一些事情睁一眼闭一眼,自会领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为官规则,不想却被西门庆利用上。西门庆抓住这个时机,在武松住的紫石街查看地形,好为自己日后亲自铲除武松。那天他大摇大摆走在街上,却被潘金莲的窗帘杆打到头上。原来那潘金莲自武松走后,每天开窗盼望,时间越长,开窗越急,这回听到声音,以为武松回来,一看不是武松,失望地松了手,手杆才掉了下来。西门庆发现武松有这么个貌若天仙的嫂嫂,伙同隔壁开茶馆的王婆,设计诱骗潘金莲出来,于王婆茶肆做成苟且之事。本来只为报复一下武松,没想到一来二去,竟喜欢上潘金莲,又想做长久夫妻,正好自家开有生药铺,有砒霜,就唆使潘金莲毒死武大。这回听得武松当庭告状,西门庆从后面入得县衙,将银子交给史文魁管家,管家又叫师爷去后面说了。知县史文魁听李师爷说西门庆送来银两及数目,办案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
从知县史文魁转变态度上,武松便知这史文魁不是值得敬仰之人,就想上告东平府。可那史文魁连证据也不给了,若去东平府上告,可就一点口实也没有。
武松情知不能以“文”的方式为哥哥申冤,带三个随从到街上办置了砚台、笔默、纸张和猪头、鹅、鸭、果类等祭祀供品,来到紫石街家中。这时潘金莲已知武松状告不准,没有怕武松的意思,反恨武松告她,把那两块红绿绸缎还给武松,“奴家哪配武都头破费!”武松没理会那红绿绸缎,只说,“因明天是兄长满七的日子,兄长去世时武二不在家,众邻及街坊出了不少力,武二当以今日祭祀兄长,顺便办酒席以谢众邻。”
武松留一个随从在家做酒席菜肴,让另两个随从分头传唤了开银店的姚文卿、开阴事铺的赵钟铭、卖冷酒的胡正卿、开茶馆的王婆、王婆隔壁卖面食的张公。自己专一买来两柱大佛香,在灵床前点着,烧纸钱、摆祭祀酒果、跪拜。
客人加上潘金莲共六人。武松让六个人围席坐定后,亲自给六人斟上酒,开口说,“今天武二请众位到此,一来武二不在家里,兄长死时众人帮助料理许多事务,武二身为兄长生前唯一的亲人,当备薄酒略表谢意,二来武二现已查明,兄长武大死得蹊跷,在座各位都是知情的人,今天当众位面,武二要问明此事。胡正卿曾于县衙为官,能写得一手好字,相烦做个记录。”就腰间拨拔出一把刀,竖在桌面上,一手拿住潘金莲,一手指着王婆,“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众人休要惊慌。武二今天就要王婆老猪狗与这淫妇对质,说清楚我哥哥被害至死的事情。待会众位只烦做个见证人,做纸签名,却无他事。”
潘金莲早已浑身酥软,只因武松提住领口才没有瘫下去。此时垂帘看着武松,双眼泪下,战战兢兢招供自己如何陷入王婆与西门庆设计的圈套,被西门庆勾搭成奸并用砒霜毒死丈夫武大的事。王婆见潘金莲招认,抵赖不过,也招认了。武松让二人在记录纸上画了字,又让众人都签上名,叫一个随从点燃纸钱,把潘金莲提到哥哥灵床前,“我哥哥慈悲能忍,最有佛缘,今却惨死恶人淫念之下!武松再不开戒,更待何时?”只一刀,剌入潘金莲胸前。
潘金莲软软地瘫痪倒下,挣扎着抬了抬头,喉管滑动,泪脸上挤出一丝解脱似的笑来。武松拨那胸口尖刀时,听到那喉管处呻唤着“叔叔……”却没理会,转过身来,见众人战战兢兢,没一个敢出声的,说,“武二本不想杀人,只要为兄长申冤,谁知告官这条路走不通,今日才自作主张。这女人暂且留在这里,只等武松去取了那个人的头来,再割了她,祭祀哥哥。众高邻休要惊慌,武二去寻那头颅就来。”
武松交待两随从把好门,矮个子随从即到后门站立,高个水随从随武到前门口,在武松出门后插上门闩。武松径自找到西门庆生药铺。西门庆不在,生药铺主管害怕武松威严,如实说出西门庆刚才与一个相识去狮子楼喝酒去了。
狮子楼是阳谷县最大的酒楼,两层,各有一个大厅,若干小间。武松识得布局,直奔二楼,在一个窗口探见西门庆后脑勺,对面是县衙的李师爷,两边各立有一个卖唱的粉头。武松撩开门帘,穿过两张酒席,直奔里间西门庆那张桌子,还没近到桌子旁边,外边人群骚乱起来,西门庆看到武松,叫了声“啊呀!”身子一吸,上到后面凳子上,一只脚跨上窗台,伸头往窗外一看了一下,缩了回来,心里正慌,说时迟,那时快,武松奔到跟前,手指轻轻一摁桌子,突地一下站在桌子上,杯盘全部滑落了下来,叮当作响。两个唱歌的粉头早没了声音,这下趁着混乱,与那些吃酒的客人跑出大厅,李师爷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大酒厅里摆有八张桌子,现在除了武松与西门庆,没有一个人。武松没想到桌面上油滑,双脚落在桌子上,便提起一脚要踢窗台上西门庆,身体往后一斜,那只在抬面上的脚板在油腻的作用下向前一滑,而这时,西庆因无路可逃,一不着二不休,于窗台上向武松飞来一脚。武松因为要滑倒,手在空中花着,同时用起了醉拳招势,准备将身体重心下移至脚板上,见西门庆一脚飞了来,又改变主意,就势抓住那只脚,站稳身子,又因为要抓住那只脚,手掌一摊,刀落了下来。西门庆脸上笑了一下,心想打虎英雄原来不过如此,原来徒有虚名!比武那天摔倒,本是跃得太急而已,并不曾受到他的攻击。便不再惧怕武松,借着窗台的硬度,一纵身,向武松来了个金猫扑鼠。武松脚下的桌子本来摇摇晃晃,这回一下散架了。
台子是被西门庆身体压散的。西门庆金猫扑鼠到跟前,武松来了个顺手牵羊,西门庆趴到台面上。台子散架时,武松落地站着,西门庆趴下了。武松抬起一只脚要跺西门庆,西门庆打了个滚,一个鲤鱼打挺站立起来,手里捏着武松掉下的尖刀,朝武松胸前一搠。
西门庆原来有一身好拳脚,在武松到阳谷县前,便是阳谷武艺最高的人,否则也难成为地方一霸。西门庆有意勾引潘金莲,找那开茶馆的王婆商议成全好事时,那王婆就说,“那潘金莲可是阎罗爷的嫂子,别弄出事端,吃不了兜着走。”西门庆说,“我西门大官人也不是吃素的吧?”王婆想想也是,才有胆量做拉皮条的马泊六。西门庆养着十多个家丁庄客,妻妾有正室一个,偏房六个,以前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只是今日,为酬谢李师爷,也为不让更多人知道有贿赂官府的勾当,没带家丁庄客,又已知武松告官不准,以为没甚事了,放松了警惕,没有带护身器械,所以刚才见武松提刀冲来,心中便虚,这下刀到了自己手里,面对赤手空拳的武松,自是毫无怯意的样子。武松盯着那把尖刀,在尖刀剌近胸口一二寸距离时,往旁边一闪,那尖刀剌进武松的都头袍,西门庆手因用力过大,也与刀子一起钻进了武松外袍,一时没有拔出来。武松人高马大,抬起手肘,就在西门庆后背上击了一下。西门庆哎呀一声,赴倒在地,只因有一只手还在武松腰间袍子里挂着,又没有完全赴倒,就用下面那只手要搬武松的脚,哪里搬得动?倒是武松自己往后一仰,另一只脚伸到西门庆腹下那地方,往上一提,西门庆就像鹞子翻身般飞落到门口最外边那张桌子上,又与桌上杯盘一起落到木阁板上。武松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低头看了下剌破的袍子,抖出缠在里面的尖刀,再看西门庆时,西门庆也靠墙壁站了起来,手里一条板凳上下翻飞。
武松没有像进来时那样急着冲上去,一则地板上无疑很油滑了,二则也想过一下拳脚的瘾,今日总算有个机会。对手没有刀械,武松也把刀别进腰间鞘里,捋起衣袖,用丁子步向西门庆逼近。
西门庆在门口那地方最有机会逃跑,但他舞了会板凳花,发现自己身体并没损伤,这下见武松赤手空拳,更不想跑。当然,作为有头有脸的地方一霸,被人打跑,以后又如何顶脸皮呢?而且,通过武松在桌上站立不稳的架势上看,也不像是真有功夫的人,更有一点壮着胆量的是,如果今天杀了武松,他有能力摆平官司,不至抵命。西门庆见武松脚步移动慢,更以为武松也是心里怯了,反倒等不及,在武松还有四五尺时,把手里板凳砸了过来。西门庆没有想到,武松居然一只手把板凳当头接住,笔直地竖立起来。西门庆手上没有一物,突然身子发软了,就朝门口奔。而武松已接近门口,只贴地一滑,就堵在了门前。
“都头,有事好商量,只管开条件。”
“还我哥哥命来!”
“只要不是这个条件,我都会答应。”西门庆想说,但来不及说出来一个字,眼前一黑,钵子般拳头闪到了面门。西门庆脸上挨了一下,但脚还能跑,就往里面跑,又跑到原来那个窗台上。
西门庆是自己跳下去的。他家里有那么多家丁庄客,只要叫上一两个家丁,摆平武松不会太难。西门庆只想快点跳下去叫人,刚落到街上,还没爬起来,武松也落到跟前。西门庆翻眼看着武松落成马步桩姿势,自己干跪不动了。
武松持刀的手在向前伸时犹豫了一下,板紧的口中还是挤出话来,“武松本不想杀人,只因我哥哥被害,你这罪人不自省悟,还结官同恶。虽武松意在修行,也不由己!此为除淫恶也!举头三尺,神明自清。”说着,左手拽住西门庆头发,右膀手起刀落,那头就提在了手里,举过头顶,“大家看,似此也为苍生吗?”
武松回到紫石街时,潘金莲身子已经硬了,脸上已无血色。武松割下潘金莲头来,把两颗人头供在灵床前,说,“哥哥阴魂不远,早日投生吧!,武二等哥哥,一道去那清净世界!武二今天是第一回杀人,只为报仇除淫,往今往后,武二再不杀人,就连这作奸王婆,也不杀她,任由官府作主去了。”
遂提王婆,与众高邻一起往县衙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