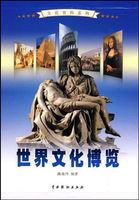豪华的建筑物后面,是一大片绿油油的大草地,占地面积非常广,足足有十分之一的京城那么大。
这里曾经是贵族马场,现在依然维持以前的风格,不过不再是贵族式,而是贵宾式,当会员很简单,有钱有权有关系,即可。
马场最著名的就是那面七彩湖泊,也不知什么原因,一到晚上,这湖泊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变色,绚丽多彩,非常好看。马场的主人便在湖泊上建一家西餐厅,只有会员才能进去消费。
程灵没有想到,席时澈会带她来这个地方,这个对他来说可以说是侮辱的地方。
“你......”
程灵停下脚步,她狐疑地盯着席时澈,不知他是什么意思。
席时澈感受到身后的程灵站着不走,他侧头看去,面容冷峻,“同个地方,拒绝我两次?”
他目光冷冽,像冰冷的北风横扫而过,程灵只觉冷飕飕的,席时澈不给她任何说话的机会,霸道地强拉着她直接走进去。
再次走进这个餐厅,回到当初那个座位,程灵却没了曾经的任性和洒脱。
两年前,她能任性无情地拒绝席时澈的追求,甚至带着唐雨泽一起给他发好人卡,可现在,她只能坐在这个位置上,扮演着她从来没有想过的角色。
程灵侧头看着外面的风景,好让大自然把她心底的苦闷给吹散。
这个西餐厅是由特殊玻璃建成,在里面可以看到外面的光景,感受不到视线上的隔阂,而在外面是绝对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拥有绝对的私密。
而程灵所在的位置,更是整个西餐厅最好的,能全方位把周围的环境收入眼内。
绿色,代表生机,她从小就喜欢绿色,望着一大片的绿色草地,紧绷的神经也有所放松。
虽然这里所带给她的回忆不太好,不过环境真的很棒,程灵看着看着也都入迷了。
若不是看到那抹刺眼的身影,也许,这顿饭,她能吃得下去。
坐在楼下露天厅的那一对俊男美女异常的吸引人,最让人瞩目的不是他们的外貌,而是男人对女人的宠溺,那似乎要把人沉溺在其中的宠溺眼神,那么的熟悉,那么的刺眼。
程灵黑眸里闪过一丝愤怒,她早就已经决定忘记他,为什么还要让她看这些?
是警告她,还是讽刺她?
程灵终于知道席时澈带她到这里来的目的,不就是想告诉她,当初的她,有多么的眼瞎,多么的无能和可怜。
“席时澈,这样玩,有意思?”
她能容忍他调侃她,调戏她,却不能容忍他讽刺她的付出。
为了母亲,她一次次地把身上的刺给隐藏起来,尽管这样会伤着自己。
“怎么,终于知道自己当初有眼无珠,惹羞成怒?还是嫉妒了?”
席时澈嘴角噙着浅笑,目光阴鸷,像狠辣的魔鬼,一步一步撕开她的胸膛,想要看清楚她的心。
席时澈的话,太过尖锐,程灵本来情绪就不太在状态,听他这么一说,她的冷静也消失了。
“席时澈,何必说得那么难听呢,你自己安的什么心,别以为我不知道,带我到这里,不就是想让我看到他们,没错,他们恶心,你也好不了哪里去。”
“你......”
“是,我收了你钱,是你的玩物,你可以随意使唤,任意还耍,可是,像你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懂什么叫付出和尊重?我承认,当初爱错人了,可不代表你能看不起我的付出。”
程灵大声吼着,胸膛起伏不定,呼吸更是有点不顺畅,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唐雨泽和那个女人,她的情绪就很不稳定。
她没有想过与席时澈说那么狠的话,毕竟她早就学会了审时度势,话一说出口,程灵也后悔了。
席时澈脸色煞白,黑眸带着猩红,犹如漫天火海,震慑力十足。
此时,服务员不知道室内的气氛尖锐得如同绷紧的气球,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爆开。
“先生女士您们好,新西兰西冷,请慢用。”
服务员正准备把菜放下,倏然,席时澈大手一挥,服务员连用碟子一起掉落在地上。
席时澈一个眼光都没有投过去,他的眼神阴鸷,直勾勾地盯着程灵,似乎要看穿她的灵魂。程灵不仅有些胆怯,她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阴森的席时澈。
“程灵,好口才,我还真小看了你。”
席时澈强忍着掐死她的怒火,随手握起一把餐刀,程灵看着阳光照射金属的亮光,她连忙双手自卫的捂住脸。
呯的一声,餐刀碰撞在玻璃墙上,应声掉在底下。
席时澈倏然站起身,盯着她的目光森冷,如同嗜血的魔鬼,没有一丝的情感,“你还是不懂。”
程灵看着暴怒的席时澈转身毫不留情地离开,只丢下她一人在原地。
这种再次被丢弃的感觉,使她的心渐渐变得麻木,跌落在地上的服务员可是被吓到了,他见席时澈离开,才敢爬起身。
“小姐,你没事吧?”
程灵独自坐回座位上,侧头看着玻璃窗,不知道在看什么,他总觉得,她是在伤心。
她看着席时澈渐行渐远,直到最后,再也看不到他的背影。
“小姐,你的菜现在能上了吗?”
他不知道怎么哄这个女人开心,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使她转移一下视线吧。
底下的湖泊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便便变色,此时,变得一片漆黑,它并没有给人带来脏水的错觉,甚至让人觉得,越发的深邃迷人。
“不了,你们这里不适合我。”
每次来都没有好事,程灵再也不想到这个地方了,那怕它盛名在外。
程灵整理一下衣襟,缓缓站了起来,没有半点的留恋,挺直腰板,坚定地走出房间。
“小姐不如再坐一下,很快,湖泊最漂亮的时刻要到了。”
那神秘极具魅力的黑色深潭,不是每次都能看到的。
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程灵的身影就已经消失不见了,显然是没有听他的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