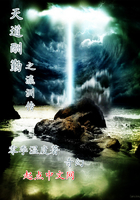冯知恩说什么也要送我们一起回去,说把青蕊留在他家这么多天,就这样回去他不放心,也不好给伯父伯母一个交代。我们离开的那天青蕊依然没有大好,但是烧彻底退了。四人去了机场,我和冯知恩搀扶在青蕊两边,与远岸告别。
在飞机上,每离家进一步,青蕊的状态便好一些,到后来她都主动要喝水吃东西。看着她脸上渐渐恢复的光彩我和冯知恩终于安下心来。
这次回来,青蕊想给她爸妈一个惊喜,我也就没跟家里说要回来。挤上公交返回市区,到站后,青蕊看着路边的煎饼果子摊就不走了,非吃不可。冯知恩好说歹说,告诉她街边小吃细菌满布很不卫生,感冒刚好些抵抗力还没那么强,吃了又会不舒服。青蕊就是不听,守在那里一派歪理邪说:“知道我为什么生病吗?就是太过思念家乡的这点儿细菌了!”不仅自己吃,还非要让冯知恩也吃一个。
煎饼摊主看阵势也忙说她的东西很干净,都是卫生部门检验过的而且自己在饿的时候也吃,不然不会堂而皇之摆在街上卖,竟然还指责冯知恩不舍得花三五块钱给女朋友吃个果子。然后一边用油滋滋的手从同样沾着油且脏的钱袋里捏出同样脏黑的零钱找给青蕊。这老板可真是睁眼儿把瞎话说得跟铁证如山似的,然后动作麻溜地做好一个果子就塞进青蕊手里。
我在一边看得头皮发麻,一边发麻还一边暗自发誓,以后饿死也在街边摊瞎吃了。我连忙劝青蕊让她也别吃了,青蕊像没听见似的接过那堆还冒着热气的食物,准备放在嘴里。一旁的冯知恩怎能眼睁睁看着青蕊把这等赃物吃进肚里,装作无意的样子故意一个急转身,把青蕊已经拿到手里的热腾腾的而且是加了两颗鸡蛋的煎饼果子碰掉在地上。青蕊气得当场发怒,朝冯知恩大吼。冯知恩只是满脸赔笑说真是不小心,路太挤,东西太多,一转身难免就会碰掉。
“你就是故意的!”青蕊气呼呼地甩下一句话后又气呼呼地迈着大步离开。
到了青蕊家的小区时,冯知恩突然有些紧张了,他不停地深呼吸,而青蕊则是活蹦乱跳自顾自走在前面谁也不理,看样子她是彻底好了。我问冯知恩是不是有些紧张,他只管摇头,直至见到叶爸叶妈后,他涨红的脸彻底出卖了他。
叶爸叶妈见我们回来很是高兴,看我们带回来的各种礼物假装生气地怪我们乱花钱。他们对待冯知恩更是客气,尤其是干妈,看小伙儿这样精神又懂礼貌,还把女儿亲自护送回来完璧归赵,她老人家满是乐不思蜀的样子。
两天后,冯知恩看青蕊是完全康复才彻底放心,准备张罗着回家,车票是我带他一起去买的。这两天以来,青蕊都一直因为那个被冯知恩故意碰掉在地上的煎饼果子赌气。要是在叶爸叶妈跟前,对冯知恩还算客气,可私下里却一句话也不跟他说。估计冯知恩这两天在青蕊家没少受她的气,他对她察言观色生怕再做错点儿什么,一看到青蕊脸色一变,就赔礼道歉百般体贴,却还是换来青蕊冷脸一张。她好不容易能开口跟他说句话还阴阳怪气的。
我私下问青蕊至于这样吗?她委屈的理由一大堆:他不考虑她当时的感受,不尊重她的意愿,不在乎她的心情等等。总而言之以小见大,说冯知恩这个人太过自我,觉着自己的才是最终正确的,大男子主义死搬教条。我继续问那所以呢?青蕊支支吾吾,最后说,哪来那么多‘所以’!
我由衷替冯知恩抱不平,觉得青蕊在这件事情上有些不可理喻。怎么病了一场整个人变得这么极端?
就这样冯知恩被青蕊冷落了两天,两天后他搭乘火车离开这里。冯知恩临走时青蕊甚至都没去送他。我死拉硬拽她就是不肯下床,干妈都看不下去说,怎么好好的也不送送远道而来的朋友呢?她推说是不舒服懒得动弹。冯知恩拉着我说别勉强她了。我看出他涨红的脸上满是尴尬。行!不理她了,我送你!随即我拉着他转身离开。
冯知恩一路无话,我除了可以确定他绝对很难过之外,便再也不知道他还想些什么,更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只有心里恨青蕊如此不懂事,替冯知恩憋了一肚子的火。出租车很快到了车站,我把他送到候车大厅,冯知恩向我道谢,我跟他说别往心里去,然后他就像受了天大似的委屈那样忽然抱住我,口中说着谢谢和再见向我告别。
我回身只走了几步路,却感觉走了好远。我依然在冯知恩难过沮丧又凄楚的视野之中。忽听得他在身后大喊:“我全都是为她好!回去好好劝劝她!”我听到他最后几个字哽咽于喉,说着变了音。他强忍着自己的情绪都能让人听出他重重的哭腔,到最后,他应该还是哭了吧。
我不忍心看他悲伤的样子就没回头,背对他狠狠点了点头,然后跑出大厅。我永远都不知道他在说完那句话后是立马转身背对着我,或是期待我回头给他一个肯定的眼神,抑或迅速消失在面无表情的人潮之里。那一刻,我觉得周身的陌生人都像是这个世界的玩偶。也包括我们自己。被感情左右但无力控制,对别人更是无力干涉。
七月下旬。
几乎每天都闷在热浪里。窗外一片片浓郁的绿色也遮不住夏日阳光的肆虐。不知为什么这次回来青蕊性情大变,忽然间成了清心寡欲的宅女,不愿出门逛街,不愿来我家,甚至都不愿到游泳馆,只是每天蜷在家里。我电话约她,她总用天气太热怕中暑怕晒黑之类的话来搪塞。我只好时时到她家里找她。
从我家到青蕊家搭乘公交只有两站的路程。在公交上我总习惯于坐在靠窗的位置,透过不太干净的玻璃向外张望。
这个夏天,类似的裙摆太多,类似的蕾丝花边太多,类似的颜色太多,类似的装扮太多,而类似的美女却太少。在这个三线的小城市里,一旦流行起什么,太多人都跟风而上。今夏,从十四五的少女到三十四五的少妇,几乎都是齐刘海加烟花烫的发型;大片大片或深或浅或正或偏的西瓜绿韩版无腰裙,在热浪滚滚的大街上横行,在领口或裙摆处缀着白色的蕾丝边。看起来就像从同一家商铺购买的。
自从那日冯知恩离开后,青蕊对他绝口不提,好像从来没有跟这个人相处过一样。只有我一说到冯知恩这三个字时,她才火冒三丈地数落人家,或狠狠地说句“你少提他”。我急赤白脸地也骂了她若干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也劝了若干次,可到最后她只是任由我在一旁费尽口舌,然后她自顾自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懒得搭理我。可只要不提冯知恩,她怎样都好,又是跟我下棋又是叫我唱歌看电影的,跟我开任何有伤或无伤大雅的玩笑,或者主动给我做刨冰奶昔水果沙拉什么的,全然展现出一幅真正叶青蕊本来的样子。
我上网的时候问冯知恩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冯知恩很无辜地说他该做也都做到了,给她打过几百个电话,传来的不是此用户已关机就是正忙,估计是把他设成拒接了;于是又给她发了若干条短信,摆事实讲道理的好话说了一箩筐,自我检讨也写了估计有几篇论文的字数,可就是一丁点儿回音也没有。
冯知恩在每次向我叙述的过程中都加深一层苦闷和无奈,我找不到安慰他的方法,青蕊对他要么绝口不提要么百般抗拒的样子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到最后,我只好如实对冯知恩讲,我也不知道青蕊究竟是怎么了,突然变得执拗而乖戾,让人无法进入她的内心,不知道她究竟在想些什么。
跟青蕊一起长大,从没见过她在一件事情上这么偏激。她到底是怎么了?连我都没看透。有段时间我总在想,她是在逃避什么还是真的已经对冯知恩没了感觉?怎么一贯大方直率的叶青蕊从嘉兴回来变得如此异常。在我没到嘉兴之前,冯知恩是不是做了什么伤害她的事?抑或她一个人在冯家的时候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可想起冯家全家老小热情善良的样子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连续几个晚上,一到睡觉就会不由地想去分析这些事,却总也没有结果。作为青蕊从小到大的姐妹,我居然开始猜不透她了,也辜负了冯知恩临走时托付在我身上的希望。我开始失眠,坐在显示屏前,或者戴着耳机把音量调到最高,聆听各种音乐,或者什么都不干,对着聊天软件上寥寥无几的在线好友发呆,心里有一堆话不知向谁诉说。
那时正逢江远岸参加一个大学生创业的培训班,我就没舍得打搅他。那个培训是全封闭的,且学费昂贵,据说请到的都是国内的专业讲师和培训教练,为期一周。远岸每天的课程都紧紧巴巴,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从心理到身体都要进行所谓专业的训练。在所有培训结束后,主办单位还要很负责任地对学员进行考核评估,对成绩优异者的奖励是退还学费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奖金。尽管远岸每天都会抽空给我短信和电话,但明显不能长篇大论了。
有天旁晚,冯知恩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真的真的筋疲力尽了,都快二十多天了,不就是个煎饼吗?怎么叶青蕊就是揪着不放。我悄悄问他是不是除了这件事外还有什么事得罪青蕊了,冯知恩突然在电话那头勃然大怒:“他大爷的!叶青蕊以前的洒脱率性都是装的吧?天大的事她都能一笑而过怎么为一破煎饼就这么折磨人!要是这样,谁爱跟她好跟她好谁乐意热脸贴她的冷屁股就赶紧贴!老子我不伺候了!”
当时青蕊就坐在我身边,她一边大把大把地抓着曲奇饼干往嘴里送,一边乐不可支地看着电视里一部名叫“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动画片,她笑得天真无邪的样子,就像动画里那几只天真无邪的羊。
冯知恩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最后一句他让我捎带给青蕊的话:从此以后他们两不相干。再然后他就气呼呼地挂了电话。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七夕情人节。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却也只能不动声色,但这种话我该怎么跟青蕊说。我像她那样抓起一大把饼干塞进嘴里。冯知恩的话虽是很糙,但也是近半个多月来,无端遭受青蕊给他的冷暴力致使他产生的猜测压抑无奈痛苦等各种阴暗情绪的爆发。这一爆发,或许他跟青蕊就真的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