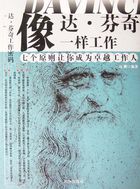我又点了一根烟,赵春祥伸手示意给他一根,我把火柴给他,他把烟点着。
苏子艺从厨房端出一碗粥放在我面前嘱咐着:“好像不是太烫。”
便回去给自己盛了一碗。
三个人,相对无言,吃着有些凉的菜。
苏:“粥不是太热了,趁热吃。”
我:“好。”我喝了一口,有点烫,便又和赵春祥碰了一杯。
苏子艺看着我们吞云吐雾笑着说道:“你要是把小说里的所有烟都换成薄荷糖就好了。”
赵笑道:“你可真会出主意。”
我也笑道:“改了应该挺清新的,虽然某些句子不通顺。”
酒虽然度数很低,却已经有一点点犯晕了,也可能是烟抽的有点猛了。
苏子艺说道:“要不然我帮你分析分析文艺启示录吧。”
我:“好啊。”
赵起身又去柜子拿出一瓶。
苏一边吃着粥,一边唔哝着念着文艺启示录:“序,温馨提示,一,本书……有毒。这个序写的挺个性的,肯定没有人这样写序。”
赵和我碰着酒杯没有说话。
苏:“腊月……之处。这个开头算是诗吗?”
我:“嗯。”
苏:“开年之初……”
我:“不用全念吧,我都记得,你说哪儿到哪儿就行。”
苏:“好。从开年之初到高考结束,我感觉要是能把你写给叶子的信也写出来就好了。”
我:“我写的时候想过写出来,但是感觉太私密了,最后想想还是算了。”
苏子艺说着话已经把粥喝完了,赵起身自己去厨房盛了一碗。
苏:“关于栖息,你以前说过是以我跟赵小伙我们俩为原型写的,写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只有首尾,我也想看看中间过程,赵小伙,你想看看不?”
赵:“想。”
我喝着粥说着:“太难写了,之前写过一个不是这么简洁的,你们俩提供的信息太少,我写着太费劲。”
苏:“那就把我俩去掉呗?”
我:“不行,要是把栖息部分去掉,就引不出后面的后文艺启示录了。”
赵:“那你的重点是写后文艺启示录喽?”
我:“嗯。”
赵:“那你怎么不直接写后文启示录?”
我:“我直接写没人看,没有文艺启示录别人怎么明白加个后是什么意思。”
苏:“那冯卡卡的原型是谁?”
我笑笑,没有说话。
苏:“你笑而不语是什么意思?是你自己?”
我:“有一点点自己的影子,也有他的影子。”我用下巴示意地指向赵春祥。
赵:“我是牧暢玄,怎么又成冯卡卡了?”
我:“你是牧暢玄,但你心中有个冯卡卡。”
赵:“那我心中就有个小石头?”
我:“滚。”
苏:“怎么了?不是吗?”
我:“小石头是一个意象,代表文艺的一个缩影,是后文艺启示录的引子。”
赵:“什么意思?完全听不懂。”
苏:“就是,小石头是谁?”
我:“虚构人物。”
苏:“切,真没意思。”
苏又看了看后面几页,我和赵春祥已经把粥喝完。赵春祥把酒倒在自己碗里,一瓶倒了一半,又把另一瓶剩下的倒了倒。
把新开的这瓶,瓶口停在我的碗的碗口问我:“行不?”
我:“倒吧。”
我递给他一根烟,给自己一根,划着火柴,给他点上,也给自己点上。
苏:“往后看,好像你已经没什么可写了,但是整篇文章都没有说到中心上,既没有说到文艺,也没有说到启示。”
赵:“那你说说,什么是文艺?什么又是启示?”
苏:“至少来说,应该把历史上的文艺人物列举一下吧。然后说说时代背景,再说说文艺的缘由。像启示应该说一说对当时时代人民群众的影响,再说说对自己的影响。”
赵:“里面都说了,苏小艺的文艺启示录跟论文似的,你现在这个思路不就是写论文吗?”
苏:“好吧,还是植物先生想的比较多,连我会什么想都想到了。”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写,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感觉文艺这个词现在挺流行的。”
赵:“以前也流行。”
我:“对,所以就感觉得写一本关于文艺的书,又不知道写啥,干脆写个文艺启示录,因为市场上也好像没有文艺启示录。”
苏:“那你为什么要以小说的形式写?为啥不一篇一篇地写?”
我:“散文式的?”
苏:“嗯。”
我:“我不擅长写散文。”我想了一下又说:“好吧,我也不擅长写小说,但我感觉现在的小说都太规范了,没有风格,没有奇葩的小说。”
苏:“你就比较奇葩。”
我:“所以我写这个奇葩的文艺启示录。”
苏:“你说的对。”
赵:“来来来,别只顾着说,来喝酒。”
他一口气喝下半碗。
我也只好猛喝几口。
五一了,冯流畅(冯卡卡原型)突然打来电话,说是酒酿好了,让我过去尝尝。
可我不知道他家怎么走。
他说可以叫赵春祥一起,赵春祥知道路。
天气很好,云很少,有一些风,风有点儿凉。
乡村间的一切,都很清晰,远处的树,绿得新鲜,绿得柔和,没有刚新生的稚嫩,没有夏绿的刚烈。散落在麦田里的树,充满了幸福。被包裹的村庄,不被所见,麦子开出的花,让空气有一些柔软,纷飞的杨柳絮,在绿幕里闪着阳光的爱。
未曾去过的,总会给人感觉遥远。
一路上,不曾出现一朵花,很是奇怪,在甚好的阳光中的花应该极其养眼,可此刻,不能养眼。
还好,在走在土路的时候,看到一大片向日葵,我试着文艺起来,可,没能够。我只是想到了混沌武士和那个画向日葵的梵高。奇葩的动画,奇葩的配乐。对我来说,原因在于,比较其他动画及配乐,是奇葩。有些许文艺腔调,而内在精神,可能有文艺真情吧。
去到他家,不见他人在哪,绕着房子找了一圈,还是没有见到,怎么办?喊。我和赵春祥大声喊着他的名字,苏子艺也加入其中,一转身,见他从低洼的水塘里爬上来。一手钉耙,一手玻璃罐儿,样子有些滑稽,但眼神却气定神闲无比。奇怪的是,他的衣服非常干净,听赵春祥说,他是一个人住在这老家旧屋,应该很邋遢才对啊。
我原以为,他可能会着古装或者那种盘扣装,有些许古风,一出场仙风道骨。
Shit,并没有。
“走吧,一起钓鱼去吧?”
赵和我:“钓鱼?”
赵:“不是喝酒吗?”
冯:“得有下酒菜不是?时间尚早,钓些鱼,傍晚喝酒,才有滋味。”
我:“好吧。”
去到院子里,一株硕大的樱桃树,极其刺眼,红绿相间,红果子,黄果子,点缀在绿叶之间,石榴树也开着火红的花,也显得暗淡。一树樱花,只为他一人开,是不是就成了真实?慵懒的柿子树绿得倒还鲜艳,挣扎的无花果树,试着争这最后的春色,为夏天夺冠。
他收拾着鱼竿,两杆工业竿,一杆手工竿,也算不得手工竿,只是是那种很久很久以前的接竿,每节一米半左右,大致七五节,叫不上来名字的那种竹子制成。
收拾好鱼竿、鱼网、水桶、鱼线、鱼漂儿我们几个就出发,他说是不远,也没法骑车,全是青草土路,有坑。
四个人,前前后后。苏子艺拍着照片。我并不知道他和赵春祥如此交好。道路很熟。
远处的村庄,叫不上来的安静。我们四个人穿过一个村子,眼前猛然开阔起来,太阳不甚缱绻。道路渐渐下坡,有些许柔和,不像那一段平坦,有坑。一路下坡,看见了河岸,看见了河,看见了船。
苏子艺很开心,赵春祥很高兴,冯卡卡很愉快。我本心事重重,顿然觉得,如此采风也是极好,便释然,脸上有了些许笑意。
也懒得去想那天雨夜喝醉,吻了苏子艺,打了赵春祥,回去的路上把车子摔得稀烂。
苏子艺拍着风景,拍着赵春祥,拍着我们三个,拍着河岸……
我们三个坐下来,撑开鱼竿,系好鱼线,试好鱼浮儿,挂好蚯蚓,钓起鱼来。
我:“你怎么不用撒网或者虚笼、地笼、迷魂阵什么的?”
赵:“那多没意思。”
冯:“那不是享受时光的东西。”
半天,鱼都不曾咬过钩。
我有些许不耐烦,让他们看着竿儿,我到河岸上抽根烟。
一个人,抽着烟。看他们盯着水中的鱼漂儿,看着远方的村落,太阳晒得我有些燥热,风却吹去了燥热,青草和麦花的香味让抽的烟变成了恶味,抽起来极难受。
东方的旧砖窑红砖烟囱在阳光中泛着古朴的红,如今的砖窑已不出一块青砖青瓦红砖红瓦,只是保持沉静,看四周村落的时光变迁。
对岸,被水削得垂直,立壁上,顽强地生长着野豆角,蜂鸟嗡嗡地吸着野蔷薇的花蜜,野枸杞枝条泛着淡绿的白。
苏子艺坐下来,把着我的鱼竿,问着他们钓鱼的秘诀。
我在想,牧暢玄是否是羡慕冯卡卡的,才要写冯卡卡的那些意识洪流,而我似乎有些羡慕牧暢玄,走过了山山水水,亲吻过大海。
《平凡之路》的歌词浮在了我的脑海。可对我来说,我不曾看过山河大海,也不曾穿过人山人海,我不曾坠入无边黑暗,我也不曾毁掉我的一切。我想做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人,可无奈资质有限,只剩痴傻。
我想做那个诗人想成为的艺术家却成了哲学家的平凡人,可赵春祥说,一杯开水叫平常,一杯开水加冰不叫平凡。
我试着想冯卡卡的一杯开水加冰,那后文启示录。
苏子艺大叫着我的名字,说是鱼咬钩了。
我跑过去,拉住鱼竿,手感确实有些沉。
把鱼拉近水面,我以为是黄刺鱼,却是一条鲶鱼,我想起了英国的一个垂钓者写的一本关于垂钓的书,大概叫《钓客清话》,又好像不是。遛了半天,才把鱼拉上岸来。
只顾了鱼,无人顾遐的白鹭,远处的芦苇,水中的田螺、蛤蜊、青虾、海虾、小螃蟹会不会因此而落寞,或是庆幸。
我本以为,只我与冯卡卡一起垂钓,吃吃辣条,聊聊天,让他给我一些关于《文艺启示录》的意见或者建议。
如此这般,也就算了。
就是给了意见我也记不住,我甚至记不住过去六千七百八十九天中的任何一天。
我不知道冯卡卡是怎么平静下来的,
绝不是找到了无聊的终极解决之道这么简单,我该假设我就是冯卡卡,可一切都变得困难,我不知道他说的生活的基本元素是什么。
我不知道无聊的解决之道。
我不知道一生必须做的一百件事有哪些。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讨厌那一百件事。
还是说他讨厌规则,讨厌教条,讨厌被局限,讨厌说教,讨厌被说教。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主义,也不知道他说的分类方法,也不知道怎么用时间线来规范,我甚至恍惚地以为他所说的什么是纠结已不是常人的纠结,更无从谈起他所说的纠结。
哲学家的分类方法又极其陌生,我并不认识几个哲学家。
看着波光中的鱼浮儿,我的眼睛好痛,我想休息一下。
我得躺在麦田边的草地上,理一理这一切,我想起一本叫《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书,我不想做一个守望者,我曾经想做一个守望者,我不想做一个守望者是因为我看了《等待戈多》。无尽的等待,是虚妄的,只是无聊,可是不守望麦田,又有谁来守望,指望稻草人吗?去年的稻草人早就烧了火。
我在想真正的冯卡卡,而不是如今的这个冯流畅,冯卡卡还有很多话没有说。
我试着想他会说些什么。
一只蝴蝶从眼前飞过。
我想起曾经在犀牛故事看的一篇叫《虚实》的短篇文章,我发现了它的另一个名字《我在精神病院住院的日子》。
我想起故事里面那个吃蝴蝶翅膀的女孩儿。
我想起有个叫柯福的作家,又好像叫福柯,又好像叫柯艾略,他研究了人类的疯癫,又好像研究了人类的文明。
算了,不想他了。
冯卡卡的后文启示录还有好多问题呢,问赵春祥是没有用的,他不是真的牧暢玄,而冯流畅也不是真的冯卡卡。
我想编造,编造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事,关于一杯开水加冰。
刚才想到哪了?对了,哲学家的分类方法,好像也只有两种分类方法吧,一个是以哲学家分,一个是以哲学流派分。《大哲学家》和《西方哲学史》就是这样分的。
脑仁儿有些疼。
我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一切之外的事呢?
比如说,百科的正确打开方式。
反十二星座作死原则。
穷作N则。
文学。
艺术。
死法大全。
作死秘籍。
各种流行病,而不是真的疾病,只是矫情人矫情出来的虚构的病。
统观法则的运用方法。
有条不紊?井井有条?严肃认真?拒绝混乱?不接受按部就班?
我们所在乎的,曾经,现在,以后。所坚持的?
活着为了什么?还是只是活着?
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隐居七律。
瓦尔登湖的账目示例。
工作的本质,房子的本质,出行的本质。
闲散的趣味。
闭着眼,一片橘红,我有些困倦了,不想动。
我想起枯树边的那两个等待戈多的老人,猛然觉得,他们是不是已经死了的,后来的绳子因为雨打风吹而腐朽才断的。幸运儿是因为唱了歌才成了哑巴,波卓是因为看见了那两个老家伙才瞎的,送口信的孩子,好像根本没有去过,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记忆,而是他们在前一天的无聊中幻想了给戈多送信的小孩儿,而戈多根本不存在,大家都说他是上帝,因为godot是他的名字,那岂不是就是说,god not to。而上帝的存在本来就是无稽之谈罢了。
我开始厌倦了。
厌倦这一切了。
我的记忆完全靠不住了,我讨厌记忆。不行,我得去洗把脸,让自己清醒清醒。
我试着坐起来,才发现,那羊在嚼着我的鞋带,我骂了那羊一句,它就跑了。
我看向河边,河岸坐着一个人,怎么穿着我的衣服?吓我一跳,怎么是我自己?我吓得胆战心惊,整个河谷,安静得可怕,虽然有虫鸣,有鸟叫,还有那呼呼的风。
我走过去,他笑着说:“你看,已经钓了很多鱼了。”
我看看水桶,果然有半桶了。
我怯怯地问:“你是谁?”
他说:“你睡傻了吗?我是刺荨麻啊。”
吓得我踉跄后退几步,肝胆俱裂。
“那我是谁?”
他:“你说什么胡话?你是冯卡卡啊。”
我大惊失色:“你胡说,我不是冯卡卡。”
他:“你不是冯卡卡,难道我是冯卡卡吗?”
我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