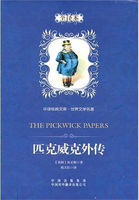山童心下骇然,心道坏了莫不是鬼搭肩,当下却又不敢立即回头去看。道上有云,若是在晚上独自一人走夜路遇到鬼搭肩,可千忌不能直接回过头来看,因为一扭头,这另一侧脖子上的劲动脉顿时就暴露无遗,那恶鬼只要找准了这一空档狠狠地咬下一口,即便是大罗金仙也救不回来。
想到这,山童只得佯装咒骂道,“他 奶奶的,这风灯的火也忒小了点”,一只手假意去摸口袋里的火折子,随即便翻到了那袋中一面铜镜。心道,这枚铜镜相传乃是无生老母下凡渡人时手持的玄黄宝镜,是历代教主秘传至宝,专克这阴厉邪祟,此间定叫尔等原形毕露。如此,将那古镜猛地一掏,立即朝自己身后照了去。
谁知这一照,竟顿时将他自己惊得是冷汗直下,脚步顿时放慢了。借着那隐约的灯盏,山童在泛着水银浸的铜镜中依稀可辨,那竟是一张紧绷到狰狞的老脸,一张扭曲得让人发蹙的脸,那脸不是别人,正是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长老的脸。那平日里本是慈祥的脸上青筋暴起,目仍在眦尽裂地瞪向前方,不断痛苦地抽搐着,似乎幽暗之中正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死命撕扯着,直将那苍老的五官恶狠狠地拧成一团。
山童大骇道,“长老,您这怎么了?”
却见那扭曲到不行的脸上僵直木讷,只是嘴角动了动,仿佛想要努力说出点什么,可就是无法说出来,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前面山童见状,也顾不得逃跑,赶忙矮生将起放了下来,就发现那老头全身肌肉都在不住抽搐,僵得像块木头似的,像极了先前在洞内发现的那个叫大壮的伙计。山童心下一沉,坏了,难不成这长老不知为何,竟也同之前进来的兄弟一样着了哪门子的道。细细查探周身,却并没有发现这老人家有任何伤痕或是淤青,只是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那洞壁,径自颤抖着。
山童觉得有些古怪,当即顺着老人的目光望去,便看到那硕大如斗的阴阳猫脸横眉瞪眼舞动着黑白相间的祭袍,直望得浑身都不自在。心道,莫不是那画壁上可憎的猫脸怪物搞的鬼,听闻巫越之地曾有一上古巫贤,尝以蛊虫之血,聚巫邪绘于画壁之上,方使得这蛊画摄人魂魄,观者即死。莫非此等壁画,也竟然还有这等能耐。想罢,便直接用手将那老头大瞪着的双眼一蒙,另一只手在其人中穴死死掐了下去。
少顷,老头悠悠醒转,气若游丝道,“看来是老朽大意了,方才老夫无意间瞧见璧画上那舞动的黑白道袍,似乎里面在蕴含着九宫变幻的玄机。细看之下,这才辨认出,那其间竟暗藏着奇门遁甲之中失传已久的摄幻之术。待老夫反应过来,却已是深陷囹圄,双眼饶已无法移开,欲想喊出来,怎奈舌根已麻,四肢抽搐也不听使唤了。”
“画摄之术?这是何解?”山童这时来了兴趣。
长老猛地一阵咳嗽,脸上的肌肉缓解了不少,这才缓缓说道,“相传奇门遁甲本是九天玄女所著天书中的一部分,西王母为助黄帝打破蚩尤便,将其盗出秘传于黄帝,创立之初便有四千零九十六局,而后黄帝的宰相风后为防后世子孙窥得天机而遭天谴,竟将其删减成一千零八十局,传至商末姜尚手里只看懂七十二局,而到了秦末黄石老人传于张良的仅剩十八局,传到今日却早已是真真假假,残缺不全。而今,后人只得在众多古籍中窥得只言片语,据传其中一局便记载着这画摄之术。据闻,这画摄之术便是以画为媒介,魅惑人心。譬如,忽见一巨物掷向自己,人便会反射性自顾地闭眼抱头,这便是简单的暗示操控。想来这岩壁上画着这诸多舞动的巫鬼,便是依按此理排列,让人一看之下,身子便失去掌控,全身痉挛,最终僵死原地。”
“此等布局之人好生歹毒,竟故意设个陋局麻痹我等,而后再伺机下杀手!”山童愤愤啐了一口,道,“这么说来,之前的兄弟多半竟是惨死在这等妖魅之下”,说完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拍脑袋道,“难不成,是我误解了,之前那伙计濒死前说于我的,竟是这等意思,‘不要跑着看画’!坏了,若是都有兄弟像我们这般,岂非全着了此道不成!”
想到这,山童连忙再次背起了长老,道“不成,得在他们出事前赶过去阻止才行!”
正待这时,却听洞窟后面轰隆隆的水声撼天震响,一阵阴寒的狂风呼啸地刮来,雾气霎时便被吹淡了不少,空气中的湿气反而愈发浓重,山童还没来得及反应,脚下被什么东西哗啦啦猛地一推险些便要摔倒,紧接着脚下一凉,一股刺寒的水流一时间,竟末到脚根。
“不好,河水已经淹到洞口了!”后面的长老颤颤巍巍地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