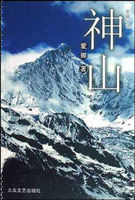一
德孝茶旅庄的伙计丁四儿,这些天来忙得像猴儿似的。自从旷继勋时常来茶堂子里喝茶,孝泉镇上的人,常到德孝茶旅庄来喝茶的老茶客自不必说了,还增加了好多新茶客。孝泉镇的头面人物——镇公所的刘团总,也来茶堂子给旷连长捧场。自然也带来了为刘团总捧场的众多茶客。今天早晨,赵先生又开始接着讲《安安送——米》……
“上回说到太白星君要马喝庞三春前头那桶水,她心里很不愿意。许久,终于……三春同意把前面那只桶里的水给马喝了。太白星君点头暗自赞道:果然是个好心的孝子媳妇啊。于是,太白星君在路边折了根柳枝,迎风一晃,变成一根闪闪发光的金鞭递给三春,嘱咐她说:“你回去后,将这根鞭子插在水缸里。缸里的水用少了,提提鞭子,水就满了。再不用费这么大劲,走这么远的路去担水了。”说完,太白金星就翻身上马,转眼间马儿便跑得无影无踪了。
“三春自从得到太白星君赠鞭以后,就不再去临江河里担水了。缸里的水少了,把鞭子一提,水就又满了一缸。庞三春每天就在家伺奉婆婆。过了几天,姜母觉得有些不对劲了,怎么没见三春去担水呢?她把这事跟秋姑谈了。嘿,秋姑正愁找不到机会说庞三春的坏话呢!她见四下无人,就贴着姜母的耳朵边,说三春行为不端,那水一定是野男人担回来的。姜母听了,顿时气得浑身发抖,用手捶着床说:‘气死我了,我们姜家容不得这样的妇人,我不喝她野男人担的水。’姜母气冲冲地进到厨房里,摸到水缸里的水果然又是满的。姜母早已气不打一处来,摸起一块大石头,一下子把水缸砸得粉碎,并追问三春是哪个男人帮她担水?三春含着眼泪把事情说了遍。姜母认为是庞三春编故事来骗她的,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姜母就更加生气了。姜母又一把抓过鞭子,折成五节朝屋外甩去。霎那间,风起云涌,雨来了,霹雳也响了,五节断鞭变成了五条金龙,在风雨霹雳中腾空而去。后来,观音菩萨怕这五条龙危害人间,就把它们压在一口井内,这就是今天的“藏龙井。”
“再说,水缸被姜母打破以后,等到龙去天晴,却见那地方流出了五股清凉的泉水,这就是今天的‘五股泉’。还有人说,这是三春的眼泪化成的,所以叫它孝泉。姜母还不甘罢休,逼着儿子姜诗休妻。姜诗听了母亲的话,信以为真,一张休书,把三春赶出了家门。
“三春手执一张休书,觉得天旋地转,分不清东西南北,想着如此被休,怎么有脸回去见爹娘呢,不如投江图个清白罢。三春这番心事,却被邻家嫂子看在眼里,赶忙上去,一把拉住三春说:‘你要死也容易,可这黑锅没丢啊!你生前背了不算,死后也脱不得身。再说,你这么死了,安安咋办?还是忍着点吧!’三春听了,觉得有理。可眼下这情形,谁肯收留她呢?邻姑嫂子说:‘那不要紧,白依庵的庵主为人很好,你就去她那儿先住着吧!’
“三春在白依庵住下后,越想越冤枉。长吁短叹,一天到晚总是哭啊,哭啊!最后她想,光哭有啥子用呢?总得想些办法呀!而且,寄居在庵主这儿,说什么也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啊。庞氏是个勤快人,就背了背篓,到芦林里捡些柴火。可在林子里前思后想,她就又忍不住哭起来了。因为哭得太久,眼睛里都哭出血来了,‘嘀嘀嗒嗒’地落在了芦根上。那泪珠,红滢滢圆滚滚的,把芦苇都染红了。三春捡了柴,庵里留了一些,再拿一些去卖。还有她晚上熬夜做出来的线活儿,也都拿到街上换得钱,买些米,几条鱼,托邻姑嫂子给送到家里去。
“三春一走,姜诗家里可就麻烦了。姜母年纪大了,行动不便,眼睛又不好,姜诗自己以前家务事全没做过。怨不得三春走后,老是惦念着家里呢。姜母吃着三春的鱼。虽然,邻姑嫂子一口说是她自己的。可姜母也晓得,你哪能经常送啊!一定是三春这个媳妇送来的。可是,她心头的气还没消呀,仍旧不让提三春回来的事。有人说得好,开金口的时候还没到呢。
“三春被休了,安安可想妈了。闭上眼,梦里梦到和妈在一块,就哈哈地笑。睁开眼,不见妈的影子,就呜呜地哭。邻姑嫂子看见了,知道安安想妈,看这孩子怪可怜的,就偷偷地把庞氏呆的地方告诉了安安。安安从小跟着妈、跟着爸,孝顺、懂事儿,晓得这事不能对奶奶说,他想去看妈,又觉得妈苦、妈累。他要给妈妈带米去,让妈妈吃顿饱饭,再让妈妈看看安安这个好儿子,妈妈好宽宽心。
“安安去塾馆念书,每天都要带学米到塾馆里蒸饭吃。安安在上学途中,路过土地庙,就抓上一把米,磕个头,藏在土地爷爷背后。说也怪,安安藏的米鸟儿不吃、虫儿不咬、耗子不敢动。好像那些飞虫鸟兽,全知道安安是个孝子,都被他这个孝子感动了似的。安安每天少吃一把米,也觉得饿呵,可他怕让奶奶知道了就不能送米给妈妈了。安安看米存得不少了,就偷偷地往白依庵看妈妈。庞三春无意间见了安安,又惊又喜——儿子是娘的心头肉。这么多天了,哪有不想他的?安安就把米掏出来让庞氏看,三春见了,以为是安安偷的,十分生气,脸色一沉说:‘安安,咱们是正经人家,可不兴偷人家的东西。妈宁可饿死,也不能让你学坏。快,给人家送回去。’安安见妈忽然不高兴了,吓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庵主在旁把安安带来的米捏撮出来,仔细捻开了瞧瞧,对三春说:“你可别冤枉了孩子,你看这米,颜色深浅不一,有陈有新,肯定不是偷的,你问清楚再说。”三春一想也是,就问安安米是哪儿来的。安安一五一十地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三春听了,悲喜交集。高兴的是有了这么一个好孩子。可是,看到安安瘦了,心里一酸,眼泪下来了,她把安安抱住大哭了一场。
“这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三春又到芦林捡柴。林子里好静,只有芦苇‘唰唰唰’地响着。好像在说:‘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回去呢!’三春捡啊捡啊,好不容易捡满了背篓。正要回去,忽然看见前面路上走来一位先生……”
赵先生的评书讲得十分闹热,但对于丁四儿来说只是劳累。张幺爷的嘴巴常常笑得合不拢,不信你看他眼睛上的眉毛都喜得打颤。平素间,任胡子是难得自己从包包里摸茶钱出来的。这几回喝茶,虽然那只摸钱的手在抖,最终还是将茶钱摸出来递给了丁四儿。可那眼珠子,却在丁四儿手上的碎铜钱上穿梭,直到看见进了别人的腰包,他才失望地轻轻叹了口气。
丁四儿虽然跑堂掺开水很累,但心理很是高兴。因为旷连长能在茶堂子里喝茶,就使德孝茶旅庄蓬荜生辉。就连丁四儿自己,也觉得精神了许多,风光了许多。况且,能给旷连长掺茶倒开水,是丁四儿这辈子的运气加福气。因此,丁四儿对所有客人的服务都分外周到尽心。
赵先生虽然不是张幺爷那样,喜得眉毛尖尖在打抖,但他心理却像喝了一碗蜜糖——甜透了。他在旷连长和众多茶客的劝说下,已在德孝茶旅庄开起了早书场子。他为了吊人的胃口,给旷连长讲一回《安安送——米》,又专门给镇上这些头面人物讲《五虎平西》。这样,赵先生把早晨吹闲壳子,摆龙门阵的时间也变成了收银子钱的好事。此刻,赵先生正在说道:
“但见那狄黄青一拳打出,顿时只听得虎虎生风。对方惨叫一声‘哎呀!我的妈呀!一声惊堂木拍在茶桌上,众人顿时被赵先生惊醒。赵先生趁机说道:“要知这人是死是活,明天早晨请早!”
正听得有趣的谌老板说:“赵夫子,熟人熟事的,你卖啥关子?”
旷连长也笑道:“这可是说书人的技巧,赵先生你说是不是?”
“这些雕虫小技,哪能瞒得过聪明人喃?”
旷连长的勤务兵给了赵先生的说书钱,赵先生连忙说道:“多谢!多谢!”刘团总也学着旷连长给了说书钱。任胡子犹豫了许久,那只手就是不肯往腰包里摸。他斜眼看见赵先生正要溪落自己的样子,赶忙将手伸进腰包,摸出了小钱,递了过去。他惹不起赵先生,赵先生那张嘴可比刀子还凶啊!
丁四儿见旷连长带着勤务兵出门,便慌忙追出去喊:“旷连长,你慢走!”
旷继勋也回过头来跟丁四儿打招呼:“丁志强,你也慢慢忙吧。”
众人都用羡慕的目光打量着丁四儿。人们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这个德孝茶旅庄的伙计,在孝泉镇也名不见经传,他竟能跟大名鼎鼎的旷连长交上朋友,就如五黄六月下起了一场大雪,十冬腊月在收大麦一样稀奇古怪。你莫看丁四儿是个残疾人,将来可能是我们这孝泉镇一位很有出息的人哩。
二
众茶客先后离开了茶堂子回去吃早饭了。丁四儿收拾了茶碗,刚在竹椅上歇息了片刻,张幺娘就喊张幺爷和丁四儿吃早饭了。
丁四儿埋头只顾吃饭,但一碗红苕稀饭还没有吃完,不知什么人站在茶堂子门口,亲切而又低声地叫道:“四儿”。
丁四儿忙将扒进嘴里的饭咽下去,这才抬起头来。原来,站在门口叫自己名字的少妇,竟是丁四儿的三姐丁三妞。丁四儿惊愣了下,才说道:“哦,三姐来了。我可都半年多没看到你了。”
“兄弟,你吃了早饭,在外头去三姐跟你说个话。”
“要得嘛!”丁四儿迅速把碗里的饭吃完,放下碗走进圆门内跟张幺爷、张幺娘打了一声招呼,就出来跟着三姐朝街外面走去。
丁四儿跟在三姐后头,在街上走了很长一段路,心里有些不安逸。原以为三姐会在德孝茶旅庄外面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跟自己说话,茶馆里很快就上生意了。三姐像很不理解兄弟的心情样,只顾埋头朝大沟桥的方向走去。丁四儿心里很不耐烦的样子,连续几次问:“三姐,你到底要往哪里去才说话嘛!”
“你跟我走嘛!就在那边。”
丁四儿压住心里的不满,继续跟着三姐朝大沟桥那边走去。姐弟二人来到那长着一片芭茅、芦竹的小溪边,丁三妞才停下脚步,等着兄弟慢慢地跟过来。随后,她又四处看看有没有人,便将快干的芭茅用脚踩倒,先坐了下来。她又叫刚走到跟前的兄弟也坐下来,摆出一副长谈的架势。丁四儿无缘无故地跟着三姐走了这么远的路,心里已经走得气鼓气胀了。况且,他对自己这位三姐,在感情上显得特别的陌生。这些年来,丁四儿跟三姐见面的次数还记得清清楚楚,三姐很少关心丁四儿这个兄弟的死活。现在,三姐将自己带到这么远来摆龙门阵,丁四儿便没有好气地对三姐说:“哪个有空跟你坐下来冲闲壳子。茶铺里忙得很,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嘛!”
丁三妞听了兄弟这几句硬梆梆的话,心里酸酸的,两串泪珠便从眼眶里涌了出来。她边哭泣边抽咽说:“我好命苦啊!我好苦命啊!连兄弟都……”
丁四儿见三姐伤心地哭了,嘴巴张了张,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丁三妞那年带着自家的男人,在洋马河割牛草。宽宽的洋马河流淌一股溪流,宽广的河边长着牛爱吃的茅草。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茅草尖上还缀着露水珠儿,丁三妞已经割满一背篼牛草了。她刚想歇口气,远处便飘来一支忧伤的民歌:
青杠树叶子多,没娘的女儿跟哥哥。
桤木树果果多,不是妹子顶哥哥。
堂屋洗脸哥哥怨,灶屋洗脸嫂嫂嫌。
哥哥嫂嫂你莫嫌,再把妹儿带三年。
听着,三妞顿时黯然神伤。她干脆放下镰刀,半边屁股坐在背篼上,希望那歌声继续飘来。丁三妞的小男人站在一旁不满地问道:“婆娘,你咋不割牛草了?我回去要告我爹。”三妞没有理踩自己的小男人,只注意民歌声飘来的方向。果然,那边的歌声又长声吆吆地飘了过来:
十八的姑娘家,泪眼汪汪如抛沙。
娘问女儿哭啥子,丈夫还是奶娃娃。
一怨爹妈太狠心,二恨媒婆贪谢金。
从我嫁出那天起,尤如丢下万人坑。
三顿吃饭要我喂,出门三步要我背。
三天不洗屎和尿,床边的裙裙一大堆。
左手提灯到床边,右手抱着我的郎。
抱在手上不算重,睡在床上不算长。
他是我儿,还是我郎?
公婆打我血长流,眼泪泡饭咽下喉。
我在地狱十八层,哪年哪月才出头。
那首歌还没有唱完,丁三妞的面颊上已泪流满面了。身旁的小男人继续威胁说:“你再不割草,我回去还要告我妈妈。”丁三妞用手抹了把泪水,可无论如何也没哭出声来。三妞爹妈死得早,如今才嫁给何家这七岁娃儿。这何家哪里是在找媳妇,分明是找了一个做家务的劳动力。这歌好像专为丁三妞编的。此时,长声吆吆的歌声,还在不断地往耳朵里灌。
十八大姐九岁郎,一锅舀饭同一床。
半夜郎醒要吃奶,抱到妻子喊亲娘。
三妞再也忍不住了,歌声刚落便放声痛哭起来。一旁的小男人,这才怔怔地,惶惑地看着她。他不晓得,自家的婆娘,为了啥子事会哭得泣不成声?又没得人打你,你哭啥子哭?
恰在这时,三妞的哭声飘进了另一个毫不相干的男人耳朵里。这个男人,就是孝泉镇卿家包的大粮户、舵把子卿廷华。昨晚,卿廷华在文家场伍八犟家里打了一晚麻将。他走到洋马河时,忽然听见一个姑娘的哭声。他好奇地走拢来看究竟,只见一个有几分亮色的姑娘,坐在牛草背篼上哭泣。卿廷华站住了。心想:这是哪家的媳妇这么漂亮哟?卿廷华在孝泉镇操了这么多年,玩过的姑娘少妇也不下五十人。我还从来没有玩过脸盘子长得这么漂亮的、眼睛这么勾人、身段子这么苗条的婆娘。妈哟!老子要是把这姑娘拐回去,屋里那三个婆娘,怕要被她比成老母猪哟!
卿廷华只眨了眨眼睛,又回过神来。听旁边那个碎娃儿“婆娘,婆娘”的叫喊,卿廷华才明白了眼前这个姑娘的处境。太可惜了,这么漂亮的姑娘却嫁给了还在穿开裆裤的小娃儿。卿廷华顿生邪念,他不顾一切地大步跨了过去,招呼丁三妞:“小娘子,你在哭啥子?你是不是在想男人,我这不是来了吗?”
“呸,我才是她男人。”
卿廷华不禁大笑,问道:“你真是他男人吗?”
“她是我爸拿银子给我娶的婆娘。”
“哦,你爸是有钱人啰!”卿廷华眼珠一转说:“你爸爸叫啥子名字喃?”
“我爸姓何。”
丁三妞已经擦干泪珠,正想背起背篼要离开这鬼地方。听这人在问自己的小男人,她忙制止男人道:“寿儿,不准说话。”三妞将牛草背篼背在背上,拉起男人快步离开了洋马河,朝回走去。
卿廷华见丁三妞拉着小男人走了,却并不去阻拦。他心里充满同情地想,你这大姑娘真是遭活罪呀!我要想把你救出苦海,你还不领我的情嗦?你冲啥子气嘛?当真话,好心给你当成猪心肺了嗦?卿廷华站起身来,朝四周的住家院子看看,便忽然大声地问那位小男人:“你爸是不是叫何福财?”
小男人惊奇得回过头来问:“你咋晓得我爸?”
“我是你爸的老朋友。”
小男人说:“你咋没来耍?”
卿廷华满脸堆笑说:“我要来,我要来的。我还要救你婆娘出苦海哩!”
丁三妞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回头过来又看了眼卿廷华。但见,卿廷华正亲切地、笑容满面地也在看着她。丁三妞心里想,要是真的能出苦海,那到也算是有福气呀。可是……她又想到自己的命实在太苦,眼泪又像断了线的珠子从眼眶里滚落出来了……
三
这天晚上,该是何福财该倒霉的时候。
何福财当初把丁三妞娶回来做媳妇,当然不是他的本意。况且,儿子才黄瓜起蒂蒂,娶啥子婆娘嘛!原来,他是想趁丁三妞死了爹娘,长得眉清目秀的丁三妞,将来一定是个美人坯子,打算弄回来做小老婆。他却又怕屋里那两个婆娘闹事。想来想去,他便以儿子的名义,先把丁三妞娶回来再说。何福财这一手果然很灵验,两个婆娘不是同意给儿子娶媳妇,却都愿意给屋里娶来了个不需花工钱的劳动力。这个夏天里,丁三妞穿得单薄,何福财常常能看丁三妞两个颤摇摇,鼓胀的奶子,被搞得神魂颠倒。这些天来,他时常都在思考着怎样越俎代庖,替儿子圆了房。但明着来又不行,以后出门会被说成是乱伦,烧媳妇的火,亵渎了祖宗,并会被别人指为不孝之子。妈的,鬼摸脑壳了,咋会把丁三妞当媳妇娶回来,现在却弄得他左右为难。但何福财又舍不得媳妇老守着空房。妈哟!先跟她睡了再说!他不断地在寻找睡丁三妞的机会。两个婆娘却把他盯得紧,好像对他是分工轮班监视着。她们不但要寿儿挨着丁三妞睡,当个眼镜子,也解除了寿儿半夜尿床也没人经佑的烦恼事。何福财就是半夜起来上茅房,也被婆娘追问。先人板板,这两个爱吃酸醋的死婆娘!
今晚何福财睡在大婆娘的床上。看了看身边躺着的母夜叉一般的老婆已经打起鼾声来,他便轻轻下了床,又轻脚轻手地去开门。
“你不睡,又到哪里去?”大婆娘睡意朦胧地问了句。
何福财一惊,连忙答道:“我去屙尿。”
“那屋里不是尿桶。”
“哪个大男人在屋里屙尿。”
“那你快些嘛!”
何福财毫无办法,只得假装屙了一回尿又回到床上。他还没有睡熟,外面便齐刷刷地跳进几个人来。何福财大吃一惊:“啊!棒老二!”他急忙跳下床来。刚刚穿了一件衣裳,还没有找到自卫的武器,只听到一阵脚步声,棒老二已经拨开了他的睡房门闩子。
何福财想继续喊,但黑暗中他分明看见了有几把明晃晃的大刀在他的眼前晃动着。随即,便听见棒老二向他发出了恐怖的威胁声:“姓何的不准乱动,格老子放聪明点,免得你身上的肉臭。”
何福财已经话不圆了:“你……们……想要些啥?”
“我们只要人。”
正在这时候,儿子在丁三妞的房间里大喊大叫起来:“爸,妈呀!”
“寿儿,寿儿。”已穿好衣裳的大婆娘惊炸炸地叫喊着。
棒老二提着大刀又对何福财说:“我们只要你那黄瓜起蒂蒂还没用的儿媳妇。你放明白些哈,你要舍不得这个媳妇,我们就绑你娃儿的肥猪。”
何福财惊恐万状,简直不晓得咋回答。但他的大婆娘却惊叫道:“放我们寿儿,放我们寿儿!你们要啥都给。”
提刀的棒老二又说:“姓何的,你这个婆娘倒还是个聪明人。我也不想跟你再卖劝世文了,你要相识点,敢快把你同丁家的契文交出来。”
何福财此刻虽然像一个被指挥的木头人,却慢腾腾地不想去找契文,他心里,是十二万个不愿意丁三妞让别人抢去。但是,三妞的房间里又传出儿子阵阵的叫喊声。何福财的大婆娘再也忍不住了,自己从木箱中找出了那份契约,说:“你们放我儿子!你们放我的儿子!”
寿儿被人送到了大婆娘的房间。棒老二把契约拿到手上后,指着何福财说:“姓何的,二天你胆敢在外头打胡乱说,小心你这娃儿被我们当成肥猪洗!”
何福财全身一下子瘫软下来了。
四
卿廷华的大婆娘王氏,晓得今晚男人又带着人在“摸夜螺蛳”就是去外头抢劫。她坐在床上睡都没睡着。她一听见狗叫声,便立刻从床上跳下来,颤巍巍的尖尖脚,很艰难地朝门口走去。卿廷华带着丁三妞来到她的面前,吓得她手上拿着的那盏油灯的火苗都在不停地打闪。她惊惶失措地问男人:“咋是个大活人?”
卿廷华将塞在丁三妞嘴里的布取出来,王氏将菜油灯凑近一照。只见丁三妞在黯淡的灯光照射下,更显得十二分动人,怜惜之情也油然而升。她顿时明白了男人的意思,嘴里立刻“叽叽咕咕”地诅咒起来。她转身立刻来到堂屋,点燃了几炷香,跪在神桌前,口中念念有词……
卿廷华跟进堂屋,来到了婆娘面前,说:“祖先人也敬了。”
王氏无可奈何地说道:“你是个馋嘴猫,今晚黑不准乱来。你到三妹屋里去睡。再撇脱也要合张八字,要是她命里带克,我看你有几条命?”
卿廷华笑了笑。心想,人都被抢回来了,还怕她变鸽子飞了不成?于是,卿廷华就依了大婆子王氏,悠哉游哉窜到三姨太房间里去了。
丁三妞被丫头燕儿拉进房间后,仍然跟木头一般。她也不反抗,给人一种听天由命的超然感觉。卿廷华带着人打开丁三妞睡房的刹那间,她本能地“啊!”了一声后,嘴便被一只胖胖的大手堵住了。随后,她就听到一声男人威严的命令:“不准喊!我是救你出苦海的。”
丁三妞一切都明白了。她不用看这个人的脸面,就知道了自己今晚的吉凶祸福。她开始惶恐,同时也怀疑,难道这就是自己命运的转机吗?她也不想反抗,由命运任意把她抛向任何一个地方。反正都是受苦受难,到什么地方已无所谓了。但是,小男人的叫喊又使丁三妞不知所措,心里乱糟糟的。正在这时,一块布又塞在了她的嘴里,将她的嘴巴堵得严严实实的,随后又将她的双手捆了。此时的丁三妞,本能地也想反抗。但想着到处都是火坑,也由不得自己了。因此,这伙绑票者叫她往哪儿走,她就往哪儿走,整个人就好像被卿廷华牵动的木偶。
丫环燕儿粗略地了解到了丁三妞的处境。不过,她相信丁三妞定要做卿廷华的第四房婆娘。假如她受宠,将来对燕儿好就谢天谢地了。说到伤心处,燕儿也想起自家的身世,不由得跟着丁三妞流了一场泪又流了一场泪。燕儿想起自己说不定也得跟老爷睡觉的,那么多的女子都没有逃脱卿廷华的手掌心。何况燕儿这个小丫头,长期生活在卿廷华的眼皮子下面,如同卿廷华家里厨房中菜板上的一块肉。全凭卿廷华砍,全凭卿廷华下油锅。想到此,燕儿竟劝丁三妞来:“丁姐姐,我妈说,变女人的都是菜仔命,就看你的香烧到时候没有。”
丁三妞再也忍不住了,忽然抱着陌生的丫头燕儿失声痛哭起来……
王氏通过燕儿了解到丁三妞的身世,便差人请来孝泉镇的张八字。她先给张八字塞了包袱,那张八字也就只好按照她的意思给卿廷华丁三妞两人合八字了。
“卿老爷,这丁姑娘是水命,你是火命,水火哪能相容?而且丁姑娘那双大脚板就像魏延那双大脚,会踩灭了诸谒亮的七心灯……”张八字把卿廷华说得眼珠子都鼓起来了。卿廷华还不甘心,哀求道:“张先生,你得给我想个办法。”
“办法嘛!”张八字瞟了瞟王氏,才结结巴巴地说道:“办法倒是有的,但丁姑娘这两年是赵匡胤流鼻血——正在红头子上,她有点逢冲。我看再过两年,等丁姑娘过了红冲期,卿老爷再娶她入房室,自然就像是林冲把婆娘献给高俅——就没球事了。”
张八字既不得罪卿廷华,又得王氏的包袱,自然觉得自家的手段实在高明。中午还被卿廷华和王氏奉为上宾,一瓶绵竹大曲酒,把他灌得醉偏醉倒的,嘴里唱着《迎贤店》中的道白回家去了……
“做生意哪个不是为了钱。”
“那么常老爷就把你这招牌改了。”“咋个改喃?”
“把这《迎贤客》改为《迎钱店》……”
“吔,你硬是挖苦人喃……”
张八字一走,卿廷华的大婆娘王氏便跟卿廷华商量说:“这两大两年时间,家中放着个大活人,就像把人参燕窝送给了过路的讨口子——硬是糟蹋了。老爷不如先把丁姑娘卖出去,随便哪家买去了我们都不吃亏。”
卿廷华本来喜形于色地要娶第四房婆娘,却被张八字一合八字,他那颗心就又被说得高悬起来了,心中好像是十五只吊桶在打水——七上八下的。他想,既然跟丁三妞做不成酒,那就……他想,自家风流多年,难免不碰到个克星。可我卿廷华还是活得十分洒脱。现在既然事已至此,把丁三妞当个长年使唤,何乐而不为呢?想到此,卿廷华便对大婆娘王氏说:“这丁姑娘既然跟本人八字不合,张八字还说丁姑娘逢冲,我也就不娶他做四房算了,当真话老子的命要紧。不过喃,丁家这女子倒是个好劳力,那双大脚是比你们这些尖尖脚做活路要强多了。我们后门围墙边有间柴房,把这间房子收拾出来给她住。一年喊她养两槽肥猪,也比把她打点出去强多了,也赚钱多了。”
王氏没办法再继续强硬争辩了。况且,男人暂时打消了娶四房婆娘的想法,这终归达了自己的目的。权且让丁姑娘暂时住下来,以后再同二房、三房商量,看咋办好,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丧门星妖精赶出卿家的大门。本来一个男人三房分夜,王氏就感觉得十分寒酸。如果再来一个“抢食”的,我这做大房的人老色衰,不是只有眼睁睁地独守空房吗?想到此,王氏说:“老爷说的也是,先把她安顿下来,就当卿家请了女长年吧。”
丁三妞的命运就这样被定了下来。这晚吃过晚饭,丁三妞在燕儿的陪同下进了后院那间已被粗略收拾了下的房间。这两天里丁三妞都没有看到卿廷华,只是在吃晚饭的时候,三房问起老爷到哪里去了。大房说是去齐福乡曾方元家里玩麻将去了。丁三妞感到一阵轻松,在这间暂时属于自己的柴房里,也许还可以睡个安稳的觉了。
可是,丁三妞不敢脱衣裳而合衣躺在床上,但却怎么也不能入睡。她在往日的夜晚里。虽然,那个小男人给了她无尽的烦恼,但在入睡前总有个奶声奶气的声音跟她伴嘴。此刻,静静想起这些情景,丁三妞忽然觉得有种甜蜜的情感涌上了她的心头。现在,她一个人睡在床上,脑海里觉得空空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硬往脑子里钻进来。后来,她又想起自己的姐姐丁二妞,也想起了自己的兄弟丁四儿。她想起爹娘的早死,想起姐弟三个各自东西。现在,二姐和四儿兄弟也不晓得,我已跨进卿家的大门了,以为她丁三妞还在何家当小人媳妇哩。我们姐弟几个命真苦,我丁三妞的命就更苦了。想着、想着,丁三妞的眼角边悄然地又淌出了一串串伤心的泪珠儿。
半夜时分,丁三妞在睡意朦笼中,忽然听到了脚步声。她立刻警觉起来,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她刚想喊燕儿,又想起燕儿离这里还远得很。外面那人,似乎也听见了丁三妞的响动,他两步来到门口对着门缝威严地喊道:“不准说话。”
丁三妞听出来了,这不是那晚在何家时同样一个人的声音吗?门闩终于被他拨开了,丁三妞看到冲进屋里的人影。他果然是那个要娶自己做婆娘的卿廷华。人影来到了丁三妞的床边,卿廷华又发出了威严的低声吼道:“不准喊!”丁三妞已经被吓得喊不出声来了。这时,丁三妞忽然被黑影抱在怀里。丁三妞惊叫道:“你……你……”
卿廷华嬉皮笑脸地说道:“你都是我的婆娘,咋还……”
“还不是……”
卿廷华没有让她说话,用嘴堵住了丁三妞的嘴亲。随后,卿廷华的嘴唇如同一块烧红的炉铁,滚烫地从丁三妞的嘴唇上向下移动,一直移到了丁三妞的颈脖,丁三妞感到一阵昏眩。
“不!不!不!”丁三妞嘴里在喃喃地说。
卿廷华便放松了丁三妞,附在她的耳朵上轻轻地说:“你不愿意跟我睡就算了,我卿廷华是不会逼你的。”说完,便轻轻地跳下床来,在房间里站了片刻才走了出去。他跨到门外,又回过头对丁三妞叮嘱道:“你把门关好,外面冷。”他将门拉上,才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夜里,卿廷华又从外面拨开门进入柴房。他站在丁三妞的床前,把一节丝绸料子放在了丁三妞的手上,嘴巴凑过去亲丁三妞。她仍然忙用手阻拦。但卿廷华迅速亲了一口又走了。在门口又不忘叮嘱三妞,把门闩好,外边冷。
第三晚上,卿廷华又用草纸包了一包糖食,放在丁三妞的枕边说:“半夜饿了你好吃。”这回卿廷华又亲丁三妞几口。丁三妞却像木头人一般。卿廷华亲了她,又很能节制地离开了柴房。
第四晚,丁三妞干脆懒得闩门,便坐在床上。不知为什么,她像在等待卿廷华似的。外面一有风吹草动,丁三妞便猛地一下提起了精神,以为卿廷华又进来了。然而,卿廷华的身影却始终也没有出现……
第五晚上……
第六晚上……
直到第十晚上,丁三妞心里升起一股恨人的怒火来。她坐在床上想,明晚把门闩了。但是,当她刚刚躺下,卿廷华又带着一件刚在外面抢来的皮褂子朝柴房走来。他刚想拨门,而那门却是开的。卿廷华心中大喜,他三两步来到床前。把皮褂子交给丁三妞,便挨着三妞坐在床边。他轻轻地端起丁三妞的脑壳,使劲地亲了一口,亲得丁三妞几乎不能出气了。随即卿廷华的手朝丁三妞的乳房伸去,轻轻地摩挲着。丁三妞惊惶失措地感到有些恐惧、浑身也不停地颤抖。卿廷华那只手随后又开始向丁三妞下身摩挲着,移动着……丁三妞猛地惊醒,本能护着……
卿廷华愣住了。黑暗中的卿廷华,声音变得更加温柔。他附在丁三妞的耳边轻轻地说道:“我要娶你做四房,你还……”
“还没有做酒。”
卿廷华失声笑道:“我们卿家有规矩,要生了娃娃才做酒。”
丁三妞本能的保护意思,在卿廷华那只手的摩挲中渐渐地消失了。当她感到下身撕裂的疼痛时,她才惊喊起来……
此后,丁三妞在卿家的地位变成了四不像。既不是名正言顺的卿家四房,也不像燕儿那样的佣人。燕儿给卿家干活,但不陪卿廷华睡觉。而丁三妞呢?既是卿家的佣人,有时还要陪卿爷睡觉。当然,这得看卿爷有兴趣想起她丁三妞住的那间柴房时才来睡她。卿廷华有时虽然也能想起丁三妞来,但还要躲过那三房婆娘,六只监督的眼睛。丁三妞时间一长没有见到卿廷华,竟然烦躁不安,渴盼着卿廷华立刻能够跨进她那间柴房来。丁三妞经常在心里祈祷着,希望自己的肚皮快些长大起来,也好堂堂正正地跟老爷做酒。这样才能搬出这间柴房,搬到四房应该住的那间高大的瓦房里去。因此,侍候并跟卿廷华睡觉,成为丁三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希望肚皮快些长大起来,也成了丁三妞生活中的希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丁三妞已经认命了。每当想起卿廷华的温柔和体贴,她就感到幸福。她已认定,卿廷华就是自己正而八经的男人了。丁三妞也在卿家这样四不像地过了好几年了。
五
丁四儿见三姐不停地哭泣,心里也十分难受。他憋闷了许久才说道:“三姐,你莫哭了,你到底有啥事嘛!”
丁三妞听兄弟的声音软下来了,果然就不哭了。她擦了擦眼睛,抬头看见兄弟的脸色已经放宽了,才问:“兄弟,听说你跟旷连长相好,当真话有这回事吗?”
说起跟旷连长的关系,丁四儿的心里忽然升起一种自豪感来。原来,平日里德孝茶旅庄,那个提开水壶的丁四儿,跟大名鼎鼎的旷继勋的名字连在一起了,就像星星跟着月亮一样沾了光。丁四儿不知不觉地成了孝泉镇的名人了。此刻,当听到自家的三姐也问起这件事,丁四儿冲口说:“那还用说吗!”
三妞又问:“听说旷连长是来孝泉镇抓棒老二的。咋都半个月了,旷连长咋还没得动静喃?”
丁四儿一听,老大不安逸,责备三姐说:“三姐,你才问得怪嘞!这些事情,人家旷连长咋会跟我说嘛?三姐,你到底问这些事要做啥子?”说完,丁四儿忽然想起卿廷华来。难道那晚在德孝茶旅庄来打抢的棒老二是卿廷华?三姐要不然来问这些事做啥子喃?想到这里,丁四儿用大人的口气训起人来,说:“三姐,你闲事少管,走路伸展。你操这些闲心做啥子?”
“兄弟。”三妞几乎在哀求自己的兄弟丁四儿了。忽然,丁三妞好像想起啥子似的。她把挎在肩头上的布包取下来解开,取出一件衣裳和一双平底布鞋,双手送到了丁四儿的面前。说:“兄弟,这是我给你做的,你试一试合不合适?”
看着衣裳和鞋子,丁四儿感激地望着三姐。没爹没妈的丁四儿,平时间全靠二姐给他缝穿的。三姐给丁四儿缝衣裳是很难得的,但他并不怪三姐。现在,他将衣裳接在手里想到,到底是自己的三姐,她也想着兄弟。
“兄弟,才将我说的那件事帮我打听下。”
丁四儿的喉管里忽然又像咽下去了一只苍蝇,心里很不安逸。三姐你不找我打探事情,是不会来孝泉镇的。难道这件衣裳,这双鞋子就是三姐拿来跟我换取消息的东西?想到这里,丁四儿恨不得将衣裳和鞋子丢给三姐,一走了之。他又低头看着坐在干笆茅草上的三姐,她那双眼睛也在可怜兮兮地望着自己。三姐也够可怜了。四儿不敢再看三姐那双眼睛,只说:“我当然不晓得,我是小娃儿,他咋会跟我说这些事嘛!我只晓得是省府老爷和德阳县的人请赖……心辉赖旅长帮忙在孝泉逮棒老二,旷连长才来孝泉镇剿土匪的。旷连长用啥办法逮棒老二,哪个也不晓得。”
丁三妞也基本满足了。兄弟不晓得,总不能逼他。况且,昨天晚上,卿爷也只是叫我来随便问问。如今,我已经了解到这么多的事,也算对得起昨晚他来跟我百般亲热了。想到此,丁三妞站起身来,拍了拍屁股上的芭茅叶子,说:“兄弟,我回去了,我就不耽误你了,茶堂子里也忙。你二天晓得啥事就跟三姐说一声哈。”说着,便起身从长满芭茅的小溪边上,往大路上走去。
丁四儿跟三姐打了一声招呼,便拿着三姐送给他的衣裳和那双平底布鞋朝德孝茶旅庄走去。这一路上,丁四儿心里却总是高兴不起来。他总觉得三姐今天送东西,是来跟他交换消息的。他回到德孝茶旅庄,走进他那间卧房,将三姐送的衣裳和鞋子甩在床铺上,便忙到外面去招呼茶客了。